記者 | 尹清露
編輯 | 黃月
距離《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第二十七屆會議(COP27)還有一周時間,隨著腳步臨近,近期一系列發生在英國的針對美術館的氣候抗議活動格外引人關注。
10月14日,英國環保組織“停止石油(Just Stop Oil)”的兩名年輕成員走進倫敦國家美術館,把亨氏番茄湯扔在了梵高的《向日葵》上。在此之后,不僅莫奈的《干草堆》接受了土豆泥的“洗禮”,維米爾的《珍珠耳環的少女》也遭到襲擊,一名男子用膠水把自己的頭粘在保護畫作的玻璃上,并聲稱:“當你看到美麗無價的東西在眼前被摧毀時是什么感覺?憤怒嗎?那么當你看到地球被毀滅時,那種感覺去哪了?”

這些事件的直接起因是英國的生活成本和能源危機,更深遠的背景則是全球范圍內的氣候崩潰。扔番茄湯的主角之一、21歲的Phoebe Plumme在聲明中稱:“對于數百萬寒冷、饑餓的家庭來說,燃料貧困使日常生活變得難以負擔,而與此同時,人們正在死于超強季風、大規模野火和無休止的干旱。”
他們的行動很快得到了大量關注,社會評價褒貶不一。《衛報》的一篇文章表示抗議者們對于“藝術重要還是生命重要”的詰問發人深省,《每日電訊報》則認為這只是效仿達達主義的一次無力的表演。有評論者支持他們的立場,卻認為這種行為本身會惹人反感、疏遠潛在的支持者。
為什么即使惹人厭煩也要堅持行動?這樣的舉措真的有效嗎?結合過往的環境保護運動來看,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會變得更加清楚。

“引人厭惡”,一再升級:抗議活動沒有其他路徑嗎?
顯而易見,“引起反感”正是這一行動的目的所在。研究抗議運動的社會學教授丹娜·費舍爾認為,這是一種戰術創新,因為游行、靜坐和封鎖橋梁事件很快就被媒體寫成了舊聞,這迫使活動者們把自己粘在藝術品上,或者至少在外觀上污損藝術品,以吸引更多目光。他們的另一個策略是“自覺被邊緣化”,與積極招募大量成員、集體抗議的做法不同,“停止石油”的核心策略在于用最少的人數獲得最大程度的媒體曝光。
這樣做的首要原因,當然是氣候新聞本來就難以吸引目光,隨著環境危機愈演愈烈,只有足夠刺眼和絕望的行為才能激起一點浪花。在向公眾進行解釋時,“停止石油”的成員就經常強調自己“別無選擇”,因為正常的系統已經失敗了。這種失望的情緒隨著COP26之后英國政府的一系列行為而變得更加明顯。一位組織內的成員發言稱,盡管英國承諾了2050年前二氧化碳凈零排放目標,但政府仍然批準了在北海新建油氣田,這使得他們不再要求政府做出改變,轉而阻止政府做出不應該做的事,“從公民不服從轉變為公民抵抗”。

另一方面,一再升級、出奇制勝的抗議手法,也和環保團體自身的生命周期有關。對政府感到失望、要求直接行動的聲音在環保歷史上并不新鮮,過往的抗議運動也曾取得過頗多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們要么曇花一現,要么總是不可避免地成長為更加制度化的團體行動模式,并出現諸多問題,比如無法進一步敦促政府實現承諾的目標。
在《改變一切》中,環保主義行動家娜奧米·克萊恩談到過環境正義運動的興盛與隨之而來的失敗。當1962年《寂靜的春天》出版時,它帶來了一種全新的、不同于以往紳士范兒的環保運動,僅在1970年代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比如共有23項聯邦環境法案正式通過成為法律。但隨著環保團體的擴張,運動的工作不再是簡單地組織抗議,而是擬定法律、起訴違法的財團公司。于是,曾經由一群嬉皮士組成的“烏合之眾”,就變成了律師、說客和聯合國峰會的專業人士。“許多人都以自己是局內人而感到自傲,他們有能力回旋于政治光譜的各個角落,并和不同勢力嫻熟地打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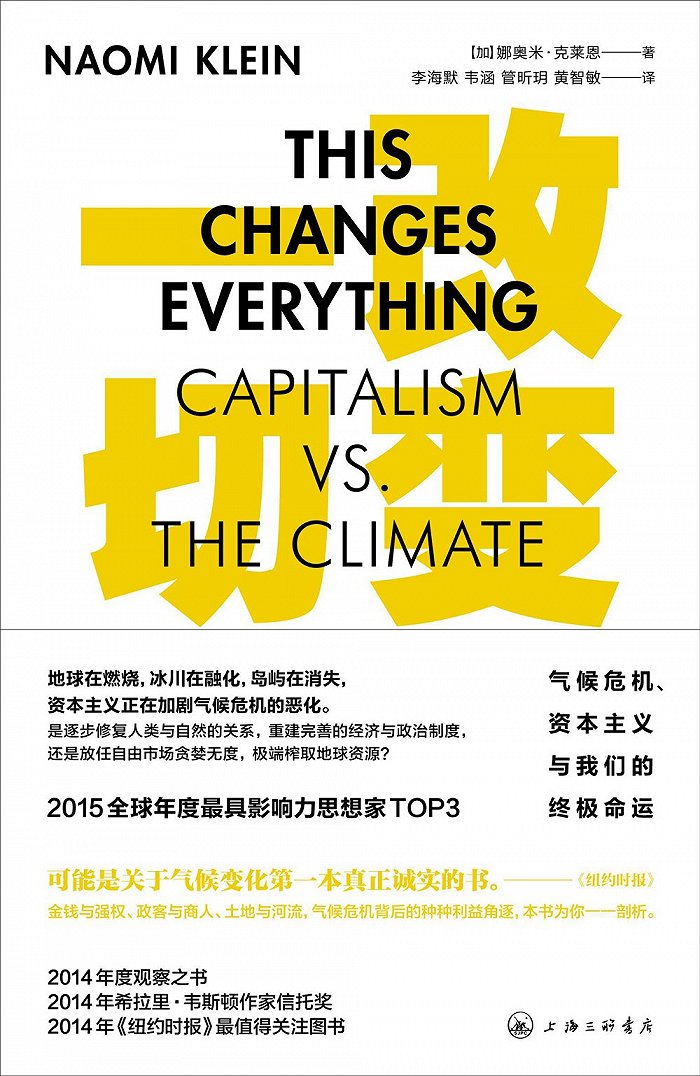
[加] 娜奧米·克萊恩 著 李海默 韋涵 管昕玥 黃智敏 譯
上海三聯書店·理想國 2018-1
在這一過程中,大型綠色組織和化石燃料財團的合作關系尤為關鍵。組織需要依靠財團的資金,而財團需要參與組織來進行形象公關,也即粉飾性的“漂綠”活動。當這些組織承諾將錢用于資助旨在嘗試阻止災難性的全球變暖的項目,卻往往會受制于財團本身的價值觀。克萊恩提到,情況經常是這樣的:雖然綠色環保組織并不否認氣候變化的真實性,但當本應推進的政策是將溫室氣體視為危險污染物加強管制時,他們卻在“推動一種令人費解的市場策略,將溫室氣體視為可以交易、打包出售和投機的抽象概念”。這種策略認為,要勸說政客去懲戒財團無疑是艱難的,與其如此,不如選擇更容易的選項,比如勸說消費者們購買昂貴但有更少毒素的衣物清潔劑——也就是將責任轉嫁到個人身上。
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一些感到幻滅的積極分子選擇和主流徹底絕緣,并組織起更好戰的、以抗爭為導向的組織。近年來最著名的,便是興起于2018年的“滅絕叛亂”(Extinction Rebellion),他們希望利用非暴力的公民不服從來迫使政府采取行動,并且從過往的草根運動中汲取靈感,他們的策略之一——通過鼓勵更多抗議者被警察逮捕、從而壓倒法院系統——可謂影響深遠,“停止石油”組織的種種行為就深受他們的啟發。

“滅絕叛亂”數十個團體出現在世界各地,不僅吸納了曾經對非暴力抗命行動嗤之以鼻的前公務員,比如澳大利亞環境部長的前顧問和前聯合國律師,還募集到大量資金、爭取到了與英國高級政治家和部長進行會談的機會。2019年5月,英國議會宣布進入氣候緊急狀態,以作為對“滅絕叛亂”等環保團體的正面回應。
即便如此,他們仍然要面對“接下來該做什么”的問題,并迎來尖銳的內部沖突。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政治科學家羅素·道爾頓(Russell J. Dalton)研究發現,雖然環境團體可以成為有力的政策參與者,但是隨著運動提出的問題在政治進程中得到解決,行動的動力就會減少。另一方面,克萊恩曾經批評過的那些大型團體的弊病也再次應驗。雖然“滅絕叛亂”旨在建立一個參與性、去中心化的組織,但已經有人抱怨道,團隊逐漸壯大之后,只允許那些聲音最大的人——也就是白人中產階級男性——占據主導地位,其他人不滿于無休止的會議、錯綜復雜的決策過程、龐大的WhatsApp通訊網絡。
由此看來,與前輩們不同,由年輕人發起的“停止石油”似乎只有繼續探索挑釁性的抵抗活動,才能保持自身的活力,只有讓自己的行為邊緣化,才能逃脫大型組織的命運。只不過,與過往團體不無相似之處的是,“停止石油”和石油公司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的資金來源氣候應急基金(Climate Emergency Fund)正是石油大亨的女兒艾琳·蓋蒂(Aileen Getty)幫助創建的,抗議者們的激進策略在長遠來看效果如何,或仍有待觀察。
藝術與石油:為何繪畫是行動目標?
另一個引人矚目的事實是,“停止石油”在此之前其實已經進行過多輪活動,但直到往梵高的畫上扔番茄湯,他們才算徹底“出圈”。觀眾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厭惡:梵高做錯了什么?歷史學家和人權活動家克雷格·默里就認為,這是愚蠢的破壞行為,因為“這幅美麗的畫并不對環境問題負責”。
不過,也有人聲援“停止石油”,并強調了這類行為的正當性。行動主義研究者、倫敦大學講師奧利·莫德(Oli Mould)撰文指出,就像化石燃料公司的“漂綠”行為那樣,這些公司也熱衷于“藝術清洗”(artwash),也就是向藝術機構提供資金,這使得藝術本身和石油工業完全交織在一起,變成了企業權力的延伸,所以,藝術作品應該成為氣候活動的合法目標。
在分析藝術機構與化石燃料公司的著作《藝術清洗:大石油與藝術》(Artwash: Big Oil and Arts)中,作者梅爾·伊文斯(Mel Evans)就曾提出,石油公司對藝術的忠誠已經變成一種全球現象,其結果之一就是,任何關注生態破壞、抵制石油資源土地掠奪的作品都可能會讓策展人猶豫不決。作者分析了泰特美術館和英國石油公司(BP)的長期合作關系,發現即使贊助商不對展覽進行直接審查,也會產生許多微妙的影響,比如策展人會考慮到“BP不會喜歡這個作品的”,觀眾也會在觀展時看到BP的標志,無形中接受那朵黃綠色小花帶來的心理暗示,認為石油公司并非想象中那樣對環境有如此糟糕的影響。

近十幾年來,為了引起公眾對石油贊助藝術的關注,陸續有團體發起了抗議活動。2006年,“藝術而非石油聯盟”(The Art Not Oil Coalition)來到自然歷史博物館,在由殼牌公司贊助的年度野生動物攝影展上把黑色的油性物質倒在展品上;從2010年開始,藝術團體“解放泰特”也多次未經允許闖入泰特現代美術館的展覽現場,進行行為表演,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個名為《人類的代價》的作品——一名裸體男性以嬰兒的姿勢躺在地板上,并被蒙面人不斷澆上石油,以此來紀念和警示BP在墨西哥灣的石油泄露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藝術館進行氣候抗議的例子并不罕見,但是目前為止,大部分動員都是直接針對和石油公司有合作關系的文化機構,而“停止石油”則是訴諸于和他們的目標看似脫節、毫不相干的傳統繪畫作品。這一點應當如何評價?
根據《衛報》的報道,是藝術拜物教而非藝術成為了活動家們的目標,只需要看看借由梵高之名在世界各地舉辦的沉浸式VR體驗展,就會意識到,藝術家已成為商品的一種以及資本主義的剝削對象,而這些展覽本身也耗費了大量能源。

在藝術界內部,雖然熱衷于提高環境意識的藝術展覽正在激增,但一方面,全球藝術系統本身就是碳密集型的,即使是表達環境保護主題的作品也會在世界范圍內運輸時帶來大量排放;另一方面,早在2007年,策展人、環境藝術支持者Stephanie Smith就警告我們,許多看似正義的展覽會給觀眾和藝術家帶來輕松的美德,對于真實的氣候狀況卻于事無補。而當“人類世”、“藝術與氣候變化”這類標題成為當代展覽中的陳詞濫調,最有效的藝術抗議就不一定要提到氣候變化,也不一定要求人們立刻采取行動,而應該致力于擴大行動的心理能力。
站在這樣的立場來看,向畫作潑灑湯汁至少做到了后者,也就是讓觀者感到驚愕和不可思議。至于抗議者發出的詰問——“藝術和生命,哪個更重要”,它的目的并不真的在于比較兩者,更多的是要讓人感到剎那間的困惑和反思。況且,它的確揭示出了重要的一點:氣候變化已經不再是藝術要解決的問題,而成為了一種歷史條件,不僅影響著所有藝術品,也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存。
而矛盾的是,也是這一根深蒂固的歷史條件,讓“不再開采新石油”的抗議聲音顯得有點單薄,因為在這個條件所造成的現實之中,一系列的問題也同樣棘手:如果政府不再開采新石油,在替代能源尚且無法填補缺口的當下,本就艱難的居民生活條件又將如何得到保障?抗議者們也許會要求富人接受更緊縮、更簡單的生活方式,從而減輕窮人的負擔,可是這一愿景要如何實現呢?氣候活動家們為這些問題打開了一道缺口,但具體應該如何回答,卻遠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參考資料:
“Opinion | The Contradictions of Climate Activism -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2/10/15/opinion/oil-energy-crisis-van-gogh.html?searchResultPosition=6
“How Should Art Reckon With Climate Change? -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2/03/25/t-magazine/art-climate-change.html
“Inside Just Stop Oil, the youth climate group blocking UK refineries | Climate crisis |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22/apr/01/down-to-earth-just-stop-oil-protest
“Climate Change Has Transformed Everything About Contemporary Art – ARTnews.com”
https://www.artnews.com/art-in-america/features/climate-change-contemporary-art-1202685626/
“Do we really care more about Van Gogh’s sunflowers than real ones? | George Monbiot |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2/oct/19/van-gogh-sunflowers-just-stop-oil-tactics
“Just Stop Oil: do radical protests turn the public away from a cause? Here's the evidence”
Russell J. Dalton. (2015) "Waxing or waning?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environmental activism", Environmental Politics
Mel Evans. (2015) Artwash: Big Oil and Arts, Pluto Press
《改變一切:氣候危機、資本主義與我們的終極命運》[加] 娜奧米·克萊恩 著 李海默 韋涵 管昕玥 黃智敏 譯 上海三聯書店·理想國 20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