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在成為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前,安妮·埃爾諾對于許多中國讀者來說還是一個比較陌生的名字。幾乎所有諾獎得主都面對著全世界讀者心中的一系列問題:他/她是誰?寫過什么作品?配拿諾獎嗎?埃爾諾也不例外。
1940年,埃爾諾出生于法國北部諾曼底一個普普通通的小鎮家庭,她的父母經營著一間兼賣雜貨的咖啡館。埃爾諾憑借優異的成績走出了家鄉,成為了一名教師。埃爾諾是她第一任丈夫的姓氏。接下來就是很熟悉的劇情了:一個嫁入資產階級家庭的女性知識分子,雖然看似實現了階級躍升,在智識層面卻失望地發現自己欲求不滿——當一個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似乎并不是她設想的自己在婚姻中的位置。
從1970年代開始,她背著丈夫偷偷進行文學創作。第一本書《一個男人的位置》是一部自傳性質的作品,她在書中追憶了去世多年的父親,該書出版當年就獲得了法國國內非常重要的文學獎項勒諾多文學獎。從那開始,埃爾諾陸續出版了20多部作品,大多具有一定的自傳色彩,她長期活躍在西方文藝界。2021年,由她的小說《正發生》改編的同名電影在威尼斯電影節捧得金獅獎,該作品講述了在1963年的法國,一位年輕的女學生意外懷孕后發生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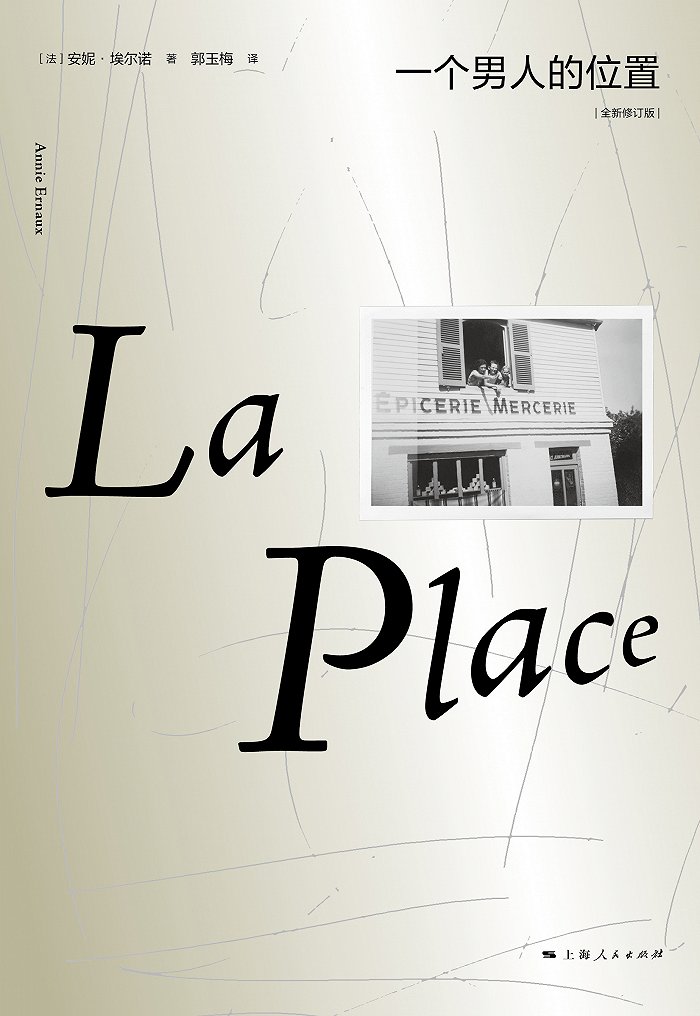
埃爾諾的經歷讓我們產生種種聯想。她的作品中強烈的自傳性是否說明她是從事“身體寫作”的女作家?她是一個離開小鎮但回望家鄉、反思階級問題的“小鎮做題家”嗎?亦或是一個真人勵志版的“我的天才女友”?日前,播客節目“跳島FM”邀請了長期關注和研究埃爾諾作品的蘇州大學法語系副教授陸一琛和青年小說家宗城,為我們揭秘了這位新晉諾獎得主的創作與人生。
安妮·埃爾諾獲得諾獎是實至名歸嗎?

宗城稱自己早就預料到,安妮·埃爾諾終有一日會獲得諾獎。在他的諾獎推演名單中,法語區列了兩位女作家的名字,一位是埃萊娜·西蘇(Hélène Cixous),另一位就是埃爾諾。他提醒我們注意,雖然埃爾諾此前在中國知名度不算太高,但她在法國文壇其實是一位很有分量的作家。近兩年中國圖書市場中的兩本暢銷書也都提到了埃爾諾的名字,一本是法國社會學家迪迪埃·埃里蓬的《回歸故里》,另一本是薩莉·魯尼的小說《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所以今年埃爾諾得獎并不算一件爆冷的事情,甚至可以說有點眾望所歸,”宗城認為。
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一位女性,她的性別身份幾乎總是會引起人們的特別注意,尤其當她在寫作中著重強調女性的身體、親密關系和生活經驗之時。宗城認為,過度強調埃爾諾的女性身份——無論是褒義還是貶義——都有其偽善之處,它暗示了女人的政治性不具有公共性,或者說書寫女性生命經驗的部分與其他面向的生命經驗(比如階級)存在二元對立或高下之分。在他看來,埃爾諾在寫作中加入關于女性的性、身體和女性對日常生活的思索,其實是在挑戰這一種成見——女性的日常生活和親密關系,是否真的比男性關心的公共議題低人一等?

宗城還注意到,一種強烈的間離感,或一種永恒的跟不同群體之間的疏離感,也是埃爾諾的寫作特點。她拒絕被一種單一身份框定,而是在努力書寫不同場域之間的交叉性。“埃爾諾注意到,全球化時代以來出現了這么一批人,他們既是自己原有階級的反叛者,但又不能完全融入所謂資產階級或主流知識精英的生活,當她身處巴黎知識精英行業的時候,她覺得自己根本上還是一個來自小鎮或者郊區的姑娘。埃爾諾敏銳地發現了這種個人的間離性。”宗城說,“寫作是標識一個獨立復雜的個體,而不只是某一種身份或階級的代稱,她希望人們意識到每個人的塑造和養成是流動的。”
根據陸一琛的觀察,埃爾諾不僅是一位小說家,還是一位積極介入現實的公共知識分子。除了女性權益以外,她近年來也非常關注底層民眾的生活,在法國諸多著名報刊上發表文章聲援“黃馬甲運動”。陸一琛認為,在新冠疫情、戰爭、經濟衰退等因素造成大動蕩的年代,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一位極度關注底層民眾的作家,反映了諾獎的立場,即希望文學的受眾不再禁錮于資產階級文學審美,而能夠更多面向底層民眾,讓他們能獲得一種文學化的存在。
陸一琛同時指出,埃爾諾的寫作吸收了很多人文社科領域的養分——她是一位人文社科專著的熱情讀者,閱讀了大量人類學、歷史學作品,因此她的寫作始終抱有一種人文精神,會將人文社科理論與自己的生存經驗結合起來,去思考與許多人息息相關的宏大命題。因此,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埃爾諾,至少是認同她的寫作所反映的一種文學取向,即集體記憶作為人類記憶的重要性和局限性。“(寫作)《悠悠歲月》后期,她得了乳腺癌,覺得自己的生命可能要走到盡頭了,所以有一種非常迫切的書寫記憶的責任感。這種人生而向死的宿命感促使她不停地書寫。我覺得諾貝爾獎其實也是在鼓勵這種以人類記憶為目標的書寫,”陸一琛如此說道。

安妮·埃爾諾 著 吳岳添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1年
鑒于此,埃爾諾也是一位很難用所謂“純文學”去定義的諾獎作家,某種程度上來說,她與2015年諾獎獲得者阿列克謝耶維奇一樣,展現了非虛構寫作在文學領域能夠取得怎樣的認可。《衛報》的評論文章稱,傳統的小說家正在失去諾獎的青睞。陸一琛認為,對非虛構的重視其實反映出了虛構作品的某種困境,如今的小說家可能無法在敘事技巧上做出更多突破了。
在宗城看來,今天的寫作者都在探索一種混合型文體,正如托卡爾丘克在她的諾獎演講中提到,她希望探索出一種跳出傳統純文學范疇,混合不同學科知識的寫作形式。智利作家羅貝托·波拉尼奧也是一個例子:他在小說《2666》中融合了社會檔案、文學評論、犯罪記錄等等。隨著混合型寫作越來越成為一種趨勢,我們也需要重構“文學”這一概念。

宗城進一步指出,一種更加具有公共性的文學似乎已經是我們時代對寫作者的要求。“其實當初提出純文學的概念是有它的意義的,是為了打破意識形態政治對文學的裹挾,但現在的社會環境不一樣了。今天大家更迫切想要看到的,是文學重新回到公共生活,更加有創造力,更加混合。可能今天我們討論埃爾諾的創作,包括虛構與非虛構的融合,最后是激勵我們能否探討出一種更加具有創造力的、反映公共生活的文學。”
樸素的語言與多元的寫作手法
在中國有這么一種說法,埃爾諾是法語系學生特別喜歡的論文寫作研究對象,因為她的作品語言簡單易讀。陸一琛表示,埃爾諾的作品的確閱讀門檻不高——首先她出版的大多數作品都是很薄的、兩三歐元就能買到的小書;其次,她的寫作語言非常簡單,對于法語系的學生來說,到了大三大四的時候拿一本字典就能輕松地讀下去。
實際上,“簡單樸素的語言表達”也反映了埃爾諾的價值取向。陸一琛認為,在學校教育和個人閱讀的雙重塑造下,埃爾諾已經完美掌握了資產階級的語言,但她選擇了一種幾乎像是寫給父母的平實語言,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消融與父母這樣的底層讀者之間的階級隔閡。
宗城則認為,埃爾諾之所以選擇這種寫作方式,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她不認為寫作是一件完全獨立于社會之外的東西。“如果今天埃爾諾參與一場‘是否存在純文學’的討論,我覺得埃爾諾可能會質疑‘純’的概念——真的有一種純的、區分于意識形態和政治社會文化的寫作方式嗎?”
另外,宗城也提醒我們注意埃爾諾寫作方式的多樣性。“無人稱寫作”或“無人稱自傳”是埃爾諾標志性的寫作技巧,《悠悠歲月》就是她“無人稱寫作”的代表作。在這部作品中,她大量使用了富有法語特色的人稱代詞“on”——作為泛指代詞時,on可以表示一個或數個身份不確指的人,其指涉需要根據語境來確定。宗城曾與朋友討論過,他們認為埃爾諾的“無人稱寫作”實則是在表現一種為女性共同體所共享的潛意識,借此“回看曾經對一代人造成了深刻烙印的公共史和私人史”。
從寫作者的角度來說,宗城認為,無人稱寫作相比單純的第三人稱寫作還有另外一重好處,就是可以跳脫出“第三人稱敘述只能局限于敘述者個人的雙眼和心靈感受到的東西”這一束縛,作者能夠更心無旁騖地去書寫一代人的公共史。他指出,《悠悠歲月》作為一部埃爾諾寫作生涯中后期的集大成之作,她或許是想把之前很多作品的元素涵蓋進去,“無人稱自傳”的寫法就與這樣一部總結性作品比較匹配。
“清單式的寫作”也是埃爾諾的寫作特點之一,宗城和陸一琛都認為她受到了法國先鋒小說家喬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的影響。在《悠悠歲月》中,她用“物的堆積”在文字中再現了種種生活場景,并由此反映一種公共的歷史。在宗城看來,這也是一種結合社會學研究視角的、對一個人的生命塑造過程的剖析。
把階級躍升當作埃爾諾的寫作重心,恐怕是一種誤讀
埃爾諾是上世紀40年代生人,埃里蓬是50年代生人,但當下的中國讀者在閱讀他們的作品時往往能獲得一種深深的共鳴,甚至有讀者評論認為,他們寫的是法國版的“小鎮做題家”的故事。陸一琛認為,與其說埃爾諾是“小鎮做題家”,不如說她是“小鎮讀書家”,因為在法國高度強調思辨的高考制度下,寫作才是最能兌現文化資本的方式。埃爾諾雖然不像資產階級家庭孩子那樣享有充沛的文化資源,但她的父母的確在她身上傾注了最好的教育資源,供她上私立學校,不讓她做家務。而她自己也非常勤奮,通過如饑似渴地讀書積累文化資本,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在宗城看來,埃爾諾的成長經歷的確能引起很多中國年輕人的共鳴。他與一個文學圈外的朋友分享過埃爾諾的故事,對方表示,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底層女作家的故事——小地方長大的女生,如果要逃離性別不友好的家鄉,需要比男生付出更大的努力。這一點可能會讓很多人對埃爾諾非常有共鳴,也不難理解為何有人稱她為逆襲版的“我的天才女友”。

埃爾諾從工人階級躋身資產階級,過程中經歷的文化沖擊、疏離甚至是羞恥,也越來越能在焦慮日益嚴重的時代引發我們的共鳴。陸一琛與宗城都認為埃爾諾和當代年輕人所面臨的是頗為不同的時代境遇。陸一琛指出,埃爾諾完整經歷了法國的“榮光三十年”,享受到了戰后高速發展的時代機遇,比如她父母的經濟條件其實比我們想象得要好,他們送了一部車作為女兒的嫁妝。
宗城說,埃爾諾作品的最終導向不是“憤怒”,而是一種對自我記憶與歷史的回溯,這與當代年輕人的精神底色并不相同。根據宗城的觀察,當下的寫作者在描述年輕人的感受時著重強調憤怒感和饑餓感。這種憤怒感來源于兩個方面:第一,階級躍升的通道正在逐漸關閉,令年輕人感到局促和壓力,甚至產生淪為結構性“棄民”的感受;第二,年輕人彷徨于難以找到生活的意義感。
“雖然今天很多中文評論者把階級流動作為一個很大的主題,但在《悠悠歲月》中沒有占很大比重,埃爾諾要討論的是當時的一些政治運動,比如性解放浪潮以及女性生活的變化。”宗城說,“我自己其實比較懷疑階級躍升到底是不是埃爾諾的寫作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