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董子琪
編輯 | 黃月
“人到了一定年齡,就不再懼怕高級百貨的女店員了。”1915年,33歲的伍爾夫在日記中寫道,她在倫敦逛百貨商場,買了一條十便士出頭的藍色連衣裙,她覺得逛街非常快樂,記日記時也穿著這條剛買來的裙子。
伍爾夫在意她的衣著。下雨天去圖書館濕透的鞋子嘎吱作響,她自覺無地自容,被朋友嘲笑打扮土氣穿戴不合適又感覺備受侮辱,有時沾沾自喜自己的穿著時髦的流蘇斗篷和耳環令朋友眼紅,有時也抗拒不了店員的游說沖動購物。
在著名的女性文學演講《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里,仿佛為前人感到可惜似地,伍爾夫說簡·奧斯丁從未乘公共汽車穿過倫敦,從未自己吃午飯或逛商店,眼界過于狹小;勃朗特姐妹也只能是在田野上眺望一下遠方,缺乏生活經驗,因此未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天賦——伍爾夫批評夏洛蒂·勃朗特的寫作雖然富有才華,卻變形扭曲,在本該平靜的地方書寫憤怒,在本該描繪角色的地方書寫自己,這是因為她貧窮而受限,被真正的生活拒之門外。
伍爾夫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她自己就是一個獨自閑逛的女性,并從到處閑逛中受惠極大。女性已經在室內待了幾百萬年,她寫道,“創造力浸透了墻壁,遠遠超出磚塊和灰泥的容量。”散步不僅能放松心情還能促進構思,倫敦能夠帶給她一部戲劇、一部短篇小說和一首詩歌,她只須邁開腿穿越倫敦的街道即可。她尤其熱愛河濱漫步,曾在日記里記錄過一次冒險:在一個誰也不見的下午,她獨自乘公共汽車到南華克橋,走下通向河道的樓梯,穿過樓梯盡頭阻攔的繩索,在泰晤士河岸的石塊和電纜間游走,路過墻皮剝落雜草叢生的倉庫。這里有老鼠出沒,布滿綠色的稀泥、河水侵蝕的磚塊和潮水沖上來的紐扣鉤,寒風刺骨,她想起巴塞羅那的難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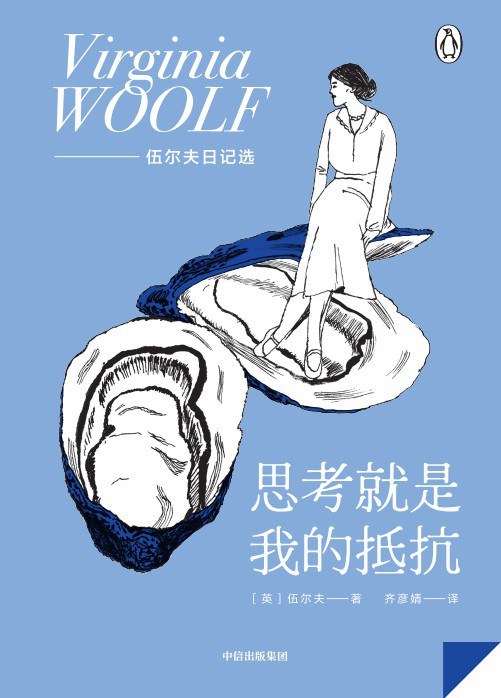
[英]伍爾夫 著 齊彥婧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2年9月
鎖門的圖書館

沖破繩索獨自漫游的女性形象,出現在伍爾夫的意識流小說《達洛維夫人》中。達洛維夫人的女兒伊麗莎白獨自乘公共汽車前往河岸街漫步,街頭漫游拓寬了她對自己的認知,也將她從身份中解脫,她不再是達洛維家的人,因為達洛維家的人不會天天來這里,她成為了一個開拓者、一個流浪女和一個冒險家。她同時也保持著高度警惕,因為她隨時有可能匯入別人的生活潮流之中——伊麗莎白向圣保羅大教堂邁開步子,就像一個偷偷潛入陌生房屋的人,生怕主人突然發現她的蹤跡。
伍爾夫穿過了阻攔她前往河道的樓梯盡頭的繩索,伊麗莎白走在大街上卻害怕主人突然冒出來將她拒之門外,這也如同對女性創作的比喻。在《一間只屬于自己的房間》中,伍爾夫將文學形容為一片開放的草坪,而對女性創作者指指點點的權威人士,就像是為圖書館上鎖的校官,他們對興致勃勃前來閱讀的女性說,“抱歉,女士只有在學院研究員的陪同下才能進入圖書館,否則就要出示介紹信。”伍爾夫鼓勵女性勇敢穿過校官的恐嚇,進入“文學的草坪”,就算他們可以鎖住圖書館,也鎖不住自由的腳步,這是任何大門、門鎖和門閂都不能阻攔的——她要做的只是忽略身邊的人,一心跨越自己的柵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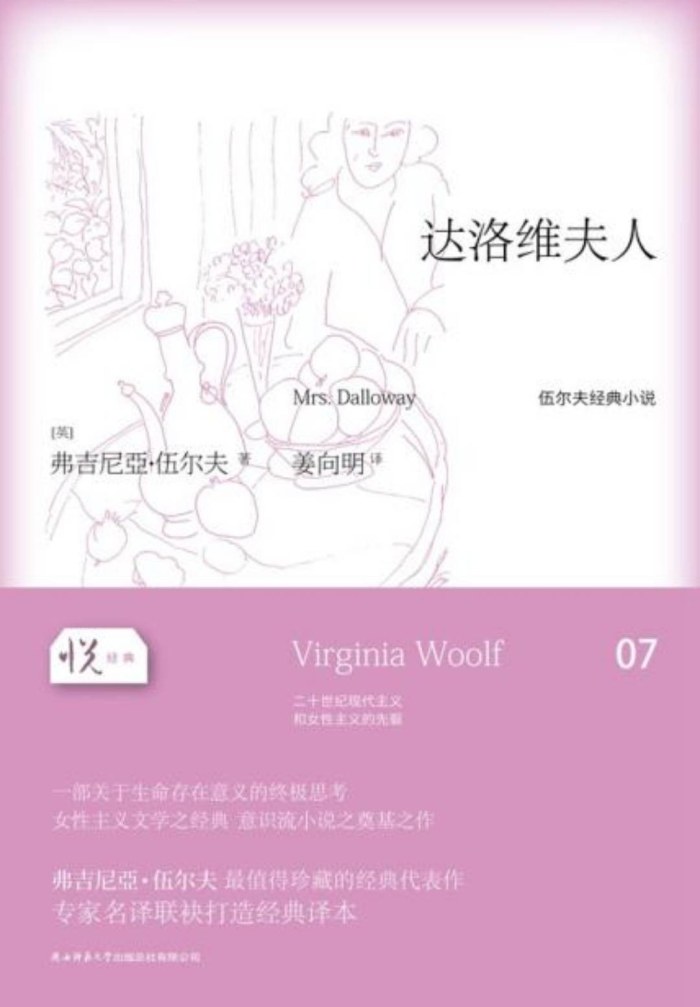
[英]伍爾夫 著 姜向明 譯
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4年
關于鎖門的圖書館,伍爾夫的日記顯示,倫敦圖書館并沒有對她關上大門,她常常前往圖書館,但確實遭受過圖書館委員會的拒絕。她的朋友向她透露,他曾試圖將她提名為圖書館委員會成員,但委員會以“女性都是不可理喻的”為由拒絕了。這一內情的披露讓伍爾夫感受到了極大的冒犯,她仿佛看到整份名單都被劃去,也似乎看到她的朋友怎樣提到她的名字,他們怎樣告訴他不行,絕對不行。被拒絕令她非常憤怒,但她自我安慰這些憤怒對她的寫作很有益,因為憤怒總會平息透明,她知道怎樣將這些憤怒變成優美、清晰、合理、諷刺的散文。她立志要在委員會拒絕她之前拒絕委員會,五年后,她的計劃實現了。
逛街文學觀
逛街的伍爾夫顯得生氣勃勃、富有熱情,事實上,逛街的伍爾夫也是寫作的伍爾夫。在《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中,伍爾夫以進入商店的女人比喻一種值得書寫卻被長期忽略的現實:
“我想象自己走進一家商店,店里鋪著黑白相間的地板,掛滿美得驚人的彩色絲帶,這幅光景同樣適合書寫,不亞于任何一座雪山之巔或者安第斯山脈的巖石峽谷。”
伍爾夫聲稱,為站在商店柜臺后面的女孩做傳記,其重要性不亞于為任何偉人作傳。為何如此呢?她相信,小說像一張蜘蛛網,看似在風中飄揚,卻連接著生活各個角落;蛛網不是懸在半空中的,而是與有形之物密切相關,比如健康、財富和居住的房子。
如此說來,商場柜臺和逛街漫步正是組成生活無數瞬間之一,商場和柜臺也能成為照見自己、認清自己與外界的關系的場合。要為倫敦街頭游蕩的女人記錄,要為站在商店柜臺之后的女孩作傳,伍爾夫是在對一種文學價值觀做出回應——這種價值觀認為,描述戰場的場景比商店里的場景更重要,他們說,“這本書很重要,因為它講的是戰爭。這本書不重要,因為它講的是會客廳里女人的感情。”在伍爾夫看來,這與足球和運動很重要、購物時尚是小事的邏輯一樣微妙而無所不在。

[英]伍爾夫 著 周穎琪 譯
果麥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年
經歷過一場低落后,伍爾夫有所領悟,人生的一大成就,就在于生命的珍寶都是深藏不露的,隱藏在平凡的事物中,就像乘坐公共汽車去里士滿以及在草地上抽煙,以至于沒有什么能夠傷害它們,也沒有什么動蕩能擾亂這種幸福。我們不應當將這種感受理解為伍爾夫對生活志得意滿,實際上,她長期受到抑郁的侵襲,并處于即將開戰的惶惑中,其重點在于以微小的樂趣抵抗傷害。
二十多年后,她在戰斗機出沒的夜晚想象河濱漫步,以使自己放松神經:
“我該想些什么呢?河流吧,比如倫敦橋下的泰晤士河,買一本筆記本,再沿著河岸街漫步,貪婪地觀察每一張面孔。”
遺憾的是,深藏的生活樂趣并非無可動搖,二戰中的倫敦開啟了燈火管制,和平時期的日常習慣成為了奢侈,戰爭將要通過摧毀散步風景的方式威脅她,對于倫敦巷道的破壞激起了她內心受到壓抑與懷疑的愛國情:“我愛步行前往倫敦塔,那就是我的英格蘭。”假如一枚炸彈摧毀了倫敦的一條小巷,摧毀了帶黃銅束帶的窗簾、河流的氣息和正在看書的老婦人,她的強烈感受將不亞于一個真正的愛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