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當地時間9月13日,22歲的庫爾德女性阿米尼因頭巾佩戴不當在德黑蘭被警察逮捕,三天后死亡,死因是頭部嚴重受傷。她的死亡引發了伊朗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截至9月25日,抗議依然在發酵。近年來,伊朗多次爆發大規模抗議,但與此前抗議多關注政經問題不同,本次抗議的重點是保護女性權利和公民個人自由。
對女性行為舉止、著裝打扮的嚴苛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我們對伊斯蘭世界的印象,而伊朗與許多其他中東國家不同的是,伊朗曾在20世紀中葉實現過較深程度的世俗化(得益于伊朗王室巴列維國王的支持),中文互聯網內也曾流傳過1979年革命前穿著打扮非常西化的伊朗女性出現在城市街頭的照片。因經濟發展乏力、國內矛盾激化,1979年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王朝,并在伊朗建立了一個伊斯蘭共和國,革命的最大推手、意識形態導師和受益者是宗教領袖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伊朗女性的社會地位、個人權利自那時起急轉直下。

近半個世紀后回望1979年革命,我們不難發現其中鮮明的“反西方”元素。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艾愷(Guy S. Alitto)認為,伊斯蘭的文化民族主義者多為宗教性人物,霍梅尼的突出之處在于,他發起的革命及其主張更深更廣地排斥西方個人主義、資本主義和物質主義——它們在理論上與伊斯蘭的公有主義與精神主義對立。事實上,艾愷在《持續焦慮》一書中指出,發生在伊朗等中東國家的“宗教-保守主義勢力復辟”不過是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的在地表現形式之一。縱觀全球,發端自西歐的現代化在帶來科學技術發展和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也引發了種種現代性焦慮,文化民族主義是其他地區的回應形式之一,“在任何文化或國家,只要是它面對現代化的民族國家的軍事力量與經濟優勢,而被迫為自衛向外做文化引進時,不可避免地就要發生。”
伊朗的1979年革命就是這種現代性焦慮的反應。英國學者邁克爾·阿克斯沃西(Michael Axworthy)在分析為何1979年革命有如此深的反西方印記時指出,形形色色的態度與動機慢慢匯聚成一股反西方潮流:19世紀以來西方殖民主義給伊朗人民留下的歷史創傷、西式教育和西式生活方式對保守主義者的強烈冒犯、年輕單身男性在面對就業機會匱乏和看似享有更多自由余裕的年輕城市女孩時被喚起的強烈焦慮與嫉恨……
阿克斯沃西同時指出,1979年革命之后伊朗女性的命運并非如外部觀察者所預想的那般黯淡,得益于伊朗社會存在的對于學習和知識素養的潛在文化尊重,女性和男性一樣被鼓勵接受教育,其中不少女性在受教育階段就脫穎而出,至少在中產階級當中,已經出現了“女性一代”——在教育部門、神職崗位、私營經濟、醫藥領域和國家公務員隊伍中都存在著大量女性。“一些伊朗女性社會地位的轉變必將會對伊朗社會和政治產生更廣泛的長期影響。”阿克斯沃西寫道,如今正在伊朗發生的大規模抗議或許正體現了這一點。
《伊朗:被低估的文明與未完成的變革》(節選)

撰文 | 邁克爾·阿克斯沃西 翻譯 | 趙乙深
01 哪些因素誘發了1979年革命?
不同于政變或能夠給政治帶來些許改變的小型事件,革命意味著翻天覆地的劇變。革命并不僅僅是替換個別人員,還會改變整個政治集團和社會階層;不僅會改變國家政策或者政治綱領,還會改變整個政府體系、意識形態、國家憲法、公共準則;這種改變不會僅持續三到五年就消失,而是會持續幾代人甚至影響全球范圍。
根據以上標準,1979年伊朗革命完全可以比肩1789年法國大革命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但是,發生如此重要且具有如此規模的事件絕不可能只出于簡單的理由。解釋革命緣起的復雜性往往會引發爭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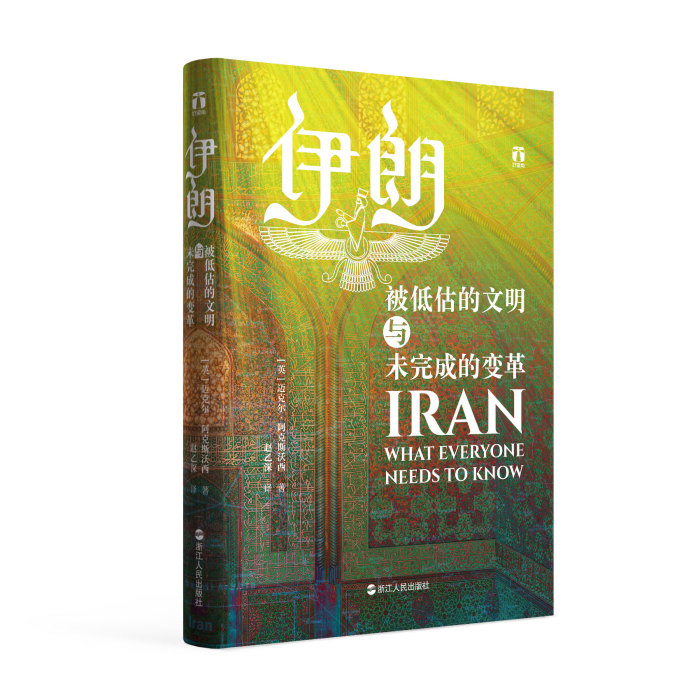
[英]邁克爾·阿克斯沃西 著 趙乙深 譯
好望角·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1-12
幾個不同社會團體和政治團體參與了1979年伊朗革命,他們參與革命的動機各不相同。有一種說法是這些團體在霍梅尼的領導下聯合起來,共同反對國王。然而革命成功后,這些團體發生利益糾紛,一些人感覺被新建的伊斯蘭共和國背叛了。所以,時至今日,在描繪革命發生的原因和整個過程時出現了幾個被廣泛認可的版本,這些說法各異且彼此相互矛盾。一個較為穩妥的觀點是這些說法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這也就意味著革命是由多種因素相互交織所引發的。
革命爆發的一個明顯原因是國王長期沒有給他的子民提供實現政治抱負的機會。1953年后,老一輩伊朗人對此已懶于改變,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新一代伊朗人登上舞臺,其中一些深受60年代風靡歐洲和其他地方的激進學生運動與暴力革命的影響。伊朗革命的一個重要團體就是由世俗左派學生組成的,他們甚至比其他團體更激進。其他參與人士還包括老一代左派人士、同情人民黨人士、摩薩臺國民陣線的支持者。有很大一部分受過教育的伊朗人仍然追求立憲主義和1906年制定的憲法原則。
另一個原因是國王刻意疏遠教團,霍梅尼是最極端的一個例子,但其他教士對于國王所倡導的全面西化、世俗改革,對前伊斯蘭時代伊朗王室的淵源的強調以及伊朗各個城市蓬勃興起的西式物質享樂主義等也充滿憤恨。和以往一樣,與教團緊密結盟的是小商販和工匠群體,他們對于經濟模式的改變十分不滿。國內鄉村地區開始出現新興超市和進口食品,導致了經濟模式的改變,這種改變將他們從傳統經濟活動的中心地位推到邊緣位置。這其中的許多人,特別是小商販們的生活被伊朗復興黨完全攪亂。起先,他們以為只要安安靜靜地經營自己的生意,復興黨政權就會放他們一馬,然而復興黨卻要一竿子插到底,將改革措施直接指向社會最基層的普通人的生活。在1976—1977年的通貨膨脹引發的價格飛漲(堪比1905—1906年通貨膨脹)的過程中,有大批小商販因所謂的投機倒把而遭到逮捕。除了小商販和宗教學生與教團緊密相連之外,還有一個團體同時與宗教支持者和立憲派人士關系密切(即自由運動,雖然規模小,但是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還有兩個極端學生群體:其中一個為伊朗人民“圣戰”者組織(Mojahedin-e Khalq Organisation, MKO),它試圖融合伊斯蘭教與馬克思主義;另一個則更加左派激進,即伊朗人民敢死游擊隊(Fedayan-e Khalq)。

引發革命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人們對于當地社會經濟狀況的長期不滿。土地改革造成的社會動蕩和混亂,使得大量貧窮、未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涌向德黑蘭尋找工作。伊朗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和中期經歷了短暫的上揚后,在1976—1977年開始下滑,在收入下滑和失業率上升的雙重壓力下,物價和房租卻依然逐步走高。有證據顯示,伊朗城市貧民在革命初期并未過多參與其中,但到1978年秋,工人的作用開始變得重要起來,他們的罷工游行嚴重阻礙了經濟和政府的正常運轉。經濟下行使得所有社會階層都開始感到不安并越來越多地抨擊政府。國王個人統治和單一政黨國家的顯著弊病就在于一旦情況發生惡化,根本沒有替罪羊來分擔責任。
導致革命爆發還有其他因素,一些已經在前面提到過,比如國王與人民之間漸行漸遠,且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和英美政府的一系列行動才是對于他本人統治的主要威脅。但他的判斷與事實可謂背道而馳。再有就是國王的病情。國王在20世紀70年代得了白血病,并且病情日益惡化(最終在1980年流亡期間死于此病)。
即使說了這么多,仍然無法完全解釋革命為何會發生,因為只有通過敘述解釋了事件發展的先后順序和應對這些事件的方式,才能闡明國王是如何一步步失去權力,以及革命為何變得勢不可當。
02 為何這場革命有如此深的反西方印記?
就革命本身而言,各種形形色色的態度與動機慢慢匯聚成一股反西方潮流。伊朗國內對于過去長久以來西方介入伊朗的深惡痛絕占據了更為重要的位置,無論是從19世紀以來西方占據伊朗領土并對國家百般羞辱,還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西方打破伊朗保持的中立并侵犯其主權。此后,西方于1953年策劃的政變使這種對西方的憤怒情緒達到頂峰。然而與之矛盾的是,許多伊朗人卻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人民懷有一種親近感甚至是崇敬感。在那個時代及以后,革命者們常說伊朗人的敵意并不針對西方國家的人民,而是完全針對西方各個國家的政府。產生這種復雜情緒,部分是緣于一種屈辱的失望感。許多受過教育的伊朗人對西方尤其是對美國頗為失望。他們認為,這些國家理應成為伊朗的朋友,并一再以朋友自居,但卻屢次辜負了伊朗人對他們的信任。

對于受西式教育和西方思想影響較少的更為保守的伊朗人來說,電視媒體和大街上各種撲面而來的西式廣告、電影和服裝給他們帶來的直觀感受是令人厭惡的,他們對于這些西方元素給伊朗宗教和文化傳統帶來的影響也麻木不仁。許多人因為美國廣告媒體的大規模轟炸而感到迷茫,并覺得受到冒犯。當時在伊朗居住著大量外國僑民,尤其是美國人(20世紀70年代末期,數量多達約5萬)。雖然也有例外,但總體來說伊朗人感覺美國人在當地表現得傲慢自大,且毫不在意當地人的感受。從某種程度上講,伊朗人在自己的國家,特別是首都德黑蘭,反而感覺像是外國人。霍梅尼也在1979年的一篇講話中提道(講話雖發生在革命之后,但霍梅尼本人的思想還停留在革命前的狀態),西方將他們所標榜的自由強加到伊朗人民頭上只是為了讓伊朗人更好地受西方控制。
這些人渴望自由,渴望我們的青年也得到自由……但是,他們渴望的是怎樣的自由?……他們希望賭場自由開放,酒吧自由開放,聲色犬馬場所自由開放,吸食海洛因者隨意吸食,抽鴉片者自在抽吸,這就是他們用來閹割我國青年人的手段,使青年再也無力起來反抗他們……這些偽民主派受到那些想要掠奪我們、使我們的青年麻木不仁的西方列強影響,倡導絕對自由,即在任何情況下任何事情都不應被禁止的自由。
20世紀70年代德黑蘭存在的另一個突出問題是對性的焦慮和怨恨。當時的德黑蘭充斥著年輕男性,除一些學生外,還有大量的進城務工人員。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來自鄉村和外省城市家庭,其中一部分找不到工作,另一部分只能從事低收入工作勉強度日。他們生活在城市南部,大部分人都處于貧困狀態,在那里女性都穿著伊斯蘭傳統罩袍。但在城市北部,他們卻能見到年輕女性獨自外出,穿著招搖,盡顯西式時尚。這些女性身上同時表現出財富、傲慢和西方的影響。他們還能在廣告中和電影院前的宣傳板上不時看到女性的形象。這一切對他們來說都是那樣使人饞涎欲滴卻又高不可攀,好像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他們自身令人絕望的劣等身份。他們沒錢結婚,更無力組織家庭,由于成長過程中嚴苛的宗教影響以及與外來時尚形象的格格不入,他們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欲望的破滅與社會緊張情緒以及對西方影響的憤恨心態已經相互交織。

此刻,這種復雜矛盾的情緒隨著20世紀60年代學生激進主義、反越戰運動等舶來品言論被不斷放大并逐漸成形,特別是在左派學生和青年一代當中。但是,許多在上一代就應該轉向左翼的年輕伊朗人在70年代卻轉向伊斯蘭教,并認為這才是一個真正的伊朗人的自我身份的核心。
03 1979年以來,伊朗社會中女性地位有何變化?
伊朗的女性地位問題自1979年革命以來就充滿了矛盾(甚至要比伊朗社會其他領域更為嚴重),如果沒有與之相反或者近乎相反的陳述以作平衡,就幾乎不可能對此問題作出任何強有力的陳述。如果想要了解當代伊朗以及伊朗未來的重要發展趨勢,至今幾乎還沒有其他哪一個復雜現象的重要程度能與這個問題相提并論。
要論述這個問題,需要從霍梅尼開始。霍梅尼對于女性地位的立場既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又具有多變性。1963—1964年,當他剛剛以反對國王而出名時,他曾抨擊國王給予女性投票權的政策(卻沒有批評自己的土地改革的相關計劃,土地改革在農民中大受歡迎,卻損害了教士的土地紅利)。但是到了1979年,霍梅尼承認女性在推翻國王過程中作出了相應的貢獻,他決定不再違背歷史潮流,從而保留了女性的投票權。然而,他卻重新引入女性需要佩戴面紗的制度,取消了國王在1967年推行的《家庭保護法》中有關自由化的規定,并再次強調沙里亞法相關條款應發揮其作用以及家庭中男性至上的原則。這就意味著,除了別的權利外,女性一旦離婚就將失去孩子的監護權;在司法案件中,女性證詞的重要性將不及男性,諸如此類。這導致女性不再可能從事法官或者律師等職業[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于1975年成為伊朗首位女性法官,卻在1979—1993年期間無法再從事自己的職業。多年后的2003年,她以伊朗人權律師的身份成為該國首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然而,取消《家庭保護法》所引發的其他變化,例如在理論上重新將一夫多妻制合法化,以及將女性法定結婚年齡下調至9歲(后又上調至13歲),卻并沒有真正起到多大作用,因為全社會都以此為恥。
伊斯蘭共和國在建立之初的幾個月里對女性地位作出的許多改變,使得許多伊朗女性,尤其是但不僅僅限于那些曾積極參與1978年抗議示威活動的左派女性,痛苦地感覺到自己遭遇了革命的背叛。盡管如此,從長遠來看,其他變化對于女性來說同樣重要或者更為重要。兩伊戰爭就是其中一個因素。當男性上前線作戰時,女性就在工作中或者家庭里承擔了男性的角色。教育領域所發生的變化也引發了其他一些重要改變,而這些改變卻往往得不到外界重視。

由于高出生率和快速增長的人口,以及巴列維政府犧牲農村以換取城市發展的偏頗政策,巴列維國王從來沒有在全國范圍內普及全民初等教育。而在伊斯蘭共和國體制下,即使是最偏遠的鄉村也至少有一所學校,在幾年的時間里,所有兒童都有希望接受基礎教育。伊朗識字率迅速攀升,在2015年達到86.8%。與此同時,許多來自更為保守的鄉村地區和外省城鎮地區的家庭(家庭里的父親)破天荒地樂于將自己的女兒送入學校,因為學校根據性別將學生進行分離,而且女孩(從9歲開始)上學期間必須穿著希賈布。男孩和女孩上學開始成為日常,許多家庭要求子女去取得盡可能優異的成績,在學校接受教育直到18歲,然后進入大學繼續學習,這體現了伊朗社會存在的對于學習和知識素養的潛在文化尊重。政府對上大學持鼓勵態度,在兩伊戰爭后的幾年時間里,一大批大學和自由大學(獨立于政府財政支持,依靠學生學費自給自足的大學)在各省相繼建立。
在此之際,伊朗出現了同西方國家中學教育階段相類似的現象——伊朗女孩在青少年階段的學習中表現得更為勤奮,考試成績也相對優異。這也使得女孩在大學入學考試中分數更高,所以在(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很多年里,大學錄取學生中60%—65%為女性。緊接著,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女性離開大學,進入勞動力市場(盡管伊朗年輕人失業率之高令人淚目,年輕女性失業率甚至更高),多數人都能找到優渥的工作。在教育部門、神職崗位、私營經濟、醫藥領域和國家公務員隊伍中都存在著大量女性(當今超過一半的伊朗教師是女性)。
伊朗女性地位的提高,可視為教士集團成功掌握伊朗政治和決策權所帶來的一種結果。教團是伊朗傳統的知識分子階層。如果伊朗國內還有哪個階層能毫無保留地將教育本身看作是一種優良品質的話,那必是教團無疑。女性接受更高水平的大眾教育,以及更廣泛地進入職場本身就是這種潛在觀點的一種體現。同時,女性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也引發另外一些現象。在伊朗許多家庭中,妻子的收入高于丈夫,更高的教育水平就意味著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有更多的選擇。一般來講,女性結婚時間有所推遲,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在選擇婚姻對象時左顧右盼,甚至干脆選擇不婚。一些觀察人士注意到,在中產階級女性中所發展出的關于家庭、職場和政治的自由派觀點與女性自信心的提升和收入能力的增強存在密切關系。其他觀察人士,特別是齊巴·米爾胡塞尼(Ziba Mir-Hosseini)和查爾斯·庫茲曼(Charles Kurzman),都提到伊朗進入了“女性一代”的觀點。
當然,人們也不應該對此過分夸大。以上現象大部分只出現在中產階級女性中,大多數底層女性甚至不敢幻想能夠找到一份收入良好的工作,她們仍然需要面對高失業率、不公正的性別歧視、極度貧窮等殘酷現實,以及毒品、賣淫、家庭破碎等問題給她們帶來的無法挽回的傷害。相當數量的女性仍然無法在國民經濟各個領域中晉升到管理崗位。近年來,政府中仍有人試圖在部分大學課程限制女性上課名額(截至目前,這種限制所產生的效果還不明顯)。法律上的不平等待遇對于伊朗實現女性平等的合法愿望來說真可謂是一個持久且恥辱的污點。

然而,一些伊朗女性社會地位的轉變必將會對伊朗社會和政治產生更廣泛的長期影響。從宏觀層面上看,盡管社會還存在很多黑暗面,但這種變化是伊朗社會光明前景的特征之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人保持謹慎樂觀態度。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伊朗:被低估的文明與未完成的變革》第四章與第六章,內容有刪節,經出版社授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