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法國大革命之后,從君主立憲制、共和制、革命專政、帝國、王朝復辟,政體不斷變化。大革命之后什么才是法國?即“自法國大革命這一基本事件以來民族特性是如何構建的?”就成為莫娜·奧祖夫“革命·文學·女性三部曲”的核心問題意識。本文梳理了三部曲之一《女性的話語》中不同時段的法國女性的生命經歷和個性、觀念,從她們或堅持信仰,或在新舊之間掙扎,或彰顯女性權利,或尋求兩性對話等豐富多元的思想特征,來認識法蘭西社會本身含混多重的性格。
《法蘭西的女性世界》
文 | 王英(《讀書》2022年9期新刊)
“女性的畫像屬于一種男性題材。它鮮有出自女性之手,也極少關心她們的話語。”奧祖夫在《女性的話語:論法國的獨特性》中開宗明義,她要改變龔古爾兄弟、米什萊這些男性史學家筆下那些刻板的女性模本,大量女性研究似乎都更傾向于規定女性的角色和義務,確定女性形象的規范和標準,對不符合典范的部分加以修改、擦拭和模糊處理,而不關注她們自身的說法和道理,傾聽她們自己的聲音。或許作為女性學者,奧祖夫更有能力和意愿詮釋女性這一含蓄而又意味深長的存在,對她們的命運給予更具同情性的理解。

奧祖夫并未令人失望,她如同一個高明的獵手,在浩如煙海的文件和檔案中,揀選出法國歷史上十位女性來探索她們的世界,通過書信、小說、回憶錄和政論文章的梳理和重構,描畫出一幅幅風格各異的圖像,令那些逝去的人物容貌和靈魂宛若新生。她也如同一個優秀的攝影師,在最能展現人物特點的那一刻按下快門,捕捉到每一個人最為幽深微妙的那一面:瑪麗的固定不變、瑪儂的英勇無畏、熱爾曼的焦慮不安、奧羅爾的寬宏大度、于貝蒂娜的執拗、加布里埃爾的貪婪、西蒙娜的渴望。經過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兩百多年的巡禮,法國女性世界如同巨幅畫卷逐漸鋪陳開來,最終這一畫卷超越了性別的含義,如同湍急的支流匯入大海,而成為法蘭西民族的象征。
一、從舊制度到大革命
哈貝馬斯曾經盛贊歐洲的沙龍文化,“在婦女主持的沙龍里,無論是貴族的,還是平民的,親王、伯爵子弟和鐘表匠、小商人子弟互相來往,沙龍里的杰出人物不再是替其庇護人效力,意見不受經濟條件的限制”。十七、十八世紀的法國沙龍是時代思想和風尚的引領者、公共生活的象征,沙龍女主人學識豐富,精通拉丁文、哲學、歷史、幾何學、物理和化學等,這里性別、等級、階層、國界都變得不再重要,只要遵守一定的禮儀和規則都可以進入。迪·德芳夫人瑪麗就是沙龍女主人的典范,她每天下午接待圈中密友,盡可能長久地留住身邊的簇擁者,達朗貝爾和伏爾泰都是她沙龍的座上賓。她和伏爾泰保持了幾十年的友誼和通信,交換著關于信仰、理性、品味等諸多事物的意見。伏爾泰深信啟蒙能夠戰勝蒙昧和愚昧,而瑪麗則判定伏爾泰將他的才華浪費在反對教權的斗爭,她相信皈依宗教有著積極意義,有信仰的人生才是最為穩妥的人生。晚年她已經雙目失明,但去世前幾天里還興奮地記錄著賓客的人數、收到的信件,操心安排晚餐。瑪麗博學多才,擁有確定的判斷力,容忍自身的脆弱和缺陷,她或許抱怨人類普遍的不幸和悲慘境遇,卻從不認為作為女性有什么特殊的制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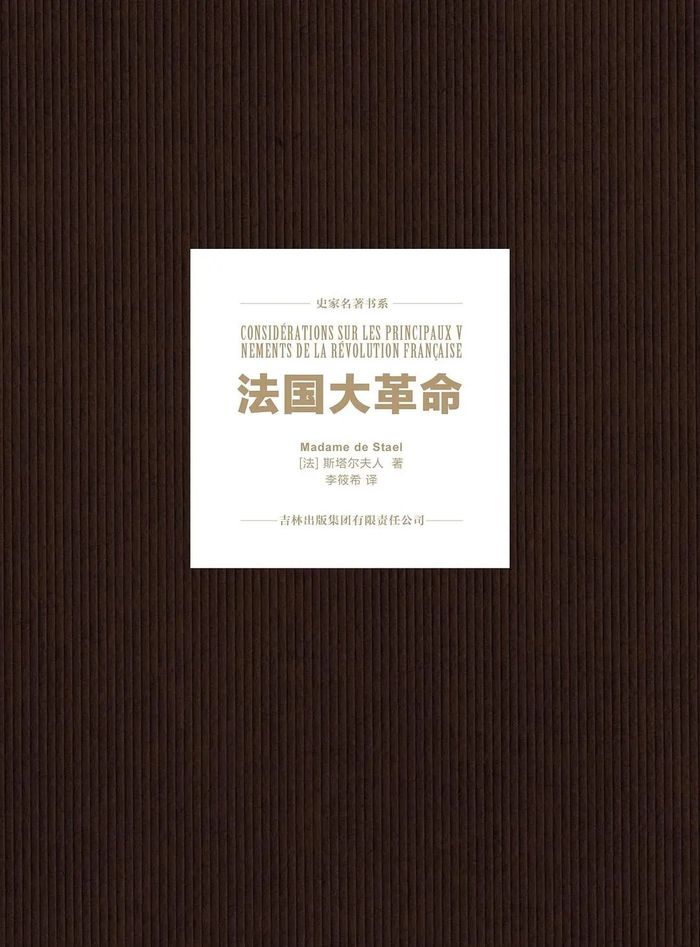
瑪麗在一七八〇年告別人世,舊時代也在幾年之后戛然而止。奧祖夫書中選擇的四位女性都或多或少地卷入法國大革命的風暴,德·沙里埃夫人、德·雷米薩夫人、羅蘭夫人,特別是斯塔爾夫人,她豐富的政治論文和文學作品,構筑了革命時代女性生存豐富而矛盾的藍本。作為路易十六財政大臣內克爾之女,斯塔爾夫人直接卷入到大革命風起云涌的上層權力博弈中,一七九五年她完成了《論國內和平》,試圖對大革命之后法國秩序重建給出自己的解釋,她反對保皇黨復辟舊制度的企圖,也反感雅各賓派過于激進化的革命,認為人們不應該被狂熱革命的激情裹挾,各派力量應該謀求一個溫和、理性的立憲政府,寬容并善于妥協是利益政見不同的派別能夠協商的重要品質,也是危機重重的法蘭西獲得秩序的必要條件。經過和父親內克爾深入討論和廣泛閱讀,斯塔爾夫人在一七九八年完成了《論當前形勢下如何結束革命和鞏固共和國》,嘗試從英國憲政中尋求靈感,幫助熱月黨人完成了較為中庸和具妥協色彩的共和國憲政設計。
那么大革命帶給女性的命運怎樣?對于雅各賓派而言,只有一種至高無上的感情,那就是對共和國的愛,為了公眾利益和祖國可以毫不留情地犧牲一切,包括婦女們對家庭的興趣、私人情感和宗教信仰。斯塔爾夫人意識到了這些至關重要的變化,《論法國大革命的主要事件》中,她清楚表明革命對女性的不友好,啟蒙時代婦女主持的沙龍已經被革命會議殺死,舊制度下的性別混雜等同于無秩序、墮落和陰謀,女性曾經擁有的生存空間被革命逐漸侵蝕。《對瑪麗-安托瓦內特的辯護》中,斯塔爾夫人確定無疑地指出,革命鑄就了一個恐怖時代,其殘酷兇狠給了女性致命一擊,瑪麗王后走上斷頭臺,所有女性都與這位美麗溫柔的母親一起遭到殺害。雅各賓派在女性身上看到的是天生的反叛者和敵人,其做法是將私人領域公共化,將家庭納入革命范疇之中,婦女們獲得自己的價值,但是僅僅是作為公民的妻子或母親。大革命帶來的兩性之間的隔閡影響了未來一個世紀,女性主持的沙龍銷聲匿跡,女人成為反動天主教會的支柱,藏匿教士并庇護暗中舉行的彌撒,她們被排斥在選舉權之外,成為共和國不值得信任的人。

對斯塔爾夫人來說,這是一個過渡的時代,舊制度下儀表、風度、信仰和生存模式已經漸趨消亡,政治和性別平等的新時代還是遙不可及的遠景。一八〇二年之后,在被拿破侖強制流放的歲月里,她創作了一系列以女性命運為中心的小說,《黛兒菲娜》或者《柯麗娜》的女主人公都有著法國數學家索菲·熱爾曼的影子,她們一生都在舊制度和大革命之中掙扎,也一生都搖擺于榮譽和愛情之間,她們為發展自己的天分辯護,但是享有自由意味著承受世俗偏見、政治打擊和無盡孤獨,無論斯塔爾夫人還是她的女主人公們都付出了巨大代價,其悲劇性的聲音穿過大革命的厚重霧靄,依然回響于法蘭西的天空。
二、十九世紀的側影
以賽亞·伯林曾經就思想家、作家和各類知識分子的氣質做過一個分類:一邊的人凡事歸系于某個單一的中心見識,一個多多少少連貫密合條理明備的體系,他們將一切歸納于一個單一普遍的原則,他們的人、他們的言論,必唯有本此原則才有意義;另一邊的人追逐許多目的,而諸目的往往互無關聯,甚至經常彼此矛盾,他們的生活、行動與觀念是離心的而不是向心式的。前一種思想人格和藝術人格屬于刺猬,后一種屬于狐貍,這項研究后來轉化成耳熟能詳的諺語,“狐貍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法國十九世紀女性世界便是這兩種氣質類型的混合,最能成為這個世紀寫照的則是老狐貍喬治·桑和大刺猬于貝蒂娜。

喬治·桑毫無顧忌地認同自己的女性氣質,“我同其他女性一樣,體弱多病,驕躁易怒,充滿幻想,極易感動,并且作為母親無謂地擔心”;她毫不猶豫地承認甘愿為了愛情而服從,她借小說《印第安娜》主人公之口說出,“控制我,我的血液,我的生命,我的整個身心都屬于你。帶我走吧,我是你的財產,你是我的主人”;她將母性情感定義為女性最獨特之處并為此而驕傲,甚至在她與繆塞、肖邦的兩段戀情中,她都會將情人像孩子一般地疼愛和照顧。但如果將她的形象固定為脆弱服從的女性,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沒有誰比喬治·桑更不愿意將自己固定為某種“特定的模式”,她就像一只狡猾的狐貍不斷變化外形,讓你迷惑于她到底是誰,她穿戴著男式西裝、寬大的領帶和灰色帽子,踏著黑色長筒靴走在巴黎街道,口中叼著雪茄和煙斗,自我指稱時隨意使用陽性和陰性,還有著男性化的名字“喬治”,她獨自住在巴黎過著和男性一樣的創作生活。繆塞稱她為“我所認識的最女性化的女性”,而她則跟朋友說,“把我當成男人或女人,悉聽尊便”。
喬治·桑的“狐貍屬性”,她的含混性、矛盾性和多重性體現在諸多方面,她的祖母是波蘭王室的后裔,而母親是一個普通鳥商的女兒,她在祖母莊園長大并接受貴族式教育,成長過程中卻被母親的浪漫主義民主理想所打動。一八四八年她站在民主派一邊,創辦了革命派的報紙,撰寫文章支持“二月革命”,但她完全禁止兒子莫里斯參與街壘活動。她對于女性主義運動亦持調和的態度,相信人類種族和性別上的平等,支持婦女爭取自己的權益,但在喬治看來,爭取婦女選舉權的做法是本末倒置,也是一個倉促的錯誤,如果婦女都沒有在婚姻中獲得獨立,取得受教育、財產和離婚的平等權利,又怎么指望她們代表人民參與政治事務?一八四八年“六月革命”的失敗更讓她看清楚了這一點,人類事務的變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過于超前的政治訴求會帶來更大的傷害,要學習妥協、等待和循序漸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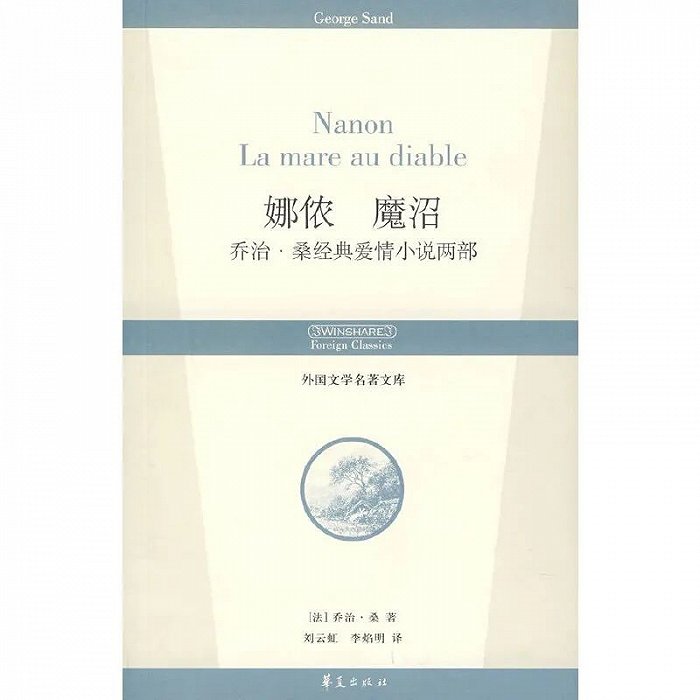
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后,喬治·桑回到了貝里,在隱居和創作中度過晚年。同一年于貝蒂娜出生在阿列省一個共和主義家庭。她二十四歲移居巴黎,從一個簡樸的套房搬到另一個,墻上始終掛著喬治·桑的畫像,然而她和變化多端的喬治實在是精神氣質的兩個類型,她擁有一種狂熱的一元識見,是毫無疑問的“刺猬屬性”。于貝蒂娜在二十歲左右思想就奇特地定型,她心中有一個不可動搖的神圣形象:女公民和女選民,終其一生都是為這個固定信仰而奮斗,經歷無數痛苦而百折不撓。她爭取婦女政治權利有幾種主要手段:給參議院、眾議院、部長、將軍、大臣、作家們寫信和申辯;收集簽名和請愿,參加游行甚至卷入暴力示威活動,到大街、廣場、市政廳要求將女性登記為選民;創建自己的機關報,她創刊了《女公民》并且撰寫了大量文章,反復重申同樣的主題。為了女性公民選舉權,于貝蒂娜忍受了逮捕、查禁、貧窮、獨身、愛人的死亡,她犧牲一切、付出一切,乃至于開罪一切,甚至不惜和共和主義的敵手聯盟,和保皇黨、反革命的教士或激進社會主義者結盟,戰斗的生活使她四處樹敵備受侮辱,執拗不討好的性格更加深了她的孤獨。
法蘭西的十九世紀是動蕩歲月,帝制和共和如拉鋸一般來回撕扯,不同集團、階層乃至性別之間都彌漫著濃厚的敵意,革命浪潮此起彼伏,稍有不慎就會劍拔弩張硝煙彌漫,因為喬治·桑,這個世紀的側影稍微帶上了一絲寬厚和溫情。十九世紀也是一個緩慢變化轉折的時代,女性逐漸在家庭、教育、政治等方面獲得平等權利,幸虧有了于貝蒂娜,一向被漠視的女性在商店、工廠和車間開始贏得微不足道的權利,選票也成為她們保護自己的一個途徑。
三、在科萊特和波伏娃之間
一九五四年科萊特去世,教會拒絕為她舉行天主教葬禮,然而法蘭西共和國接納了自己的女兒,為她舉行了隆重的葬禮。科萊特有一系列令人目眩的標簽:大作家、同性戀者、脫衣舞女演員、法蘭西時尚代言人。但女性這個身份對科萊特具有決定意義,她拒絕模仿男人的形象,不斷抗議時代將男性化角色強加給女性,自由意味著對于女性稟賦的接受、深化和贊美,自由在于堅持不懈地成為自己,回歸女性的使命和天賦。科萊特的生活和作品中,女性都是更有智慧和力量的存在。在《流浪女伶》《桎梏》《麥苗》《葡萄卷須》這些小說里,科萊特沉溺于描繪那些擁有力量感的女人。這些女性擁有男性所沒有的膽量、勇氣,面對不幸有非凡的抵抗能力,她們還擁有不放過任何人尤其不放過自己的無情目光,毫無粉飾地評估世界、貪婪和計算的能力,女商人一樣的精明和誠實。而她小說里的男性呢?其才能微不足道,平庸而脆弱,經常因為無足輕重的挫折就倒下了。科萊特作品如此,生活亦如是。她的父親是一個沉湎于幻想的退伍軍人,做著不切實際的文學夢,卻沒有在本子上寫下一個字,而母親茜朵是一個不屈不撓的典范,為自己和孩子們建造了一個堅固的生活堡壘;她的丈夫威利竊取了妻子的小說署上自己名字,這樁丑聞最終以離婚而告終,而科萊特一生中最真摯的愛情給予了貝爾伯爵夫人米茜,雖因世俗壓力被迫分離,但終其一生科萊特作品里女同性戀的愛情總有著不同尋常的深情,帶給人別處沒有的純粹和安全感。

背對宏大,面向近處。遠離荒謬而混亂的政治世界,女性的智慧就在于迅速回收被周圍災難摧毀的生活碎片并重建家園,科萊特的小說里彌漫著巧克力和金雀花的香味,有著飄飛的長方形小果實,花園里色彩斑斕的蜥蜴,鑲嵌著米粒大珊瑚珠的耳環,關注并描繪這些微觀、富有生活氣息的感性事物,在她看來是女性追求自身完整性的一種方式,也是在混亂而不完美世界中自我救贖的永恒法則。就在科萊特去世的一九五四年,西蒙娜·波伏娃女士獲得了法蘭西龔古爾文學獎,她和科萊特反向而行,最終殊途而同歸。西蒙娜從不關心動物、植物和小飾品,她接受了和男性相同的教育,二十幾歲就取得了和男性一樣的成績和經濟獨立。對西蒙娜而言,完整性意味著可以自由出入男性世界,平等成為他們中的一分子并取得同等成就。西蒙娜介入了她那個時代幾乎所有重要的智力創新和政治活動,成為一個和薩特并駕齊驅的存在主義領袖、一個知識分子,她也參與了時代波瀾壯闊的政治實踐,是歐洲左翼政治運動的先鋒、共產主義的同路人、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的支持者。忽略瑣屑,擁抱宏偉,她是一個永不疲倦的廣闊世界的探索者和開拓者。

四十歲之前,女性身份對西蒙娜來說毫無意義,每個人都要面對疾病、命運的變幻莫測,每個人都要扛下艱難的工作和生活,男人和女人并無區別。女性的發現和《第二性》的寫作對西蒙娜來說是一個偶然,國家圖書館浩如煙海的資料將她驟然拋進一個女性世界,一個她身在其中而不自知的世界,而對于絕大多數女人來說,性別構成了她們命運的底色,甚至是她們的全部。《第二性》把西蒙娜·波伏娃推到風口浪尖上,她得到幾乎等量的榮譽與辱罵,信任和懷疑。一方面她揭露女性的屈從地位、社會性的奴役和壓迫,被推選為婦女解放的旗手,成為最著名的女性主義者;另一方面西蒙娜竭盡所能地抗拒兩性之間無法溝通的觀念,也不愿意接受性別之間完全敵對的假設,激進女性主義者則懷疑她的態度,辱罵她的虛偽和兩面派。西蒙娜始終會做出自己的選擇,她珍視性別之間的難能可貴的關系,就像她和薩特一樣,自然、輕松、有競爭合作,或許愛恨交織而最終不失誠意的關系,她始終沒有采用美國式的攻擊性腔調,而保留了適度的節制和溫和,這是波伏娃本人的選擇,也可以看作法國女性主義運動始終都比較溫和的一個標志。
四、在女性世界尋找多元
一個國家就像一條船,在漫無邊際幾乎靜止不動的水面航行,水面之下便是悠久的歷史和文化,看似平淡無奇實則變化多端。波瀾不驚的文化河流承載了法蘭西民族國家的這條大船,也決定了法國何以為法國。年鑒學派的前輩布羅代爾在《法蘭西的特性》導言中指出:“雖然過去和現在被丘陵、山脈、斷裂和差異等障礙物所隔開,但過去終究經由大道、小路乃至通過滲透而與現在相匯合:陌生而又似曾相識的過去在我們周圍漂浮。”他搜索那些陌生而又熟悉的過去,追逐那些起落不定的潮水,探尋那些來自歷史深層的泉涌,判斷它們怎樣像江河匯入大海一樣融入現實。奧祖夫遵循著布羅代爾的教誨,她拓寬了丈量歷史的時間尺度,得以搜索法國女性文化的豐富和多元,觀測兩百多年間迥異的生存故事和生命意義如何匯入當下。《女性的話語》里奧祖夫展現她捕捉多元價值和多種人類命運的能力,觀察主人公各自不同的性情、觀念和舉止,不厭其煩地傾聽那些語氣和音色大不相同、意味深長的私語,陪伴她們感受生存的快慰與艱辛、命運的幸福或悲戚。這些豐富多樣的聲音和女性畫像構建了法蘭西的民族記憶,也不經意間緩解了現代女性主義的極端傾向,并塑造了法國的獨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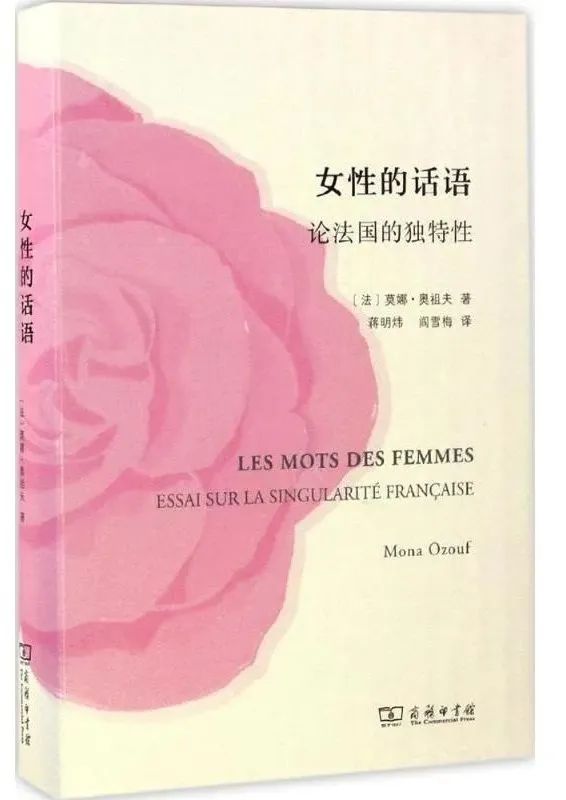
在源遠流長的舊制度和大革命所帶來的震蕩之間,奧祖夫一直在尋找一條和解之路,她關心的核心問題是法蘭西“自法國大革命這一基本事件以來民族特性是如何構建的”,而革命·文學·女性三部曲正是她探索法蘭西民族特性的嘗試。在奧祖夫看來,法蘭西的特性存在于兩個相反相成的特征之中,《革命的節日》展現了法蘭西特性的一方面,“人們是通過革命者的意志主義教育學,通過消除相異事務的熱火朝天的熱情來進行這種建構的”,法蘭西致力于創造一個民族國家共同體,建構一個統一的認同,用革命熱情統攝和取代一切;《小說鑒史》和《女性的話語》則探索法蘭西特性的另外一方面,“人們反其道而行之,通過抵制這種事業來從事這種建構”,婦女和文學所扮演的角色,指向對于多樣性的尋求。大革命并沒有將女性變成千篇一律的愛國者,而是各自有著鮮明的形象:執拗或靈活、庸俗乏味或富有創意、寬宏大度或獨斷專行、擁抱整個世界或將世界圈入設定的界限。奧祖夫深知正是在她們身上,蘊含了一個更真實,或許更會流傳久遠的法蘭西,就像是十三世紀法國寓言長詩《玫瑰傳奇》中的形象,優雅鮮明并飽含著敵對的美德。
來源:讀書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