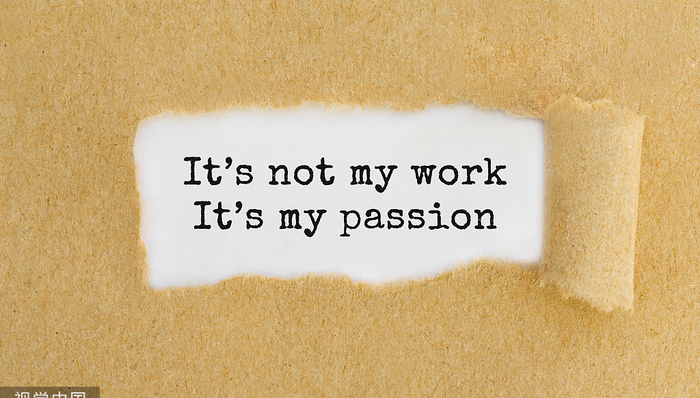049期主持人 | 林子人
最近在讀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的《毫無意義的工作》(The Bullshit Jobs),看到書中討論的一個話題正是我們越來越感到困惑不解的一個現象:工作的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正在呈現反比態勢,而且人們似乎默認了這種情況是合理的。
新冠疫情爆發后,此種悖論可以說是極大地凸顯出來。城市封控期間,依然在第一線保障市民健康和城市基本功能的工作者,如醫護人員、清潔工、快遞員、外賣員、小商販,他們所做的是對全社會有極大意義的、不可或缺的工作,但他們卻承受著最多的風險,甚至遭受更為嚴重的壓榨與傷害。格雷伯指出,毫無意義的狗屁工作的存在本身令所有勞動價值理論都站不住腳。首先,普遍的道德直覺告訴我們,如果一份工作達成的成果(比如提供某件商品或某樣服務)能夠滿足人們的需求或改善人們的生活,那這份工作就是有價值的;其次,當人們在探究工作的意義時,“有意義”往往是“有用”“有益”“有價值”的代名詞;然而,這種意義和價值卻在很多情況下與經濟價值割裂,似乎工作對他人越有益,帶來的經濟回報就越少。
格雷伯認為,“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劃分出現于公元前600年前后,橫跨歐亞大陸“非熟人交易市場”興起的時期。一旦金屬貨幣系統的發明讓陌生人之間建立交易關系成為可能,面對物質時的利己主義(經濟價值)和面對理想時的利他主義(社會價值)就開始拉鋸,大眾宗教就開始宣揚物質不重要的理念,規勸虔誠的信徒要無私奉獻、捐物行善。然而事實是,將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完全隔離開是不可能的,兩者總是相互滲透,而在當下這個由貨幣購買力構筑生存基礎乃至成就聲望的時代,社會價值不能完全轉化為經濟價值不免讓我們感到不公。
與此同時,現代社會又強調我們應該熱愛自己的工作。谷歌圖書詞頻統計器Ngram Viewer的數據顯示,“追隨你的熱愛”(follow your passion)這個詞組在2008年出現的頻率比1980年高出將近450倍,當時幾乎沒人那么說。這句話似乎是在暗示,我們每個人都具有某種天賦的激情,只要下定決心投身于激情,努力工作,就能在職業生涯中獲得好的回報。但我們已經知道,很多時候情況并非如此。格雷伯諷刺道,現在很多公司覺得如果某份工作有價值意義,能帶來滿足感,公司就可以不付報酬。一個“志愿者階級”正在興起——企業開始將收割勞動成果之手從有償勞動力的身上慢慢移開,伸向無償實習生、互聯網愛好者、積極分子、志愿者和發燒友,從他們熱情的自發勞動中攫取利益。

[美]大衛·格雷伯 著 呂宇珺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2-7
美國《大西洋月刊》資深編輯與撰稿人埃倫·拉佩爾·謝爾(Ellen Ruppel Shell)在《工作:巨變時代的現狀、挑戰與未來》一書中指出,那些對工作充滿熱情,有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的“蒙召者”(the called),其實是雇主最喜歡也最省心的員工,這不僅因為他們無需鞭策就會全身心工作,還因為他們不會講條件和提要求。從這個角度來說,追隨你的熱愛,做一份自己真心喜歡的工作,對我們來說是不是反而是一件壞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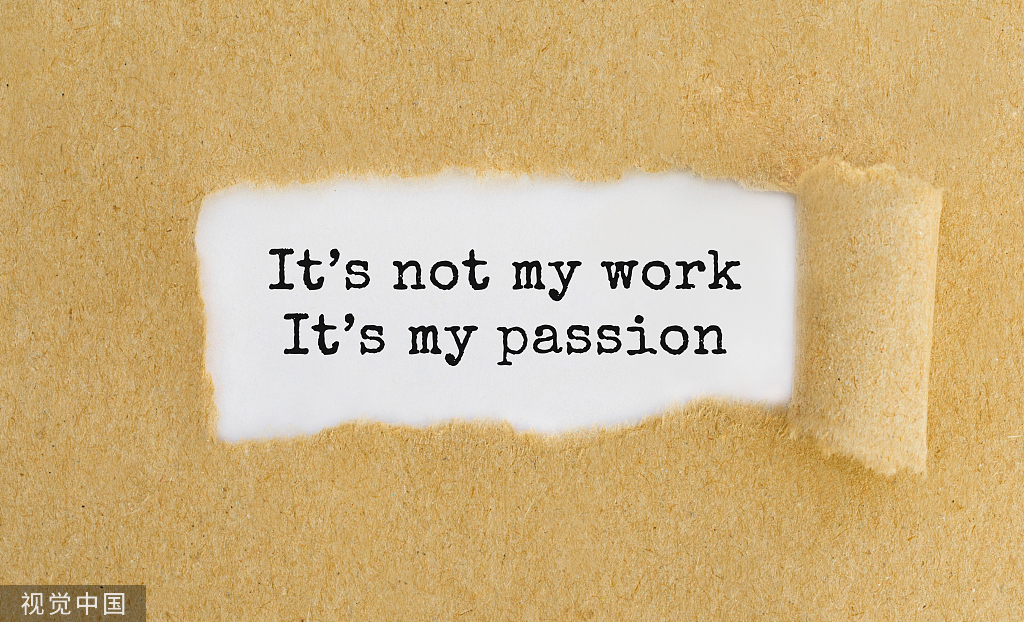
在謝爾看來,在工資增長停滯、工作不穩定性上升的當下,我們應該克制理性地對待“工作的激情”,不要被期待或被強迫從具體崗位中獲得意義。“好的崗位(job)越來越少,我們的應對措施不應是試圖‘創造’更多‘有意義的崗位’,而是應該打消在崗位中尋找意義的想法。”
01 所有“夢想的工作”都會經歷調試和驗證的過程
徐魯青:我從初中開始就一直想做記者,但從沒想過自己會做文化記者,最早的時候是想去中東當戰地記者,在槍林彈雨里從前方發來伊拉克相關報道。記者法拉奇的傳記我讀了一遍又一遍,她經歷過印度和巴基斯坦戰爭、南非動亂、中東戰爭,越戰開始后又做了八年的戰地記者,隨行的背包上一直貼著聲明:如果發現我的尸體,請運交至意大利使館。她從不害怕冒犯采訪對象,去伊朗找霍梅尼時,憤怒于必須要帶著面紗才能采訪,直接當著霍梅尼的面撕開面紗,大聲對他說:“許多人說你是個獨裁者!”采訪基辛格的時候她咄咄逼人地問:“權力是誘人的,基辛格博士,權力對您有多大的吸引力?希望您說真話。”基辛格一直后悔接受了她的采訪。當然,現在回看法拉奇的言論,會發現其中充斥著對伊斯蘭教的污名、對中東文化的鄙夷,我也不再相信對抗、激怒與劍拔弩張能呈現出最有價值的信息,但她戰斗到底的姿態太打動當時的我了。

年歲漸長后我越來越怕死,戰地記者肯定是不想當了,也沒有生長出足夠蓬勃的江湖氣,在社會新聞突發現場做得游刃有余,反倒后來對學術的路徑感興趣,有過一段時間想讀博。以賽亞·柏林把人分成刺猬和狐貍兩種類型,狐貍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專門知道一件大事,狐貍各處刨洞,對什么都好奇,刺猬能沉下心鉆研得很深。我是絕對的狐貍型人格,文化記者的工作屬性相比讀博更適合我。這么說來,好像確實很喜歡自己的工作——這話我寫出來時擔心了幾秒不夠正確,或許也反映出了現在找一個不狗屁的工作實在太難。
尹清露:所有“夢想的工作”都會經歷一個不斷調試、驗證可行性的過程吧。小時候想當(抽象意義上的)“畫家”或者“作家”,很天真地覺得這兩者差不太多。我首先向“畫家”進發,初中嚷著要藝考,這個幻夢持續到大學,但終于發現自己不是那塊料,比起創造我更喜歡觀察、比起圖像好像對文字更加敏感,再去作為一枚中介去傳達真正值得言說的事物。
如此想來,文化記者確實很合適自己。我很喜歡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提出的“bricolage(拼裝)”的概念,利用手頭現有的材料或他人的話語努力地做出點什么,就像家庭主婦/主夫會用冰箱里的剩菜燉一鍋例湯那樣。當然,并不是說記者就是如此不堪的存在,但是每次想到魯青提到的“狐貍型”人格,一只小狐貍興致勃勃地四處搜集寶物的形象總會出現在腦海中,這也是我自己正在做的事。我曾覺得做一個勇攀高峰的刺猬比較酷,但狐貍的人生也可以很幸福。
02 “情懷”和“金錢”為何總是水火不容
潘文捷:這幾天在看豆瓣勸分小組,里面有一些典型話術,男方不送禮物顧左右而言他或者給了0.25元紅包讓女方倒著讀,女方表達不滿,他就會說:“我以為你不是物質的人呢。”“你和我戀愛就是圖錢嗎?”哇,不知道別的行業怎么樣,在文化行業這種大家普遍認為“有情懷”的行業里,可是太經常聽到這種的話了。
并不是說每家文化企業都是如此,只不過利用年輕人的熱情來進行剝削真是十分常見。“重版出不來”經常會發一些出版行業的匿名吐槽,進入出版相關行業的有幾個不是出于熱愛呢,但是現實有的時候卻令人心寒。你仔細翻翻,不論是出版業翻譯待遇、編輯待遇、營銷編輯待遇,一堆雷點。前幾天這個賬號發布了一條由自稱為“潦草”的內部人士提供的單向空間強制加班通宵的事。文章稱,為了心目中理想的工作來到書店,結果“一周連續三四天加班到兩三點,發工資最后只拿到兩千塊錢”,“除了工作,幾乎失去一切自己的時間”。而結果呢?連自己追求的那點熱愛都沒能實現——工作有很大部分是在“微信搜索一下,復制粘貼改個語序”。文章還轉述上級教育他們的一句話:“所有理想主義的背后,都是需要富士康一樣的勞動運作的。”以為自己在追求價值、追尋熱愛是挺感人的,另一方面不過是和富士康工人一樣被壓榨罷了啦。

葉青:文捷提到的譯者待遇我非常能感同深受。之前有同事來問我現在的市場翻譯稿費標準是多少,聽完我的回答,他說和他們十年前一個價。這是什么概念?十年前成都的房價才幾千塊,現在都開始往4萬沖擊了。當然用房價來做對比不太公平,但一個行業的平均薪資水平十年都沒有明顯變化,顯然是不符合一個良好市場的發展規律的。尤其是文學翻譯,在我看來應該算是最難以及最耗費心力的翻譯活,但如果你拿文學翻譯的稿費和幫企業做一些資料翻譯的稿費相比,兩者能差好幾倍。價格這么低,說文學譯者是在“用愛發電”毫不為過,更別提還有拖欠稿費等問題。
我問過一位合作的譯者,為什么愿意這么多年一直幫我們做編譯,他的回答是因為我們的稿費會按時發放。同時我們在譯作的豆瓣評論里常常能看到讀者吐槽翻譯太爛,倒不是為了幫某些譯者做辯護,但是我想“一分錢一分貨”這句話在翻譯行業可能多少也有些適用。
徐魯青:我也很喜歡看豆瓣的“重版出不來”和“青年編輯們”,發現出版圈吐槽大會真有那么多破事,出勞工權益書籍的公司回頭壓榨自家勞動者,一直強調版權保護的地方一點都不尊重譯者的勞動。媒體也是一樣,單向空間的新聞出來后,又看到很多人轉載某雜志相關的性騷擾女員工的截屏。之前還讀過一篇聯合國的相關文章,里面提到已然正義化身的聯合國從不會支付實習生勞動報酬,很多實習崗位還需要倒貼錢,這導致聯合國的雇傭人員背景出現了明顯的中產階級化,底層的孩子很難爭取到進入這個圈子的機會。我覺得不管是什么公司,宣傳什么樣的理念,和我們最根本的關系永遠是雇傭關系,是資方和勞動者的關系,看清楚這一層才不會被情懷濾鏡所騙。

03 熱愛與否不應成為工作的必要條件
尹清露:我也時常陷入有關熱愛和意義感的迷局。分三塊來說,那些執著于意義感或理想的人是被剝削最嚴重、也不那么注重現實利益的;不太追求意義感的人反而能劃分開生活與工作,甚至能以“熱愛”之名為下屬畫大餅;與此同時,支撐這層虛無縹緲的意義的是卻是底層勞動者,像是外賣員和基建工人,他們似乎不具備談論意義感的生活基礎。
可能重要的一點在于,關于“什么東西值得熱愛”已經被標準化了,比如智識性的腦力勞動值得熱愛、創造經濟效益的工作值得熱愛,但是體力勞動就沒有意義,好像它是純動物性的、更低一級的。如果這層標準不被動搖,有毒害的“熱愛文化”還是會源源不斷地產生,而且會持續分化工作之間的等級。上世紀60年代歐洲有一個先鋒藝術團體提出了“情境主義”的概念,意在顛覆日常生活。他們認為“每個人都是藝術家”,這并不是說每個人都要做職業藝術家,而是誰都能親身實踐藝術,在這段時間內,人們不再是擁有特殊任務的、被異化的勞動者,而是街頭的普通人;同理,每個人也應當在某些情境下嘗試更多種類的勞作,并且意識到其中蘊含著的意義和價值。當然話雖這么說,實踐起來也很艱難,“狗屁工作”系統中的工作細分決定了我們都要各歸其位、掙扎著混口飯吃,不然擁有烏托邦理念的情境主義團體也就不會過早地解散了吧。
徐魯青:清露提到的被標準化的“什么東西值得熱愛”我覺得很有意思,一份工作被視為沒有意義肯定會加劇勞動本身的枯燥,比如像送外賣就很明顯。在國外生活的時候我送過一段時間外賣,整個過程其實可以體會到一些樂趣,比如我會騎著車在很少有人注意的狹小巷道穿梭,沒過幾天就熟悉了城市的細節和紋理;進入平日很難近距離接觸的住宅,沿老房子的旋轉樓梯一步步向上走時,感覺像走進了十八世紀的歐洲小說。接外賣的人也各有各的不同,有時還可以從訂單里猜測他們的來歷和故事。但這一切樂趣都是建立在工作的勞動強度不大,充裕的送餐時間讓我有閑心看東看西,外賣員身份也沒有受到歧視,得到的報酬更是體面的——甚至不會比當地公務員的時薪差太多。我想,在理想的環境里,外賣工作被普遍得到了認可,這樣的勞動其實比公務員要有意思有價值太多了。

姜妍:如果只是單純地把“熱愛”理解為工作的話,那么其實世上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即便真的做了一份自己熱愛的職業,只要在一個正常的工作體系中總還是會有各種需要調適的部分,比如不是說你喜歡讀書、是個文青,就和文化記者是匹配的;你喜歡追星,就是個好的娛樂記者。我的父母一代都是國家分配工作,離追隨熱愛實在距離甚遠,可能只能反過來熱愛你已經“追隨”的。但如果把這種熱愛寬泛化去理解的話,我當然希望每個人在內心深處能追隨自己所熱愛的東西,那不一定非得轉化為工作,甚至有時候因為熱愛和為稻粱謀有些距離而更純粹。我們之前做過的“野生作家”系列訪談中,已經有許多相關的例子。
林子人:謝爾在《工作》中提出了一個看似反直覺的觀點:“熱愛”與否其實不是一個人是否能做好一份工作的必要條件。她采訪過一位入行多年的消防員,這位消防員認為,為穩定收入工作、認為“工作就是工作”的消防員其實更可靠,做得更好,那些“一腔熱血”的“蒙召”消防員反而有可能會拖后腿,因為他們可能會用一種英雄主義的心態來對待工作,即使到了下班時間也會堅守崗位,發生火警時會違令擅闖火場,再極端點的“簡直和縱火犯差不多”。

[美]埃倫·拉佩爾·謝爾 著 秦晨 譯
后浪 | 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2021-9
那么“愛崗敬業”“追隨你的熱情”之類的職業道德觀又是如何變得如此深入人心的呢?我之前在《從渴望閑暇到鄙視懶惰,倡導加班的工作倫理是怎樣形成的?》一文中提到過,“有意義的工作”這個短語在英文圖書中出現的頻率自1970年代起直線飆升,它恰恰發端于勞動者的經濟回報開始下降的時候——二戰后勞動者生產率和工資同步增長的趨勢被打破,生產力提高的潛在收益開始不成比例地進入頂層精英的腰包。因此,“有意義的工作”這個信條不過是一種心理補償機制。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一份工作有沒有意義,而是一份工作能不能給予我們體面的、有盼頭的生活。能做到后者,雇主也就無需擔心員工是否真的有熱情了。遺憾的是,“熱情”“意義”“情懷”這些非常主觀的東西如今越來越被資方所利用來最大化地攫取勞動成果。
這兩日讀《吸血企業:吃垮日本的妖怪》,作者今野晴貴提出,鑒于日本已經變成了一個所有企業都有可能對員工“用后即棄”的“俄羅斯輪盤賭社會”,年輕人要采取的一個戰略是時刻保持警惕,和用人單位“保持適當距離”的工作方式反而是更加現實的,一味相信公司的“老好人”在今后的時代會越來越難以生存。讀到這里的時候我其實感到一絲悲傷,當勞資關系中只有責任沒有義務,社會信任被極大破壞,其造成的高昂社會成本將是由全社會的人來承擔的,比如工作效率下降、公共福利資源的浪費和少子化。從個人角度而言,更理智地對待工作當然是一個重要的自保手段,但一個更好的社會難道不應該讓那些熱愛手頭工作的人無需對從事這份工作有任何遲疑和悔意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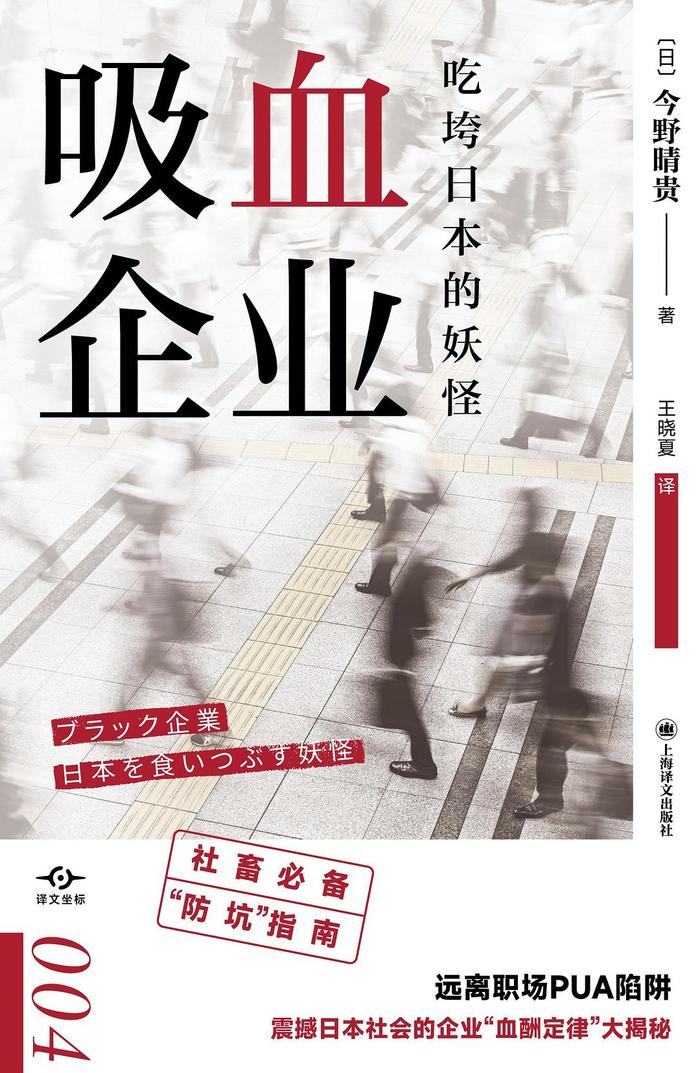
[日]今野晴鬼 著 王曉夏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