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8期主持人|徐魯青
近日,杭州的柳樹上了新聞。西湖斷橋邊的7棵柳樹被移走換成月季花,景點“柳浪聞鶯”新栽的柳樹尺寸遠小于原樹,大量杭州市民對此提出批評,“沒有楊柳的西湖缺少靈魂”、“破壞了文化”……壓力之下,杭州政府向市民道歉,并重新補栽了柳樹。
這并不是我們第一次關心城市里的樹。2021年,廣州市政府在實施“道路綠化品質提升”“城市公園改造提升”等工程中,砍伐了三千多棵榕樹,市民發起了“榕樹保衛戰”。2020年,成都桂花巷的20棵大桂花樹被砍,市民表示不滿。2011年,南京為建造地鐵,計劃移除2000棵法國梧桐,也激起了許多人的反對。植物承載了一座城市的集體記憶,在上海與南京生活過的人不會忘記,走過植滿梧桐的街道時葉隙漏出滿地明滅光影;重慶最常見的黃葛樹能深深扎根陡峭坡道,春夏之交,金黃的樹葉灑落一地;每年春天的北京,滿城飄蕩的楊柳絮在讓不少人過敏的同時,也頗引離人懷念。
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副院長肖毅強認為,植物和古建筑一樣,也有自己的歷史與文化意義,他認可廣州人對榕樹的保護,“五十年代,因為修路、埋市政管道,北京拆了不少老城墻;八十年代,因為道路拓寬,廣州也在拆老騎樓。如今我們對城墻和騎樓是歷史風貌的載體、應該呵護它們的存在有了共識,但卻對珠江兩邊的榕樹漠然,其實是歷史性認知錯誤的重演。”然而,在許多城市規劃中,樹木只被當作提高城市綠化率的工具、打造網紅景觀的零件、基建設施建設的阻礙,這不僅忽視了樹木的文化與歷史意涵,也掩蓋了它們承載的情感與記憶。

在路旁、身邊與心頭:扎根在我們城市記憶里的植物
姜妍:北京其實很多植物都讓我印象深刻,童年時窗外是一排楊樹,日日盯著這排楊樹發呆和胡思亂想,當然是很難抹去的記憶。北方干燥,秋冬樹葉落下,我很喜歡枯葉踩在腳下的那種感受,但唯有銀杏葉因為水分含量大,無論如何不會變得徹底干燥,也會讓我多一分注意。有一年去臺北,天心老師講起自己第一次去日本,坐在列車上看到銀杏樹的時候很驚嘆,剛好是銀杏樹金黃的季節,她就問身旁的老師那是什么樹。老師偏偏紹興口音很重,回答了兩遍天心老師都沒聽清,又不好意思再追問,只好循著發音給友人寫信道,“我在這邊看到一種好漂亮的樹,叫——銀行樹。”天壇北天門至祈年殿的路上也植著兩排銀杏樹,每年秋季很多人從地上撿白果吃,去年卻幾乎無人問津。想來是因為去年氣溫驟降,大風一夜間把銀杏葉都吹掉,而白果也還沒真正成熟的緣故。銀杏葉雖然好看,但落地上的白果卻并不易清理,氣味也很感人。

林子人:杭州的市樹是香樟,但市民最有感情的應該是市花桂花,幾乎每個街道都種了桂樹,從8月下旬開始,杭州人就開始期待桂花盛開,滿城桂香的時節,杭州人會去“滿隴桂雨”游玩,找一家農家樂,和三兩好友坐在桂花樹下喝龍井,消磨時光。你們能想象杭州有些幸運的小學生的課外活動是“打桂花”么?宋樂天在《無盡綠》里記錄了她在2014年9月底隨一群小學生“打桂花”的經歷。滿覺隴的村民有感于小學五年級語文課文《桂花雨》中的配圖謬誤(圖中母女二人通過搖動樹干來收集桂花,但與事實不符),邀請了杭州的“小伢兒”(杭州話里的“孩子”)來親自體驗“打桂花”:三人結成一隊,二人手持紗帳站在樹下,一人用竹竿輕敲枝干,金黃色的花雨就簌簌而下,落在紗帳里。我讀到這里的時候真是羨慕這些孩子,這樣的童年記憶應該是杭州獨一份的吧。打下來的桂花會被加工成桂花糖或桂花干,我當年出國留學特地帶了一罐桂花干,在泡龍井的時候加一點桂花干進去,添上一縷幽香,聊以慰藉思鄉之情。就像宋樂天所說,桂香最是撫慰人心,“這時我忘記我是一只駱駝,我身上負有人生的重擔。”

潘文捷:香櫞是我老家的市樹。這是一種本地樹種,結出的果實顏色形狀有點像柚子,可以散發柑橘的清香,并能存放很久,據說也可以做中藥材,但是不能直接吃。一般家庭就把果實放在家里做裝飾,還能清新空氣。
香櫞樹在老家隨處可見,也有兒童藝術團、本地企業起名為“香櫞”的。我們和鄰居家的中間地帶就種了一棵。生活中為了土地吵架的例子很多,據說這棵樹苗是對方的,土是我家的,結出來的果實兩家分享,有以示友好的意思。雖然不清楚當年的具體情況,但我想他們選擇香櫞而不是其他樹種或許有一定的寓意。對我來說,這種植物已經算是一種情感的維系。
葉青:成都簡稱“蓉”,是因為市花是芙蓉花。據成都博物館的介紹,五代十國時期后蜀皇帝孟昶在成都遍種芙蓉,以此花承載他的政治理想,愿國家如芙蓉盛開般昌盛。但民間流傳的說法稱芙蓉是為了他心愛之人花蕊夫人所種,因此芙蓉花還象征著愛情。根據成都市林業園的統計,成都在2017年就已經種了14萬余株芙蓉,但我平時走在街上并不常看到(很有可能是我沒認出來),個人覺得成都最多也最好看的還是銀杏,春夏還不明顯,深秋時節街上金燦燦的一大片,好看極了。

網紅景觀、忽略當地生活與植物年限:城市綠化有哪些問題?
徐魯青:很多時候,城市綠化太注重追求景觀造型,忽略了植物與生態系統的發展。生態學學者楊永川提過一個例子,上海在2000年初準備世博會的時候提出要把全世界同緯度的樹種都移來栽種,但同緯度大部分地區都是沙漠,于是上海移了很多棕櫚樹,后來發現這些樹冬天都快凍死了,只能給他們“穿衣戴帽”。后來雖然上海停止了這類移栽,但其他小城市的綠化都朝大城市靠攏,也開始種棕櫚樹。
尹清露:雖然濟南被稱為“泉城”,也常被評價為“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但就植被覆蓋率和樹種多樣性來說,肯定沒法和南方城市相比,到了冬天,城市也會變得灰撲撲,街上往往就只有稀疏的行道樹(即使最近兩年經過規劃已經好一些了)。最近屬于濟南的植物高光時刻應該是泉城廣場的大片郁金香,四月正好是花期,好些朋友都去打卡拍照來著,近看是很好看,但是密集的花海在混凝土城市背景里還是很突兀,如此一來,花變成了人們瞻仰的景觀,反而說明了城市里植物的貧乏。
這些問題和地形地勢不佳、北方城市氣候肯定有很大關系,但是“先天條件”的缺乏是不是也會導致居民對植物的重視不足,從而影響更合理的城市規劃?比如我就從小和植物的關系比較遠,體會不到植物的美,去過植被豐茂的地方之后才發現它們的重要性。

徐魯青:“花海”之類的網紅景觀好像在中國城市中經常用來吸引游客,我印象里有縣城會打造“薰衣草花海”或“玫瑰花海”,稱自己是“小普羅旺斯”之類。也有一些城市為了旅游業或者“花園城市”的名號喜歡追求植物奇觀化,比如廣州砍掉榕樹的一個理由是要打造“花城”形象,讓榕樹為開花樹木讓道,但這不一定適合當地人的生活。實際上,很多廣州市民都喜歡在榕樹下乘涼,榕樹如果砍光,廣州夏天的街道會非常熱。這里也涉及到城市到底為什么而建的問題,無論是“花城”也好,還是不允許人親近的大塊綠地也好,都像是為觀光、為展示而建,但如果真的從當地生活出發,只能看不能躺的大綠地并沒什么意義。
姜妍:不太了解這次杭州柳樹事件的具體情況,但是由于不同的植物確實有不同的壽命年限,所以在做城市景觀決策的時候需要納入這一考量因素。比如日本的櫻花樹其實也是在替換的,而且不會說等到植物年限快到的時候再進行操作,這個替換可能對偶爾到訪的游客來說感知不明顯,但是在地居民肯定能捕捉到。
徐魯青:植物年限確實是城市規劃需要考慮的一點,學者楊永川也提到,現在的城市綠化相比于培養小樹,更喜歡大樹移栽,但很多樹現在放在路上可能大小合適,等五年十年后,作為行道樹就太大了,會阻擋行人通行,而且移栽也會破壞大樹本來有的生態系統。大多數城市管理者可能就只在一個地方待幾年,小樹并不能馬上見到綠化成果,于是傾向直接用大樹,而不是等待一個生態系統慢慢建立起來。
除了“被馴服的自然”,也要有肆意生長的自然
尹清露:深圳的城市和植物的關系很近,坐在出租車里都覺得心情愉悅,因為窗外都是果樹、椰子樹。去年住在南山區,每次出門都會路過沿著海岸線而建的深圳灣公園,感覺如同度假,還因為家門口的桂花太好聞,特地買了桂花味的香薰蠟燭擺在家里,不過也就能還原30%真實的花香。
林子人:和許多其他城市相比,杭州的幸運在于自然是它的有機組成部分。2000年以后,杭州施行了環西湖景點免費的政策,進一步將西湖整合進城市景觀之中,姑且不提此舉對提振杭州旅游業產生了多少積極的效應,對于杭州市民來說,這肯定是一件好事——親近自然本就不應該有經濟門檻。
搬到上海,我一開始的確有些不習慣,覺得這座城市綠色好少,但慢慢地我發現上海的自然是靠各種城市公園堆砌起來的,甚至在街角都能劃出一片小小的空地做成一個花園,還挺可愛的。
這兩天社交網絡上流傳環貿iapm的階梯上雜草叢生的照片,有人感嘆,當城市無人時,自然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重新占領空地,也有人指出這本就是iapm的園藝設計。我是覺得它提醒我們注意,城市中的綠意或多或少都是“被馴服的自然”,需要人類不斷地去修剪和維護,即使是西湖也是如此,因此它是“世界文化遺產”而非“世界自然遺產”。但我們需要承認,植物也是城市景觀的一部分,和建筑一樣能讓城市居民產生深刻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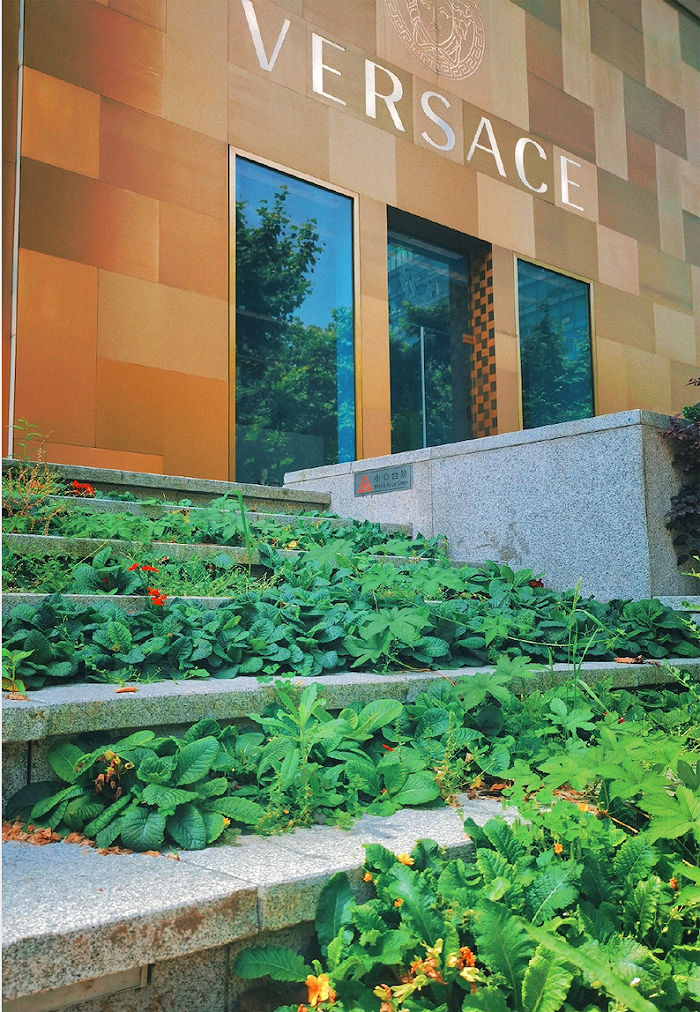
徐魯青:很同意親近自然不應該有經濟門檻。這讓我想到北歐一些國家的“自由漫步權”,也叫“自然享受權”。北歐大多數原野和森林都是私有的,但是法律規定人們有權利進入私人的林地,采摘野果、蘑菇、野花,或者搭帳篷露營等非破壞性活動,這保證了人人都能享受美麗的自然。
一直羨慕一些西南城市,喀斯特地貌讓市民在城中心走幾步路就能夠到山野與林地。上海確實有很多可愛的小公園,但在我看來它們太過修整,光有“被馴服的自然”是不夠的。一些城市規劃學者也開始批判傳統“綠化”概念缺乏對人類中心的反思,提倡城市綠化不應只是整整齊齊的人工景觀,而是再現田野和森林的真正生態系統——讓人行道旁長出灌木與野草,讓公園里的野花肆意生長。植物也不能只被視為服務人類的工具,它們同樣是城市的居民,同樣應該有空間自由生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