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被邊緣化的動物們,不得其所的命運若要有所改變,還有待更多人愿意了解,”在《它鄉何處》一書中,作者黃宗潔將城市空間視為思考動物議題的開端,結合文本分析、時事評論、倫理思考,并借由文學與藝術作品中看待動物的各種角度,探討了人與環境、人與自然、人與他者之間糾結錯綜的關系。在了解之后,或許我們可以為如何保護和對待與我們共享同一空間的動物找到行動與論述的支點。

《不得其所的動物》
撰文 | 黃宗潔(節選自《它鄉何處》)
01 城市中的動物身影
2015年5月,在美國舊金山灣區的車底下,出現了一只看上去奄奄一息的小海獅,路人報警并將其送至海洋哺乳動物中心療養后,所幸并無大礙。但獸醫檢驗時卻發現,這只小海獅同年2月間已入住過該中心,當時取名為“垃圾哥”(Rubbish),救援并增重成功后已于3月底野放,想不到才事隔月余,它又形容消瘦地流落街頭。
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國香港地區,2017年7月間,有登山人士在大嶼山引水道旁發現一只體型瘦弱的大理石花色小狐貍,救援后包括漁護署、愛護動物協會、海洋公園等多個單位皆表示無力長期照顧收容,小狐一夜之間頓成“狐球”,不知該何去何從的命運亦引發眾多市民關切。
上述兩例無論就物種、城市環境與動物落難原因都看似迥異,沒有相提并論的理由,但它們指向了同樣的問題核心,那就是無論要討論當代動物的處境,還是人與動物的關系,往往必須回到城市中思考。這其實是個違反過去我們所熟悉的“常識”或“直覺”的選項,因為提到動物,過去多半是放在自然、荒野的脈絡之下進行討論。一直以來,將文化與自然、人與非人動物視為二元對立的兩種互斥系統,始終是多數人看待生活世界的主流態度。然而,人與動物關系的改變,其實與都市化的進程息息相關,這是一個持續與自然對話/對抗的過程,因此,若將動物抽離城市的脈絡來思考,不僅不符合現實,亦無法真正梳理出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復雜互動。

黃宗潔 著
三輝圖書|南京大學出版社
無論美國的小海獅或中國香港地區的小狐貍,它們同樣都出現在某個“不該出現”的錯誤場所。海獅擱淺是海水暖化、海洋環境劣化影響食物來源所致;而小狐貍無論是人為棄養或走失、逃逸,都與非法買賣及運輸野生動物有關。換言之,它們的“不得其所”,推論到最后仍然是人類行為所致。這也是何以在當代人文地理學的反思中,一個很重要的潮流正是重省人與動植物“混雜動態的生命”。如薩拉·沃特莫爾(Sarah Whatmore)所言:
(過去)動物的地位大多掉落在當代人文地理學與自然地理學的議程外,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掉落在這些議程的間隙里。不過,新的“動物地理學”焦點正在浮現,試圖證明動物位居一切社會網絡中,從野生動物的狩獵旅行,到城市動物園、國際寵物貿易,到工廠養殖,擾亂了我們有關動物在世界里“自然”位置的假設。
本書的核心概念,正是希望指出此種新的“動物地理學”的視野,將眼光放回我們生活的場域,正視動物非但不是少數愛好者才需要關心的對象,更與我們的生活緊密連結,且早已被人類毫無節制與遠見的所作所為嚴重影響與傷害。動物與自然不是框限在電視機里那看似遙遠到與我們無關的沙漠或草原,而是就在我們的日常之中。
保羅·波嘉德(Paul Bogard)在《黑夜的終結》(The End of Night)一書中,就曾以拉斯維加斯的發展為例,說明城市的開發與快速的變化,如何令原先生活在當地的生物措手不及。文中描述這座世界最明亮的城市,在夜晚會吸引大量的蝙蝠與鳥類,來捕食因為趨光性而飛舞在燈束下的無數昆蟲,看似食物不虞匱乏的環境,卻是蝙蝠與鳥類改變在棲地覓食的習性,必須耗費體力長途跋涉到市中心的致命陷阱,因為等它們再飛回巢穴時,往往沒有足夠的食物喂養下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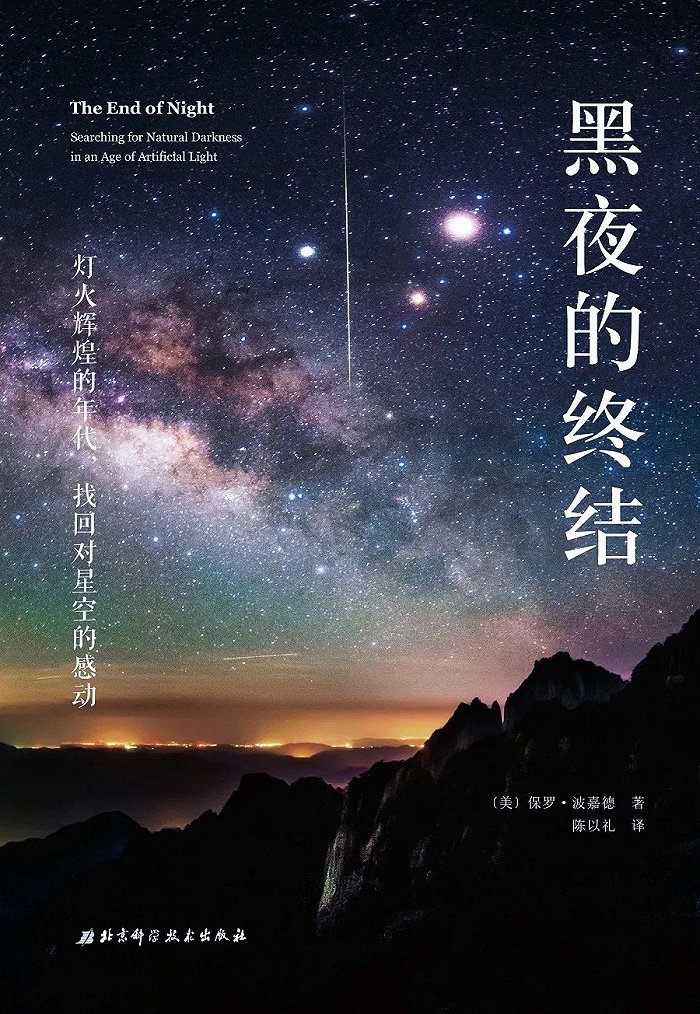
[美]保羅·波嘉德 著 陳以禮 譯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他因此回想起自然主義作家埃倫·梅洛伊(Ellen Meloy)筆下,在酒店外被人工火山爆發驚嚇,最后誤觸拉斯維加斯大道旁高壓電纜,瞬間變成焦炭的那只母野鴨,并感嘆道:
這座城市最早的住宅區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比第一家簽約設立的賭場更早點亮光線,但在不到人一生的時間內,原本幾乎一片漆黑的地方,已經發展成全世界最燈火通明的地方,人口數從1940年代的八千多,快速成長到1960年代的六萬多,再一路成長到如今超過兩百萬的水平。“歡迎來到拉斯維加斯”的好客標語,不過是1959年以后才有的事物。但梅洛伊筆下的母野鴨、盤旋在天際星光里的蝙蝠與鳥類,在這塊土地上繁衍多久了?如果以進化論的時間軸來看,它們根本就沒機會和拉斯維加斯快速變遷的環境一起演化。
人改變與破壞地球的速度太快,快到許多動物的腳步根本來不及跟上。這是何以近年來,許多科學家主張以“人類世”(anthropocene)概念來理解當代人與環境的關系。“人類世”一詞的出現,正是因為“許多專家認為地球已被人類改變得面目全非,因而可以認定全新世已經結束,應代之以另一個新的地質世代”。于是尤金·史多謀(Eugene F. Storerme)及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提出的“人類世”一詞逐漸普及,標志著“人類的世代”之來臨。不過,即使同樣站在同意人類作為已改變地球環境的立場,看待人類世的態度也可能有相當大的差別。由此開展出的一連串討論中,有兩種完全相反的態度,一是認為人類具有創造性的力量,重塑了自然亦將啟動一個更好的未來;二是認為人類目前遭逢的環境危機,正說明了“他們其實既不明白,也無法控制大自然,無法掌握復雜的全球變遷,而人類世將人類意圖和施為的失敗,銘刻進地球的地質和大氣之中”。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在《半個地球》(Half-Earth)一書中,對前者所抱持的態度多所批判,黛安娜·阿克曼(Diane Ackerman)《人類時代》(The Human Age)一書,亦談了許多人類行為如何影響生物演化之例——在這個快速變遷的環境中,動物們雖然看似如波嘉德形容的,演化的速度跟不上人類所帶來的時間差,必須被動與被迫去面對環境的巨變;但在適應的過程中,人類其實等于介入了動物的篩選機制,只有那些更能應付城市生活的物種與個體,方有可能存活。
問題在于,盡管人類的作為早已改變動物在“自然”中的位置,卻又不愿意正視與接納此一位置的改變。文明越是“進步”,動物與自然越被當成應該驅逐的他者,一旦稍有“越界”之虞,我們便因其所具有的力量、疾病與污穢等可能的威脅而感到驚恐、憤怒。這或許也說明了何以中國臺灣地區在2013年傳出鼬獾感染狂犬病的消息時,人們陷入巨大的恐慌,一連串擊殺野生動物、棄養同伴動物的事件,在那兩個月比病毒蔓延得更加迅速。換言之,想要維持動物在我們想象中既有“位置”的企圖,讓人與動物的關系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產生某種斷裂,在城市文明潔凈合宜的秩序與邏輯之下,動物被視為一種失序的介入與存在,中國香港地區的“未雪”事件亦為一例。
2014年8月間,一只小狗誤闖港鐵軌道,列車暫停幾分鐘后驅趕無果,港鐵便恢復通車導致狗被撞死,這不只在當時引起眾多批評,也成為香港動物權益運動史上的指標事件。韓麗珠據此指出:
只有在職責和“正常運作”大于一切的情況下,而群體又把責任攤分,活生生的性命才會成為“異物”,必須把它從路軌上鏟除。“異物”的出現并不是因為人們變得鐵石心腸,而是人和人之間,人和外界之間的連結愈來愈薄弱。清晨的鳥鳴、山上的猴子、流浪貓狗、蚊子、樹、草、露宿者、低下階層、吵鬧的孩子、反叛的年輕人、示威者、雙失青年、不夠漂亮的女人、性小眾、意見不同的人……才會逐一成為“異物”,給逐離和排擠。
這些被排除、被視為“異物”的動物,在城市邏輯的運作下,何處才是它們得以容身之居所?又該如何才能將這些斷裂的連結重新接合?這正是本書所關切的核心命題,亦是選擇城市空間作為思考動物議題開端的理由。
02 動物書寫與動物倫理
動物書寫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本書對于文本的選擇,并非局限于傳統定義下的“動物文學”或“動物小說”。過去所理解的動物文學,多半是指以動物為主角的故事,早期這些故事皆以兒童讀物或寓言故事的形式出現,具有高度擬人化的色彩,動物被賦予刻板化的角色形象,與它們本身的特質并無直接相關;其后,厄尼斯特·湯普森·西頓(Ernest Thompson Seton)等人將動物小說帶入另一個新局面,《西頓動物記》(Wild Animals Have Known)中不只有鮮明的動物角色如狼王羅伯、烏鴉銀斑,故事本身也結合了西頓對動物行為的觀察和知識。因此,這類作品已然達到如吳明益所形容的“在科學知識與文學想象之間的‘雙重接受’”之效果。若以此作為觀察其他動物作品的標準,也可發現傳統的動物小說似乎總在科學知識和文學想象的光譜兩端之間挪移,最糟的狀況則是“雙重不被接受”——一如這些作品所描述的主角一樣,在人類社會中找不到安身之所。
因此,秉持著“雙重接受”的態度,本書選擇的作品并不局限于文學性強的小說,亦不刻意強調符合科學知識者才納入討論,甚至動物也不需要是主角。希望在科學性或文學性之外,亦能兼顧甚至凸顯動物之主體性。因此,在本書定義下的動物書寫(animal writing),是以動物為主體進行的相關思考與寫作。一直以來,動物書寫若較偏向生態環境關懷或具有科學知識者,如劉克襄、吳明益、廖鴻基的作品,多半被納入自然書寫的框架中進行討論,且自然環境又被切割為海洋與陸地,其中以鯨、海豚為主角的創作,就會另列為海洋書寫或海洋文學;至于較具有文學或寓言性質的,則會回到傳統文學小說的文本分析脈絡中。本書希望打破舊有的分類框架,選擇以較為廣義的方式,將創作中涉及動物議題、動物關懷或可反映人與動物關系者,皆納入“動物書寫”的范疇,因此,就算動物不是主角,或者整部作品涉及動物的比例不高,甚至作者本身不見得是要談論或反映人與動物的關系,但只要其中的情節內容有助于理解或反思動物倫理議題者,都會納入討論。這是何以例如吳明益的《單車失竊記》或J. K.羅琳(J. K. Rowling)的《哈利·波特》這些傳統上不可能被歸類為“動物文學”或“動物小說”的作品,仍在本書的討論范圍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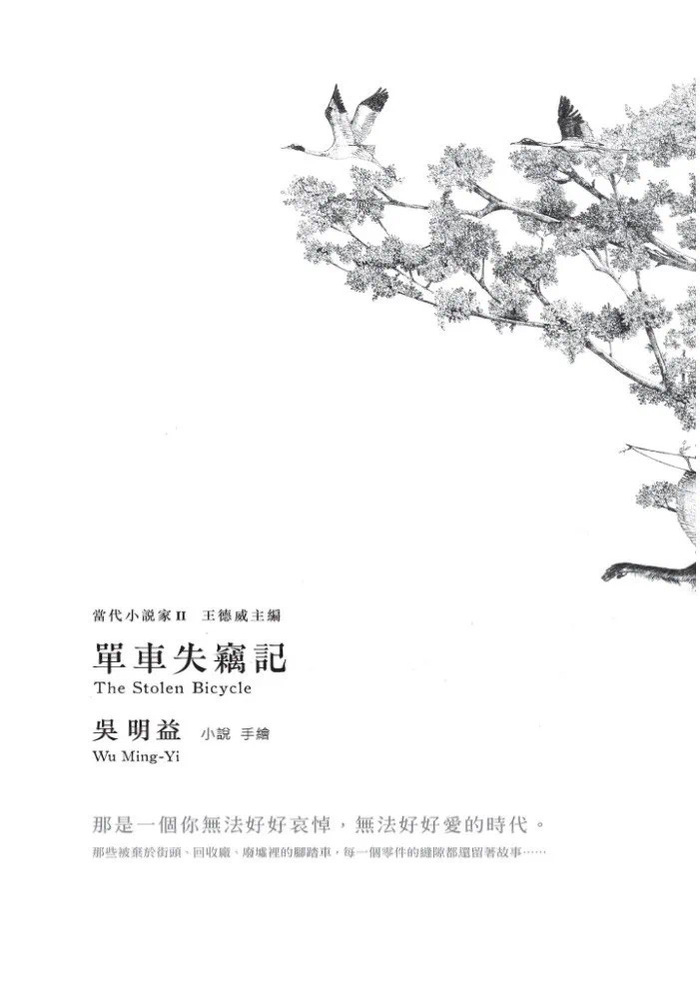
吳明益 著
麥田出版
動物權與動物福利
珍·古德(Jane Goodall)曾引用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的名言:“我們需要一種包括動物在內的無邊界的道德”,提醒讀者“我們目前對于動物的道德關注,實在太過于微不足道,而且,還相當令人困惑”。凱斯·桑斯汀(Cass R. Sunstein)在《剪裁歧見》(Conspiracy Theories and Other Dangerous Ideas)一書中分析了有關動物權利可能引發的各種爭議之后,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但是既簡單又嚴重的問題是,在太多時候,動物的利益不曾受到絲毫考慮。”本書立論的基礎,在于我們需要將動物納入道德考量的范圍,亦即以倫理學的角度,重省人對待動物的方式。而在討論有關非人類動物之道德地位時,有兩種時常被混淆、卻是基于不同甚至相對的哲學觀而來的概念,即動物福利(animal welfare)與動物權利(animal rights)。
動物福利
動物福利的觀點,主要是基于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的哲學觀,代表人物為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和彼得·辛格(Peter Singer)。邊沁駁斥一般人認為不需將動物列入道德考量的態度,主張“問題不在于‘它們能推理嗎’,也不是‘它們能說話嗎’,而是‘它們會感受到痛苦嗎’”。辛格引述邊沁的論點后,補充說明雖然邊沁于文中使用了“權利”一詞,但他要追求的是平等而非權利,邊沁所談的道德權利,“實際指的是人和動物在道德上應該獲得的保障;可是他的道德論證真正依賴的支撐,并不在于肯定權利之存在,因為權利的存在本身還需要靠感受痛苦及快樂的可能性來證明。用他的論證方式,我們可以證明動物也應該享受平等,卻無須陷身在有關權利之終極性質的哲學爭議里頭”。

至于邊沁與辛格所倡議的平等原則,是考量上的平等(equality of consideration),而非待遇上的平等。舉例而言,冬天晚上因為不希望孩子受到風寒而給孩子加一床被子和讓家里的狗進屋睡覺,雖然對待方式不同,仍可說是基于平等的考量。此外,效益主義既以動物是否能感受痛苦(suffer)作為給予其道德上的平等考量之關鍵,因此,在效益主義的概念下,人類進行的各種動物利用,都應以產生最少痛苦為著眼點,且將人與動物可能承受的痛苦同樣列入考量范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動物福利的立論觀點,是基于人類不可能完全避免動物利用的前提進行道德考量,因此一般以“動物福利”為倡議目標的立場,多半是指“人道”使用動物,最低限度應禁止“不必要的殘忍”。換言之,無論是科學研究、飼養動物作為食物還是將動物作為狩獵的對象,“只要做這些事所產生的整體利益,高于當事動物所承受的傷害”,并符合上述人道標準,效益主義是可以容忍某些動物利用的。
至于何謂人道或考量動物福利,有三種主要的看法:一是強調動物的感覺(feel),因此應免于讓動物處于過長與過度的疼痛、恐懼、饑餓等狀態,能感受到舒適;二是要滿足動物的生物性功能,使其能正常生長和繁衍;三是強調自然的生存方式(natural living),要能生活在合理的自然環境中并發展其天生的適應能力。這三個取向偏重的要點雖有不同,但在評估動物福利的優劣時,都會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之一。
動物權利
主張動物權利論的代表人物為湯姆·睿根(Tom Regan),相較于效益主義認為只要人道利用,并且不制造不必要的痛苦,就可以進行有限度的動物利用;權利論則主張,人類使用非人類動物在原則上即屬不當,因此探討什么程度的痛苦和死亡算必要,是未掌握問題核心的討論。因為既然根本不應該用這些方式使用動物,那么任何程度的痛苦或死亡都屬于非必要。也就是說,如果一件事情在根本上是錯誤的,它就不該有程度上的差異——如果用動物進行致死劑量實驗是錯誤的,這個錯誤不會因為由使用兩百只動物下降為六只就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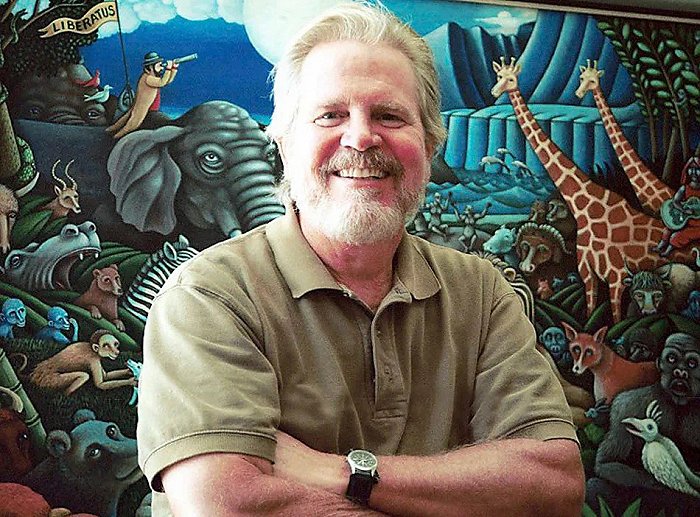
睿根認為,人與動物關系中真正“根本的錯誤”不在于動物受到的苦難,而是“將動物視為我們的資源的體制”,在這樣的觀點下,只是讓肉牛有多一點空間,少一點擠在一起的同伴,并不能消除甚至觸及這種將動物視為資源的基本錯誤,因此,若就農場動物的議題而言,它們需要的不是讓飼養方式更人性化,而是要完全解構農牧經濟體系。
權利論可說是對于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道德哲學的擴充,康德批評效益主義的哲學觀,認為效益主義的論點若推到極致,那么只要整體利益大于個體,不只動物可以被利用,人也可以被傷害。康德認為,人必須被當成目的本身,而不能僅被當作手段,不論利益多強大,傷害某人來讓其他人獲得利益必然是錯誤的。權利論則主張動物也應被當成目的本身。值得注意的是,康德的角度說明了他認為人對動物只具有間接責任(indirect duty),人對動物本身并無虧欠,這些動物本身也不一定應得任何特定的對待,只是人類處理它們的方式必須受到限制;但權利論主張的是人對動物本身有直接的虧欠或責任,也就是直接責任(direct duty)觀點,在這點上權利論與動物福利論的態度是一致的,只是在看待動物利用的問題時,權利論主張全面廢止(abolition),福利論則支持改革(reform)。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權利論的道德主張其實是陳義甚高的理想,要落實在現實社會中仍有相當的難度,畢竟要全面廢除動物利用或農牧經濟體系,絕非輕易可達成的目標。因此當代的動物權利運動(animal rights movement)有不少結合了動物權與動物福利的主張,“認為動物權利乃是一種理想事態,唯有不斷落實動物福利措施,方能實現。這個混雜的立場——動物權利是長期目標,動物福利則是近期目標——稱為‘新福利論’(new welfarism)”。對新福利論的倡議者而言,任何運動目標都是漸進式的,亦即,“今天若能爭取到較為潔凈的籠子,明天才可望爭取到空的籠子” 。
其他的倫理進路
此外,仍有許多從不同進路思考動物倫理的方式,例如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針對西方哲學長期忽視道德情感的狀況,重新賦予情感在道德行為中的重要性,主張以能力進路(capabilities approach)考量。生命個體需要一些能力,方能進行其生命所需的各種運作。因此,為了讓生命個體能順利地運作,活得像個生命,其能力應該獲得尊重,不可以被剝奪和傷害。換言之,對努斯鮑姆來說,讓動物的生命能夠順利運作的前提,就是所謂的“能力”,她列出的能力,就動物而言包括了生命、身體的健康、身體的完整(不受傷害)、感官與反應能力(不被剝奪)、情緒(不經受驚恐與剝奪安適的環境)、與其他動物互動玩耍等合適的生存環境。

努斯鮑姆的倫理觀特別強調情感的價值,認為人類之所以會具有倫理行為,是因為人有“憐憫之情”(compassion)。她主張情感并非一種“非理性的運動”(non-rational movement),相反,情感是具有認知要素的。努斯鮑姆依據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對憐憫之情的解釋加以修正,認為憐憫之情具有三個認知要素:⑴“分寸的判斷”(the judgment of size);⑵“非應得的判斷”(the judgment of nondesert);⑶“幸福的判斷”(the eudaimonistic judgement)。簡言之,憐憫之情成立的條件是,我判斷這個對象遭受了嚴重的苦難;此外,當事者不應承受這樣的苦難;第三,我們把受苦者納入自身生命計劃的一部分,當其處境改善時,我們自身也會感受到幸福與滿足。努斯鮑姆的倫理觀將人作為道德行動者本身的情感能力列入考量,從而讓情感與倫理的實踐可能打開一個不同的面向。

另一方面,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倫理哲學,則由“臉”(face; visage,亦有學者譯為“面貌”)這個關鍵字切入,主張人與他者的倫理關系,是由人類的“面貌”所展現的。其實對于動物的面貌是否足以讓我們將其納入倫理關系之中,列維納斯的答案是相當模棱兩可的:“我不敢說在什么時候你有權利被稱為‘面貌’。人類的面貌是完全不同的,而只有在那成立之后我們才發現某只動物的面貌。我不知道一條蛇是否有面貌。”但基本上他仍認為“我們不能完全拒絕動物的面貌。透過面貌我們才了解(譬如說)狗”。他曾如此解釋倫理的意義:
倫理作為第一哲學的三個基本重要概念:存在、空間(地方)和他者(別人)。所謂倫理,就是要漠視自己生物性的存在,超越掠奪空間的欲望,完完全全迎向他者。……游走于我之外的他者,他可能會騷擾我在家的安寧,而我對他卻毫無制約的能力。雖然我對這位陌生人一無所知,但我們之間可以產生一種既非融洽和諧,也不是爭斗齟齬的關系。
此處的他者,能否由人類他者延伸為動物他者,從而在人類掠奪空間的欲望中,保留一個不必融洽但也無須爭斗的可能?對于當代人與動物爭地的緊迫關系,列維納斯的倫理學,無疑提示了一個可能的方向。
綜上所述,無論是睿根追求核心價值探問的權利論;辛格用量化實踐的方式進行評估的效益論;努斯鮑姆對“憐憫之情”的重視,在道德行為中賦予情感重要性的主張;或是列維納斯對于將他者的臉列入倫理考量的價值觀,都各有其不容忽略的意義和價值。阿馬蒂亞·森(Amartya Kumer Sen)曾在《正義的理念》(The Idea of Justice)一書中引用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看法,強調倫理是一種實踐,也因其是一種實踐,就不只涉及價值判斷,還包括哲學、宗教與對事實的信念。換言之,倫理追求的不是至高無上的絕對真理,而是在現實上可行的方案,因此他建議:“涉及現實抉擇的實踐理性,需要有個框架以對于各種可行方案的正義進行比較,而不是指出一個不可能被超越的、卻很可能不存在的情境。”在面對這些立場各異的倫理觀時,這或許是個相當實際且中肯的建議。
來源:三輝圖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