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期主持人 | 林子人
作為高考中分值高達150分的三大主科之一,英語在高考中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可近年來英語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卻有些尷尬,以至于社會上頻頻出現“高考取消英語”的呼聲。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許進認為,90%以上的人在日常工作中用不到英語,讓大家花費那么多時間去學習一門“工具性的知識”,有點得不償失。建議孩子去學習音體美這種“對身體對健康對成長有好處的知識”。
前兩日讀卡爾·克勞的《四萬萬顧客》,書中對民國上海的描述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上海的中國男孩個個都擠破腦袋想進外國公司,好比洛杉磯的美國男孩都想闖好萊塢一樣。”要入職外國公司,英文讀寫和口語表達是必備技能之一,上海每個有此打算的男孩都會盡早開始學習,再不濟就先掌握能夠給公司留下好印象的單詞,只學那些最實用的詞語,先拿下工作機會再說。這種將英語能力和個人前途緊密相連的觀念,我作為一個“90后”其實非常熟悉。
事實上,每當開始強調“對外開放”或“與國際接軌”的時候,人們就仿佛發自本能地重視起英語學習來。我小時候家里最早出現的英文書是一本英漢詞典和舊版的《新概念英語》,當時我媽媽在自學這套教材。她一直很得意的一件事是,90年代末去美國考察時遇到了一個問題,她曾代表整個考察團用蹩腳的英語與美國人交涉成功。她也一直羨慕許多上海同行能夠不用同傳直接參與國際會議,于是在我讀書的時候她總是百般強調一定要學好英語。我相信許多90年代出生長大的城市孩子都曾肩負過這樣的期望。英語能力還聯系起了個人前途與國家的國際化發展——我記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前夕都曾號召市民學習英語常用語。
近年來,隨著國際化的發展和中國國際地位及發展水平的提高,漢語作為國際交流語言的地位有所提升,在“全世界都在說中國話,孔夫子的話越來越國際化”的民族自豪感中,學習英語的價值在遭遇質疑,高考英語改革的呼聲就是價值觀轉變的一個信號。之前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訪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但漢松,他提到大學英語系如今有一種“濃厚的末日感”,隨著越來越多優秀的學生不愿意就讀語言類專業,中國大學的英語系會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在將來,學習英語真的會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嗎?
英語學得好是小時候對現代都市女性的一種想象

潘文捷:我從小學五年級開始學英語,因為不怎么上心成績一直很差。直到班上來了一位十分有魅力的英語老師,氣質非凡,談吐利落,打扮時尚次次不重樣。第一次上課是發之前的試卷,我分數很低,老師遞來的時候笑了笑什么也沒說,我卻莫名感到了丟臉。從此發憤圖強,在家也好好聽錄音做練習,成績也慢慢好了起來。說實話,其他科目的老師也可能是穿著涼拖上課的大叔,唯獨英語老師往往都是洋氣的、自信的,是楷模一般的女性,這樣的印象一直在腦海當中存留了下來。英語學得好確實是我小時候對現代都市女性的一種想象。
徐魯青:我小時候也最愛上英語課。英語老師確實比其他科看起來更時髦一些,常常很親和也很好打交道。課堂上除了學英語,還會和我們聊國外的流行文化。我第一次知道“gay”這個單詞是從初中英語老師那里,她告訴我們是什么時全班都在起哄,男生們開始壞笑。我印象很深的是,英語老師告訴我們歧視gay是錯的,在當時是很少有老師會去說這些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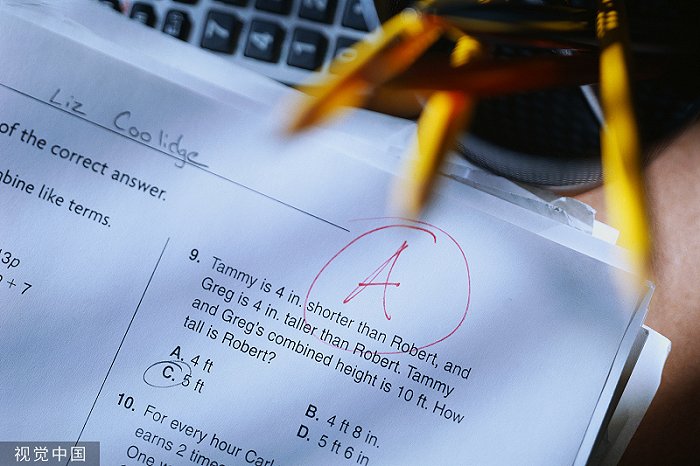
林子人: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的一個好朋友去上了英語培訓班,我們的課間娛樂活動就變成了她來教我和另外一個小伙伴英語單詞。從各種水果到人體器官,我們跟著她一遍遍地練習發音,還相互比賽誰記得更快。競爭心被激發以后,我求著爸媽也送我去上英語培訓班,所以我和當時很多小學同學相比早一年學英語。我的中學以外語教學為特長,英語老師會用各種生動的教學方法讓英語學習更有趣好玩,比如課前演講、角色扮演、電影配音比賽、演話劇等等,英語就成了我最喜歡也學得最好的科目。
《黑箱》作者伊藤詩織曾說過,她覺得自己在說英語和說日語的時候感覺完全不同,說英語的時候更自信篤定,更有自我主張。在這一點上,我和她挺有共鳴。仔細想想,可能和我中學時接受的英語教育有關:英語課非常強調口頭表達能力,英語文法本身重視清晰的邏輯與結構、論點與論據,會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在使用英語的時候更直接清楚地表達觀點,同時也反過來影響了我的漢語寫作與表達。
語言不只是工具而已,還是一整套文化和思維方式
潘文捷:語言不只是工具而已,還是一整套文化和思維方式。把一種語言當做工具,那可真是把路走窄了。我接受過譯員的訓練,非常了解的一點就是,譯員是可以很容易做到把字詞翻譯出來,但是很可能并不知道這個字詞背后真正的涵義。可以描述冰山一角,卻難窺其全貌,這樣也會導致翻譯出現問題。
學者孫歌的《從那霸到上海》一書收錄了《竹內好兩次關于翻譯的論戰——兼論翻譯的主體性與政治性》一文,她給出實例,說竹內好屢次批評日共翻譯的毛澤東著作。例如,其中有一段話,竹內好翻譯成“正是這主要的方面,才是在矛盾中起指導作用的方面”,而日共譯本為“所謂主要的方面,是指在矛盾當中起主導作用的方面”。聽起來沒有什么大問題吧?至少也沒有什么譯錯的地方啊,可是竹內好卻很不喜歡日共的譯本。他解釋說,這個譯本的態度是:世界已經完結,讓我們來說明吧。是一種靜態的說明。可是竹內好自己的譯本的態度則是,像毛澤東的《矛盾論》這樣的著作,本來就是應該向那些認為世界應該變革、為此我們需要發現矛盾的人推薦的,應該有一種躍動著的主體表達。孫歌看到,竹內好的毛澤東和日共譯本中的毛澤東,前者是戰斗的、未完結的,后者卻是絕對化的、固定化的、神格化的。沒有想到吧,幾個字之差,背后的問題卻有那么深刻。說實話,如果只是把一種語言當做工具,這樣看似沒有錯卻實際上犯了大錯的譯本就會存在,而我們甚至不會發現其中的問題。
徐魯青:歌德在面對語言逐漸失去多樣性的時候說過,“沒有一個單語者真正了解自己的語言。”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好好想了想一下自己,普通話和方言是母語水平,英語雖然做不到但也能讀能說,或許勉強蒙混過關不算個“單語者”。和方言相比,英語更給了我審視中文的一扇窗,中文里許多詞匯可能因為同聲字,或者因為概念劃分本身比較模糊,常會出現概念的混淆,而用英語可以做到更好的澄清。比如在我們談到權力(power)和權利(right)這兩個在公共討論中常出現的關鍵詞時,因為口頭表達很難區別,人們在書寫使用上也常混淆使用,進一步使得這兩個詞本身的概念更不清楚了。權利是人生來享有的,而權力則是被授予的,應該得到監管和控制的,這兩者的區分或許在英語中就更明顯。
從更實用的操作上來說,翻譯和同傳也很難深入到個人生活中,再加上翻譯的薪酬又是那么低,很多句子難做到精準的校對,哈貝馬斯書里的“后自由主義”(Post-Liberalism)甚至曾被翻譯成“郵政自由主義”。世界上或許有70%的信息都是由英文寫作與傳遞的(必須承認這是語言多樣性的不幸),如果失去了英語這個“工具性的知識”,只是看中文世界的消息,是不是很有可能以偏概全,進而影響到人的思維呢。
葉青:但凡嘗試過文學或影視作品翻譯的人,都知道翻譯技術的局限性。翻譯是一項腦力活,機器再怎么學習,是無法理解一句話想表達什么,再經過思考,用符合人物口吻/語境的詞句表達出來的。譯者陳以侃之前在回應毛姆作品《紳士肖像》譯文爭議時談到,“翻譯翻的是一個意圖,一個概念,一個畫面,它和某種特定語言在字面上的聯系是偶然的,是牽絆,一定要盡可能忘記它。”這句話我很認同,而機器翻譯恰恰著重的就是在字面上的聯系,出來的譯文是死板的、千篇一律的、喪失了原文韻味的。翻譯技術可以作為輔助手段,但這不是說使用者就不用再學習英語了,恰恰相反,作為使用者的我們需要更高的語言水平,才能甄別出機器的不足之處,加以改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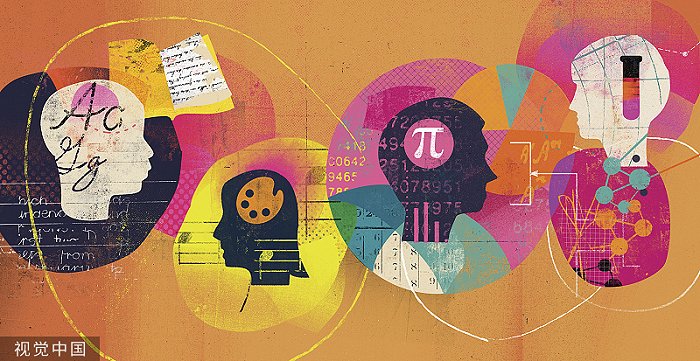
林子人:雖然我大學讀的是英語系,但我當時的確是心存“英語只是工具”、“以后絕對不想做和翻譯有關的工作”之類的心思。諷刺的是,我現在的工作倒是有很大一部分內容和翻譯有關(苦笑)。在遇到采訪非英語國家的采訪對象的時候,光是“雙語能力”還尤嫌不足,恨不得自己有“多語種能力”才好。根據我的經驗,目前的翻譯/同傳技術再先進都會丟失一部分信息或存在錯譯情況,其有效性是遠不如自己直接用英語交流的。多掌握一門語言,你就會多一種信息和知識獲取的渠道,而弗朗西斯·培根早就告訴過我們“知識就是力量”。所以,包括英語在內的外語是一種非常寶貴的技能,在可預見的未來我不認為它的重要性會降低。
董子琪:時過境遷啊,當年鼓勵學外語的時候不是說多掌握一門語言就是多一種靈魂嗎,人們不希望靈魂的充盈嗎?語言就是思考的介質,不僅英語需要掌握,別的語言也多多了解才更能了解這個世界的豐富與復雜。就以英文寫作的華裔作家來說,以前聽一些批評家說英文表達是次要的,特別的經驗傳遞才是主要的,可這也是一種語言工具主義的思考方式,我還是會懷疑某些以簡易英文寫作的華裔作家能否精確傳達自己的思考和感受,而不陷入粗陋幼稚、過度戲劇化的圈套——至少我在讀那些作品時發現驚奇感大過美感,對語言的要求已經喪失殆盡了,這應當是海外華語文學的樣貌嗎?就像我們會嘲笑迪士尼對中國氣與八卦的淺顯理解一樣,對于文化的系統性理解是需要通過語言學習才能達成的,看起來迅捷的替代物只能接近而不能真正抵達。
姜妍:所謂語言是不是工具要看從什么層面理解吧。如果從文化研究層面,當然每種語言都有自己的特點、藝術性、價值等等,比如納博科夫精通三種語言,俄語、英語、法語,他在寫作生涯里面也是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變化,在這三種語言中間切換。但是他也在采訪里說過,他認為英語是一種生硬、不夠自然的語言,用來描述日落或昆蟲沒什么問題,但當需要表述貨棧與商店之間的捷徑時,英語就難以掩飾其句法和日常用詞的貧乏。他說,一輛老式的勞斯萊斯并不總是優于普通吉普車。
從現實溝通層面理解,我覺得英語有作為工具的一面存在。在一些國際化的項目中——比如我很喜歡的古典音樂和網球——圈子里可以說沒有人不會英語,因為大家需要便捷地溝通,剛好國際化程度最高的語言是英語,所以就變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這些音樂家也好,網球選手也好,很多在年幼時就去到國外的音樂學院或者俱樂部里面求學,成年以后又一直全世界演出和打比賽,所以很自然地需要一種方便的溝通交流工具,但除非是自己對語言有興趣,否則不會說要去把英語研究得多透徹多好。在網球場的賽后發布會和采訪中,你如果想去挑球員的口音或語法錯誤一定有的挑,但人們會忽略掉這些,李娜一樣可以用英語開玩笑,引得大家會心一笑。
工具主義的學科建設思維會影響未來幾代人
陳佳靖:一個語種對于外人來說或許只是交流的工具,但母語者卻將其視為民族身份、歷史與文化的載體。即使再簡單易學的語言,在我看來它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奇跡。很多人只將語言看作是由一些符號拼湊出來的代碼,這是對語言非常可悲的理解,這種觀念正在使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小語種被邊緣化,走向衰落和消亡。一個很諷刺的例子是,每年無數人去冰島、瑞典等北歐國家看極光,還有人自稱是精神上的北歐人,卻找不到幾個人在學冰島語、瑞典語。人們會說,在當地說英語就夠了,這等于在說,我們的好奇心只有這么多。
上學的時候我的英語學得還不錯,但當時只知道學好了能考高分,不懂學習這門語言的內涵。反而是成年之后,當英語學到了一定程度,實現了所謂的工具性之后,才發覺我學到的英語是多么匱乏。我想“90后”普遍都有一個轉折期,就是突然發現我們過去學到的很多英語固定用法到了英美國家的真實環境里完全不適用。你會發現老外們平時不是這么說的,而且他們還會說很多你聽不懂的俚語和新鮮的流行詞。世界在變化,語言也會跟著變化,學習難道可以停下來嗎?即使站在功利性的角度,我們學到的真的夠用了嗎?翻譯軟件真的夠用嗎?我對此非常懷疑。
徐魯青:政協委員的提案是從日常工作中用不到就很浪費這個角度來說的,這樣來看,基礎教育階段難度極高的數學物理不是更大的“浪費”嗎?我高中是理科生,大一學的是統計,現在雖然完全用不到這些具體知識,但它們始終在影響著我的思考方式。
姜妍:其實我關心的不是“有用”或者“沒用”,而是這里面體現出來的是一種學科建設的思維,這個思維會在若干年后影響一代人,甚至更久遠。比如,有時候我會想,假如說中醫在今天的課程設置里是一門必修課會怎么樣?假如體育課里考的不是800/1000米而是太極拳會怎么樣?其實是這樣的某些選擇,會造成一些影響和變化。
董子琪:但漢松老師說的語言學習的濃厚末日感好有意思。讓我想起同樣是講英語系故事的電影《文科戀曲》(不過,影片中的英文系應該相當于中文系),大齡失意的男主回到系里跟年輕學妹交流時說過一句話,“我兼修了英文和歷史專業,就是確保我將來找不到工作。”這不就是在區分有用與沒用的知識嗎?這種自嘲在“沒什么用”的院系里相當常見。在國外讀東亞文學更是經常被問到“學這個有什么用啊”的問題,那時候就回響起“為了確保我將來找不到工作”這種回復。

在小說《斯通納》里,斯通納最開始學的是家里人希望他學的農學,之后背叛家族期望選了沒什么用的文學系,父母在他畢業時才知道,他將不和他們一起回家了。這種轉折是極其殘酷的,聽到兒子的最終決定后,他們在黑暗中痛苦地啜泣,仿佛這是對于農民身份和有用前途的雙重背叛。我很熟悉《斯通納》中描寫的美國中西部景象,因為地點就在密蘇里。冬季霧氣彌漫的校園,長長的顯得孤寂的走廊,那也是我在被問“學這個有什么用”的問題時所看到與感受到的。小說里斯通納的朋友諷刺說,學院是留給那些老弱病殘的庇護所,而也許庇護與安撫正是它存在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