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徐魯青
編輯 | 黃月
我們與老虎的交集不僅僅在新年日歷與紅包里,老虎從未間斷以或真實或隱喻的方式進入我們的生活。2021年4月,野生東北虎“完達山一號”闖入黑龍江省密山市某村莊,受到驚嚇后撲倒一位村民,后被麻醉控制。同樣是4月,東北虎豹檢測系統在吉林琿春拍攝到野生東北虎追逐梅花鹿的鏡頭,這是國內首次記錄到野生東北虎捕獵狀態,畫面中東北虎身型壯碩,矯健地躍過枯枝,朝獵物飛速奔去,雖然只是在鏡頭前一閃而過,卻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與野生東北虎捕獵視頻相對照的是,在賀歲檔電影《東北虎》中,19歲的蒼老東北虎被困在鶴崗動物園的籠子里,沒有開闊的林地,早已喪失了狩獵的技能,是電影里絕望生活的喻體。
不只是老虎,許多瀕危的動物們都在動物園與國家公園里被人工圈養育種,野生數量極少,保護工作道阻且長。在思考動物保護現狀的實然問題外,反思動物權利的應然性至關重要。曾有許多學者指出,人類對野生動物的義務為“由它們去”,但人類與動物真的可能做到各自獨立、互不干涉嗎?新近出版的《動物社群》一書為我們展望了一種新的人與動物關系的視野和以及人類與動物交往的準則,讓我們看到人與動物之間隱秘而不可避免的交集與互動,重新思考自然的邊界與動物的權益。

[加拿大]休·唐納森 著 王珀 譯
新民說|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2
動物權利的哲學論爭:動物是目的還是手段?
我們對動物的態度并非無源之水,而是被眾多思潮所影響塑造的。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影響了西方哲學家審視動物與人的關系,他將大自然中的萬物排出了高低秩序,等級鏈條中人類是最高等的,其次是動物,再次是植物。在《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寫到,“自然界原本是一個等級結構,理性能力低下者就是為能力更強的人而存在的,因此植物為動物而存在,非理性的動物為了人而存在。”
經過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理性成為人類的新信仰,亞氏的觀點也被進一步認可,人們以機械方式看待自然,在此背景下,笛卡爾論斷靈魂是人類特有之物,沒有靈魂的動物和機器沒有區別,這個觀點為后來大量流行的動物活體實驗鋪就了合法性基礎,人們如同修理機械般對待實驗動物,科學進步的步伐之下遍布動物尸體。對動物保護運動起到重要作用的《動物解放》一書寫道,“據詹森教派的記載,那時的一些實驗者滿不在乎地鞭打狗,而且譏笑那些對狗產生憐憫的人。他們說這些動物就像時鐘,它們挨打時的哀嚎只是像觸動一根小發條產生的噪音。”


關于動物權利的重要爭論之一在于,什么決定了生物享有基本權利(例如避免痛苦的權利、生命權等),是人與非人的物種區分嗎?物種分類始終找不到完美的生物學標準,縱使是最被學界廣泛認同的“生殖隔離”,也無法解釋同屬智人的皮格米(Pygmy)女性因盆骨尺寸過小不能與瓦圖西(Watusi)男子繁衍后代的現象。分類學家也發現,人與黑猩猩之間的差別,遠小于黑猩猩與大猩猩之間的差別。正如哲學家德格拉齊亞所說,“訴諸物種的最大困境之一就是,與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類似,它并沒有為把‘我們’從‘它們’中分離出來提供更多證明。”
澳大利亞倫理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動物解放》一書中著重批判了上述物種主義觀點。辛格是功效主義(Utilitarianism)哲學家,功效主義相信 “最大的利益”是衡量良好或道德行為的唯一標準,辛格對功效主義的重要突破是將“最大利益”的計算從人類范圍擴展到所有具有感受能力的動物,他強調,不是物種也不是理性,而是對痛苦的感受能力,構成了一種生物能否享有基本權利的關鍵。《動物解放》對動物保護運動影響深遠,許多公司在該書引發轟動后取消了動物實驗,化妝品公司不再為了人們臉部的保養而弄瞎兔子的眼睛,養殖場也在壓力之下改善了動物飼養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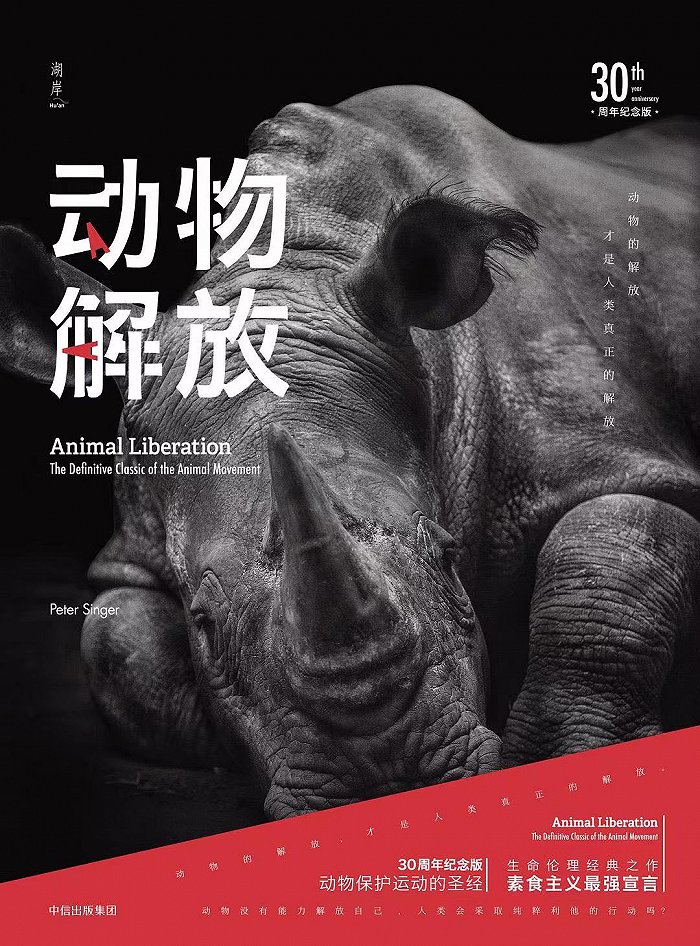
[澳] 彼得·辛格 著 祖述憲 譯
中信出版社 2018
在動物保護領域,另一個重要學者是哲學家湯姆·雷根(Tom Regan),雷根對辛格的功效主義立場提出了不同想法。雷根認為,在功效主義追求整體效益最大化的立場下,生命成為提高效用的工具,過分偏重總體利益的傾向也導致少數群體的利益被忽視。雷根更支持康德的道義論原則,即行為好壞在于其所依據的原則和動機,結果并不重要,比如在康德著名的說謊案例里,即使不騙過歹徒會傷及無辜(行為后果),人也應該出于道義論原則不說謊。然而,康德的問題在于他認為理性能力是擁有道德權利的前提,動物沒有理性,所以只有人是目的(end),動物作為手段(means)存在。這無法解釋現實中很多人類也并不存在“理性”,比如嬰幼兒、智力殘障人士、老年癡呆患者等。雷根修改了康德的理論,將“生命主體”(Subject of a life),即擁有感受能力的生物,取代了康德的“理性主體”(Subject of rationality),動物在他的理論框架下也是享有道德權利的主體。
人類與動物關系: “由它們去”是對野生動物最好的保護嗎?
在《動物社群》一書中,哲學家休·唐納森與威爾·金里卡認為上述經典動物權利存在一些缺陷,其中重要的一點是強調消極權利,卻忽視了動物的積極權利。比如主流動物保護的觀點主張 “不干涉”是對動物最好的保護方式,動物保護的目標是盡量讓動物在沒有人類影響的環境中自由生活。上文提到對動物權利有深遠影響的哲學家也持此觀點,彼得·辛格認為“只要消除了我們自己對其他動物不必要的殺戮和虐待,這就夠了”,而且“我們應當盡可能地遠離它們”。湯姆·雷根也曾總結說,人類對野生動物的義務為“由它們去”。
人類與動物真的可能做到各自生活,互不干涉嗎?唐納森與金里卡質疑這樣的動物保護思路,他們認為動物與人的關系緊密交織,規避人類影響的方案并不現實。縱使不直接捕殺或狩獵,人類活動帶來的氣候變化、破壞動物的食用物種等行為仍會影響野生動物。另外,野生動物的棲息地遠比我們想象得廣闊,《動物社群》中提到,1991年,有科學家在狼的身上安裝了信號跟蹤它的活動范圍,在兩年時間里,狼的足跡遍布40000平方英里,大約是16個上海的面積,這些區域中分布著大量公路、鐵軌、電力線、國界線等人類設施活動。時不時闖入我們視線范圍內的東北虎,棲息地的面積也廣至10000平方英里。動物從來不是也無法只生活在無人涉足的原始之地,它們與人類的生活軌跡始終互相關聯,難以分割。
《動物社群》認為,我們所需要的動物權利論必須能處理人類與動物間不可避免的交集,為互相牽涉建立規則,而不是試圖讓動物生活在不被人類涉足的荒野之中。基于人類同動物緊密而多樣的關系,政治哲學出身的金里卡與關心動物倫理的唐納森合作,嘗試將公民理論應用于動物權利問題。具有群體性差異的人類公民身份理論在學界早已建立,同樣的分類法也可以拓展至動物問題上。兩位作者指出,人們對公民身份理解過于狹隘,對動物與人類社群的關聯方式也理解不足。事實上,動物與我們的關系比野生/家養動物的二元劃分多樣復雜得多。家養動物、城市邊緣動物、野生動物與人類有不一樣的交往,也意味著人類對這些動物承擔不盡相同的義務,例如對圈養幾千年而依賴我們的飼養類動物,我們應該承擔許多積極義務來保障它們的生活,而對待不請自來與我們共享城市空間的野鴨與老鼠,我們的義務則更多在避免傷害。
《動物社群》以“關系”為中心,劃分了家養動物、城市邊緣動物與野生動物三個類別,如果類比公民理論中劃分的三種身份,分別是公民、境內少數群體以及他國國民,三種人類社會身份可以和三種動物的劃分互相比照。家養動物世世代代被圈養,已經依賴人類,應該享有部分公民權利;城市邊緣動物類同于選擇來到人類居住區的移民,與我們共享城市空間,但并未參與進我們的公民合作體系之中;野生動物則應被看作他國國民,它們在自己的領土上組成了獨立的主權社群,外部社群不應該侵犯,人類既不能破壞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如不正義的國家入侵,也負有保護和援助野生動物的積極義務——在主權體系中國家間互惠關系的一部分。
縱使《動物社群》中的觀點在學界仍有許多爭議,在基本的動物權利仍無法保護完備的當下似乎也“過于超前”,卻能啟發我們重新反思與動物的關系。縱觀歷史,人和動物的聯結深切久遠,深嵌各自的生命脈絡之中,自最古老的巖畫起,動物就一直存在于人類的藝術、科學和神話里,人與動物的伴侶關系更是歷史悠久,河北省徐水縣就明確發現過距今一萬年左右被馴化的狗骨。用環保主義者保羅·謝潑德(Paul Shepard)的話來說,“是動物,使我們成為人類。”
參考文獻:
《動物解放》[澳] 彼得·辛格 著 祖述憲 譯 中信出版社 2018
《動物社群》[加拿大] 休·唐納森 著 王珀 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2
郭鵬 | 動物倫理與立法:幾種誤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