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尹清露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ChatGPT的廣泛應用、諾獎頒給人工智能領域學者、美國大選受DeepFake影響……即使你不太關注技術話題,也不得不承認,人工智能已經深度卷入了我們的世界。然而,看著“AI”熱詞滿天飛,大科技公司占據新聞頭條,我們到底要如何揭示人工智能的真正意義,以及人類身處其中的位置?
《再見智人:技術-政治與后人類境況》作者、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吳冠軍認為,在技術呈指數級發展的當下,缺乏的是政治智慧;對人工智能的信任危機,其實根植于人類彼此的信任危機。書中分析了技術加速、智慧缺失帶來的困境:大量“無用階級”失業者不再被社會需要,大國互相爭斗,“智人”的“智”不再名副其實,人類本身也成為了人工智能文明的序曲。
界面文化對吳冠軍的專訪,不僅涉及了“AI與人類的創造力如何不同”等一直被討論、從未有答案的抽象議題,也從特朗普與馬斯克的聯合、諾獎委員會的選擇、學歷貶值等近期熱議的話題出發,步步逼近那條最終的道路:今天,我們必須呼吁一次政治智慧的迭代,如果我們以AI為啟發,更新思維范式,不再止步于人類主義的固有框架,那么,智人便有一線生機,在新的地平線上看見自己。

01 人不只是不信任AI,彼此也不信任
界面文化:與尤瓦爾·赫拉利側重于人工智能的信息與聯結不同,《再見智人》側重人工智能的“技術-政治”面向。為什么研究人工智能需要強調政治?
吳冠軍:巧合的是,我和赫拉利的新書都是在9月10號出版,我們都是1976年生人。《再見智人》和《智人之上》兩個書名也具有鮮明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赫拉利作品的原名是“Nexus”(聯結),就像我在那本書的推薦序中所寫,這個關鍵詞恰恰有一個具體的政治面向。
亞里士多德說,men by nature are political animals(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動物)。“政治”的詞根在希臘語里是polis,指的是城市,人是在城市生活的動物。亞里士多德認為政治是人的定義性特征,政治對智人來說是唯一關鍵的、自我界定的向度。意味著人能夠以共同體群居,而不是獨立生存。所以,政治不是很多人理解的暴力爭斗,這恰恰是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現。動物為了交配殊死爭斗,這不是政治,而是政治的反面,是政治向度的缺失。
現在有了人工智能,我們就更清楚智人是怎么回事了。一種可能是我們離智慧越來越遠,智人本身被邊緣化,也就是“再見智人”了。年輕人傾向于躺平和自我放逐,畢業找工作時,發現自己還比不過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盡職盡責、知識面廣、工作效率又高,信息整合能力也很強。
另一種可能是,我們在新的地平線上重新看到人之智,也就是另一重意義的“再見智人”。在人工智能已然超越人之智能的那些領域,我們是否能夠發展出與之合作的方式?還是堅持站在人類中心的位置拒認其超出人的智能?可是很多人就是這么想的:我不讓你發展,因為我怕你比我更強。為了擺脫這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模式,我們需要智人獨有的智慧,那就是形成共同體的智慧。雖然目前人工智能已經很厲害、但讓它提出解決當下中東問題或俄烏沖突的方案,恐怕它仍力所不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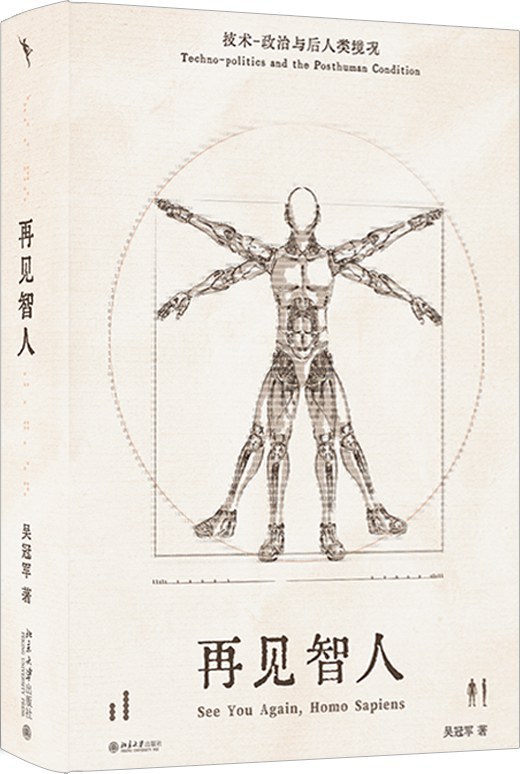
吳冠軍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4-9
“再見智人”是一個雙關語:一個是和智人say goodbye,智人文明是可能會結束的,沒有本體論保證使它會一直持續下去,人類可能只是技術發展的一個階段而已;但是,人類也可以發展出或重新拾起人工智能仍然沒辦法取代的能力,“再見智人”可以指see you again。“技術-政治”這個詞很好,技術和政治是人類的兩根拐杖。雖然赫拉利在書中沒有明顯使用“政治”詞匯,但是“聯結”就是一種政治性。聯結意味著通過各種方式互動,無論是通過神話故事還是信息技術,聯結一旦中斷,更高層次的文明發展就會變得困難。
最近人工智能專業很熱門,政治專業卻非常邊緣了,外語專業也似乎不再重要,因為AI翻譯足夠強大。但我們面對的一個核心問題是:以后要如何與這些“后人類”合作和對話呢?我認為,被逐漸忽視的政治學恰恰是應該重視的。政治沒有終極答案,它不斷面臨新問題,也不能簡單地抄襲或套用以往的答案,永遠是一個持續迭代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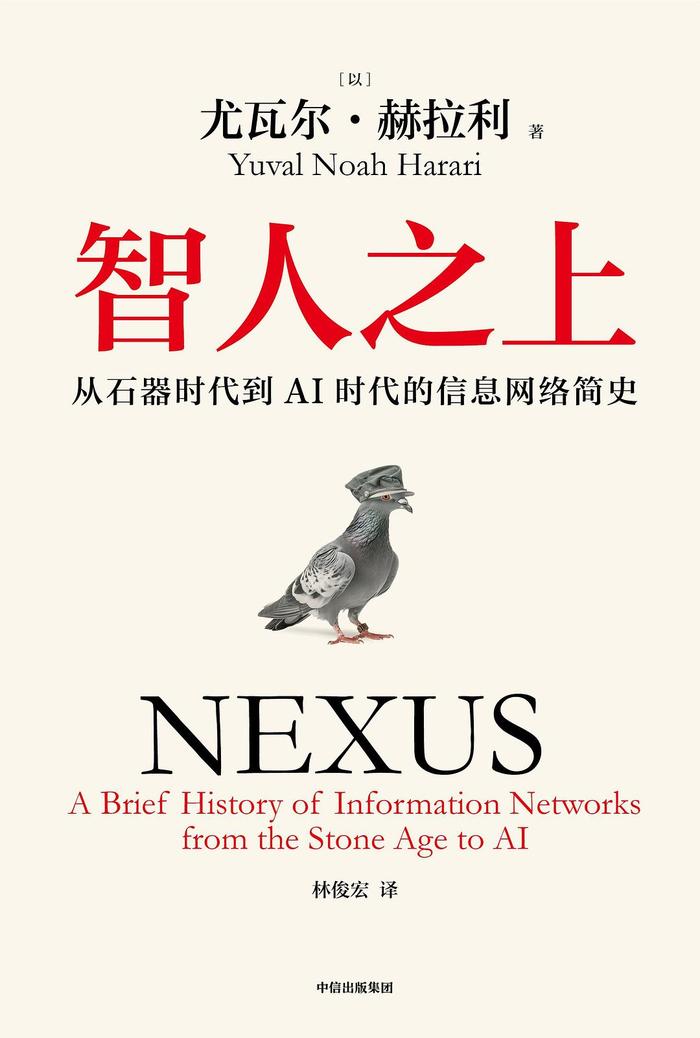
[以色列] 尤瓦爾·赫拉利 著 林俊宏 譯
中信出版社 2024-9
界面文化:一方面AI技術非常先進,另一方面我們的思維模式還是互相爭斗。這讓我想到你在書中強調的“信任”,而信任其實是一個沒有理性支撐的跳躍。你為什么會這樣強調?人工智能這一新成員的加入,會怎樣影響信任缺失的現狀?
吳冠軍:很多人提出要做trustworthy AI(可信任的人工智能),或者停止開發AI,因為AI內部是一個黑箱。但是我們不妨想想,人類的大腦也是黑箱,AI的人工神經網絡作為一種仿生學概念,模擬的是人類腦神經網絡,人腦中有大約800億個神經元,它們通過電信號相互交流。腦科學能夠監測到大腦皮層中哪些區域很活躍,但是無法還原為腦海里在想的內容。
我們不斷從新聞中看到這種事情:在西方社會,一個人昨天還是你的同學,今天拿起槍在校園里掃射。美國政府最怕的不是群體作案,那樣還有辦法監控,最怕的是一個個腦海黑箱式的“獨狼”。

可是,人類是否因為大腦中的黑箱而停止合作了呢?并沒有。背后的原因就是信任,我稱之為一種政治性智慧。信任這件事并沒有基礎,如果我能掌握你100%的信息,那我就是上帝了,而上帝是不需要信任他人的,只有人才需要相互信任。可是,沒有任何本體論來保證人的想法一定符合哈貝馬斯所說的sincere(真誠)和communicative(可交流的),我們只能對信任他者做出一個躍步(leap)。
然而今天,無論是全球層面的國際政治,還是私人層面的夫妻關系,政治智慧都變得很稀薄。我們在面對人工智能時還能擔得起“智”人的身份嗎?我們不只是不信任AI,我們彼此也不信任。
02 人工智能發展出慢思考是極有可能的
界面文化:雖然人類和人工智能都是黑箱,但如你在書中所寫,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黑箱,比如人類懂得愛和創造;與人工智能相比,人類有一種“本體論上永遠無法被完全實現的潛能”。關于這一點也有不同觀點,比如赫拉利認為,機器也可以進行文化創造。你對此怎么看?
吳冠軍:我們稱人類的大腦為“濕件”(wet ware),既不是硬件也不是軟件,而是一團肉。它有一個關鍵的有趣之處,也就是可塑性(plasticity),大腦雖然被認為利用率已經很高,實際上仍有很大的可塑性。而人工智能模型完成預訓練后,它的能力也就基本定型了,你要么重新再訓練一個更高級的模型,比如從GPT-3到GPT-4。

所以,即便人類在知識廣度上差人工智能很遠,但是我們擁有一個獨有的潛能,那就是可以不斷地再生成、再組織。舉個例子,盲人失去視覺輸入后,視覺神經處理區域會逐漸變得不活躍,但即使是遭遇了這樣的創傷,大腦還是會以積極的方式去應對,比如重新調用觸覺信號,讓你經過訓練后能讀懂盲文,這對視力正常的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再比如對文科學者來說,年紀大了以后,盡管生物學意義上神經元總是在變少,由于此前的積累與相互激發,還是進一步能輸出更好的想法。
從生物學上來說,個體在演化過程中不是很重要,演化是一種快速殘酷的迭代過程,生完孩子基本就完成了DNA傳承的使命。但是,由于人類具有再學習和不斷重新訓練自己的能力,人類就擁有了一個獨特之處——個體生命變得非常重要,而不是局限于簡單的生物傳承。除非你放棄自己大腦的潛能,躺平做一個吃貨——那就相當于早早結束了自身的演化可能性。
界面文化:人工智能是否能夠進化出更多潛能?你在書中談到,人工智能的大語言模型是一種前意識的“快思考”,只有人類能夠“慢思考”,但是隨著近日OpenAI開發出o1模型,人工智能也能進行慢思考了。
吳冠軍:這種情況相當有可能。2022年之前,我們都不曾想到,人工智能竟然能具備如此強大的生成能力。有時我們取笑人工智能數學不行,比如有次它認為18.18大于18.8,錯誤地將18視作兩位數。但問題是人類普遍也是數學不行,人類最擅長的思維模式就是快思維。我們看到長得像蛇的東西會認為很危險,先逃跑再說;有人對你說了有攻擊性的話,你馬上會感到不快,如果對可能的威脅與危險沒有快思維,根本就活不下來。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強大,就在于它用快思維的方式,在很多方面能做到人類只能通過慢思維才能做到的輸出,尤其是文本處理方面。你讀完一本書后寫書評,需要在腦海中提煉書的核心內容,而人工智能可以將復雜的思維過程轉化為迅速的輸出。人類的快思考是無法處理抽象的文字,然而人工智能的快思考能夠直接針對具體的象征性符號,直接處理抽象語言。從這方面上來看,它可能真的是一個更厲害的species(物種),而o1這樣的模型顯示出人工智能發展出慢思考是極有可能的。

03 比起民族國家,“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更好的政治智慧
界面文化:特朗普勝選后與馬斯克的一系列聯合、硅谷精英集體轉向右翼,都似乎說明技術威權主義十分盛行。你如何看待當下的情況?
吳冠軍:我的理解是,事情都是在變化中的。很多人沒想到,馬斯克竟然會和特朗普合作,他們兩人在很多地方分歧很大,馬斯克做新能源車和SpaceX,核心訴求是改變能源結構和探索火星,為人類文明留后路。但是,特朗普代表的是氣候變化的“拒認者”,他決定讓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認為人類可以繼續過往的方式發展,不需要做什么改變。特朗普宣布退出協定的第二天,馬斯克就退出了總統顧問委員會,他認為特朗普是一個大忽悠。然而今天,他們又達成了合作,這是很有意思的。

我的分析是,馬斯克對人類文明懷有一種危機意識。比如9月30日,他為特朗普單獨搞了一場競選演講的背書,表示西方文明可能面臨終結。他認為,民主黨是更加不作為的,過于關注政治正確如性別議題,忽視了其他人類的大問題,民主黨上臺可能又是白白浪費四年。馬斯克尤其痛恨“覺醒文化”。我們暫且不評論馬斯克的認知本身,在他的認知中,首先就沒有那么多時間可以浪費。
再反過來看特朗普是一個怎樣的人。特朗普非常在乎“贏”這件事,他甚至說過一句話:“我認為競選總統比做總統更有意思。”并且,特朗普是商人出身而不是政治家出身,他的施政就可能不會被此前的說法和做法所綁架,說出的話也經常隨便改口。他可能會愿意談判,只要他認為他能贏。但如果按照政治正確的標準,很多話是不能說的,稍微說錯就會被貼上標簽。
所以,這就產生了一種可能性:當特朗普和哈里斯勢均力敵時,馬斯克在關鍵時刻給予助力,讓特朗普獲得了很大的優勢,那么接下來,馬斯克就可能擁有很大的政治介入空間、能夠深入影響政治議程,比如帶來技術和生態方面的改變。我們也已經看到,特朗普在很多場合都帶著馬斯克,比如和澤連斯基通話、參加巴黎圣母院的重開儀式。
這是件好事嗎?我覺得還是蠻好的,今天的時間常常浪費在政客們彼此指責、彼此起外號的話語中,但我們需要能夠實際地帶來變化的人。至于怎樣變化還無法預測,但至少會有新的可能性。
你可以不喜歡馬斯克,但他的確是一個思考者,一旦想好以后執行力也很強。比如在此之前,沒有人認為去火星這件事可以由私營公司來完成,但是他承擔了下來,并且做得有聲有色。
界面文化:雖然馬斯克是一個思考者和行動者,推出了Neuralink腦機接口等非常“科幻”的技術,但如你在書中所說,他的愿景歸根結底是超人類主義的,會導致權貴精英最先享受到增強技術,進一步加劇全球不平等,馬斯克對AI的恐懼也仍然根植于“人類-AI”的二元對立。與之相反,后人類主義則是激進地打破了二元對立。可以簡單談談兩種框架的區別嗎?
另一個問題是,如今,真正掌握技術的人才許多都被招至OpenAI等科技公司,他們也會不可避免地進入技術-商業精英的框架;而還在想象“后人類”未來的,似乎是并不擁有技術的“文科生”。即使我們知道后者才是努力的方向,但是在提出理論之余,還應該怎么做?
吳冠軍:這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首先要講一下超人類主義和后人類主義的區別。人類主義是一種基于生物性身份的思維邏輯,超人類主義是人類主義的延伸,當馬斯克看到人工智能的挑戰,他會想:不能讓人工智能比我更強大,所以要通過腦機接口等方式,使它成為我思維的一部分,從而駕馭它。人類主體是一個基座,其他所有東西都往上加,目的是提升我的能力。經常會出現兩種心態,一種是對人工智能充滿恐懼、不讓它發展;另一種是寄希望于人工智能來解決人類的問題,這也是一種人類主義,叫做有效加速主義。
在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多走一步路,提出另一種思維方式。人類對自己的能力具有信心的歷史并不悠久,只有四五百年,再往前其實并不是這樣。西方文化中有全知全能的上帝,泛神論中山有山神、樹有樹神,許多事物都比我們厲害,《西游記》里的唐僧看到一棵杏樹里的樹精都要嚇死了,所以人類沒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幾百年來,人類形成了一定要坐在中心的思維方式,當智能有可能被超越時,就不能平心靜氣地對待了。
因此,“后人類”的概念很好,它不是反人類主義,而是要在人類之后,看看不一樣的可能性,有沒有被人類主義所掩蓋和忽視的存在值得探索和合作。它也不是取代關系,不再是中心-邊緣的框架,而是擁抱多樣性,打開主體間性、文明間性、物種間性和智能間性。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種智能,其實你也很孤獨,這意味著你很難再提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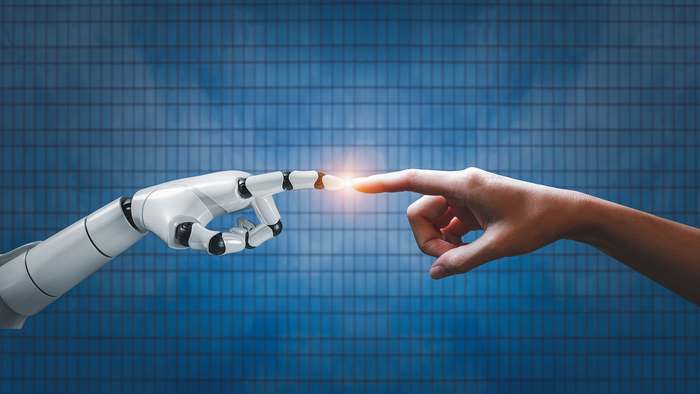
舉個例子,人類的成就與其他生物的合作密切相關,同身體中腸道菌群的合作形成了我們的健康狀態。從國際角度來說,切斷國家之間的合作并進入“掐脖子”狀態,是一種很愚蠢的行為。很多人留戀人類主義也很正常,就像是留戀故鄉,但我們應該有更大的思考格局,學會謙卑,去看到一開始讓你不舒服的存在者。并且,當人類文明變得越來越陳腐、老化,公共平臺上充斥著各種對撕和謾罵,還能出現這么有意思的可能性,這不是很好嗎。
界面文化:奇怪的是,人工智能技術本身是去中心化、跨學科的,可現實卻是,它成為了一種中心化和威權化的技術。按照書中的觀點,如果全球資本主義秩序、民族國家格局沒有改變,人工智能趨于中心集權化的未來是否就無法改變?
吳冠軍:這是人類的自我組織的兩種主流方式,兩種方式彼此依存,延續的時間很長,同時也構成了我們當前的僵局。
我們先從民族國家的角度來談起,自威斯特伐利亞合約以來,歐洲國家進入了民族國家狀態,這種狀態后來主導了世界。盡管聯合國呼吁了許多事情,但它的力量也很弱,我們仍處于不斷擦槍走火的局面中。
曾經,民族(nation)讓世界有了新的可能性。通過這個概念,我們能夠建立連接,形成想象的共同體,連結許多氏族和種姓,打破了以往不可合作的壁壘。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反而成了紛爭的源頭。政治智慧是沒有最終結論的,今天可以被視為一個迭代政治智慧的階段,比起民族國家,“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更好的政治智慧。它超越了傳統的民族框架,在人類乃至行星的意義上思考共同的命運,它更可以開啟各個物種命運共同體的后人類視角。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生存依賴于外部,資本主義不能自給自足地增長,它一定要開辟新的市場、發現新的方式。今天全球化的程度越來越高,既有的市場越來越飽和,各種資源也已經被深度開發,那要如何找到新的地方呢?于是,技術變得極為重要,一有新技術出現資本就撲了過去。

過去的世界是廣闊的,但今天的行星變得越來越小、已經變成“地球村”了,導致了許多矛盾。盡管中國和美國地理上相隔遙遠,但地球變小使得他們很近,有人就會感覺對方多吃了一口肉,我就會少吃到一口。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共同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矩陣,嚴重制約了人類文明的進步,也讓我們陷入危險的邊緣,比如生態危機。
在資本主義中,什么都要算一算利潤,生態問題的成本就很高,例如,實現碳中和的成本就很昂貴。而民族國家的模式讓局面變得更糟糕,特朗普認為,美國憑什么要承擔責任?但問題是,生態問題主要是經歷過工業革命的發達國家造成的,而不是南方國家。在這個意義上,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結構使很多事情無法做成。
技術也是一樣,AI原本是一個非常好的討論平臺,但現在AI本身變成了一場軍備競賽。所以,我們要呼吁一次政治哲學的大的迭代。上一次的政治智慧迭代是三四百年前,在以往等級化的社會中,很多人的幸福指數很低,活著就是吃飽這一件事,但那時的啟蒙哲學家們發明了一組新概念,讓我們進入了現代性,人類也取得了許多成就。現在我們又到了一個關頭。
04 就算人類輸給人工智能,也不意味著一切都結束了
界面文化:你在寫這本書時,諾貝爾物理獎和化學獎授予與人工智能領域相關的學者的消息還未公布。但你也在書中寫到,技術已經不再是科學、政治、藝術等維度之一,而是凌駕于這些維度,成為主導性維度。在你看來,諾獎委員會的選擇是技術凌駕于科學的表征之一嗎?你如何評價這一選擇?
吳冠軍:諾獎物理學獎公布后,我的朋友圈幾乎炸了。我的一個朋友是有名的哲學教授,本科學的是物理學,他非常生氣,說:“諾貝爾獎委員會瘋了,杰弗里·信頓和約翰·霍普菲爾德都是搞人工智能的,計算機科學有圖靈獎,怎么又跑來搶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又沒有受過物理學的學術訓練。”
我的分析是,這次的諾獎既激進又保守。激進在于,他們竟然大踏步沖破學科的壁壘,關注研究者跨學科的貢獻,而不是物理學歸物理學,計算機科學歸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本身就是跨越學科的,ChatGPT或者Sora可以是物理學家,也可以是人類學家。
保守在于,諾獎委員會在評選時仍然要證明這是人類獲的獎,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仍然存在。這導致了某種扭曲——約翰·喬普是AlphaFold的首席科學家,他并不是做結構分子生物學的,然而他領銜做出來的計算機模型是一位很棒的結構分子生物學家。但諾獎委員會無法認可一位連“臉”都沒有的科學家的成就。同樣,辛頓在人工神經網絡方面的一組奠基性工作使得物理大模型有了可能性,但并不意味著他是這個領域的專家,所以信頓接到獲獎電話時還以為這是一個玩笑。

界面文化:我讀過一篇諾貝爾物理學獎評獎委員會委員Ulf Danielsson的專訪,他也認為AI只是工具,不能自己推動科學前進。
吳冠軍:我這本書也是一個努力,希望慢慢打開我們的格局。我們只是倚賴生物性的快思考的時候,格局比現在更小,看到不同膚色的人會感到警惕或恐懼。所以人工智能要用起來、不同國別民族的朋友交起來,互相學習才是解決生物性恐懼的方式。就算人類最終輸給了人工智能,那也沒關系,不意味著一切結束了,我們人類還可以regroup(重新部署),就像愛因斯坦去到普林斯頓大學后進行了重新調整,相對早年物理科研上進展有限,但他成為了一個偉大的公共知識分子。
今天的情況是相反的,學者在論文署名時,還是不允許給AI共同署名;由于不能署名,學者使用了ChatGPT進行文獻梳理,結果就被抓出來說成抄襲。這都是很猥瑣的事情,有好的工具為什么不允許使用呢?
05 當下是人類文明史上政治智慧和技術智能最脫軌的時代
界面文化:你在書中著重寫了AI時代的教育問題,認為在AI取代人類工作、知識更新迭代加快的當下,教育應該從實體學校的單線灌輸式教學,轉變為網絡狀結構的終身教育,所有人都是教-學實踐的行動者,需要時時與網絡互動,這樣才不會被淘汰。關于AI對教育的啟發,可以再展開談談嗎?
吳冠軍:今年1月份的Nature雜志有一篇很棒的文章,題目叫做《It Taks Two to Think》(要二才能思)。人類的思考過程從來不是孤立的,看似是“吳冠軍”寫的書,但這建立在我閱讀了許多優秀著作、向很多深具洞見的作者進行思想交流的基礎上,只是在人類的寫作傳統中,“作者”不能寫上幾百個,所以我的書“后記”變得很重要,里面有在我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交流者。
法國哲學家拉圖爾有一個“行動者網絡理論”,個體并不是以自我為本體論根基的行動者,而是在互動中才產生了行動者。并不是首先有兩個個體在彼此互動,而是通過互動才有了這樣的你和我。所以,改變和互動是最根本的,關鍵不是你是誰、有怎樣的理念,關鍵是你做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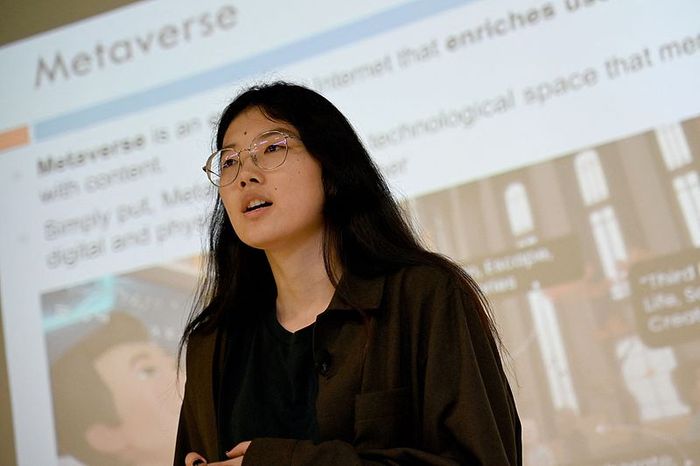
界面文化:一個疑惑在于,在學歷貶值、畢業即失業的嚴峻情況下,以上討論對大部分人的意義是什么?清華大學基礎科學講席教授劉嘉也提到,在AI時代,教育應該從就業導向變為跨學科的通識教育。可是能做到這一點的,似乎仍然是精英群體,你怎么看?
吳冠軍:可以從兩個角度回答。第一個角度指向自我、我該怎么做;另一個角度是整個社會應該怎么部署,使我們能夠更好的合作,而不是互相傷害或產生大量失業。
從自我出發就是倫理學,從社會結構出發就是政治學。然而在今天,這兩個學問都幾乎停滯不前。政治學被邊緣化,我們也不怎么講倫理了,反而要求人工智能講究倫理。
從自我出發,今天面對世界的唯一可能性就是重新構建認知地圖。以前,我們是在同學、父母的軌道上學習,但是了解人工智能的學習模式后,我們可以反思人類的學習制度。傳統上,人類的學習周期是20多年,工作后就停止學習了。然而,學習本身是一種重要的倫理實踐,人工智能也要通過學習生成新內容,因此,學習應該是終身性的投入,并且要與各種人、后人類對話。
雖然你提到精英與非精英的區分,但反過來也可以說,你愿不愿意提升自己呢?學習的確很累人,因為慢思考會消耗能量,也不符合人的本能,人的眼睛不擅長梳理抽象文字,更擅長處理圖像,所以刷短視頻很開心,但同時你也喪失了很多。而倫理學要求我們走出舒適圈,不僅僅滿足于當一個“吃貨”。
從政治學出發,我們面臨的一大挑戰是,大量的人不再被需要。以前只是在體力上不被需要,比如工業化生產代替了木匠的手工藝,但如今,AI在智能方面的表現也經常超過人類。在文明史上,已有的各種社會形態都高度依賴人力(體力與智力),連戰爭也需要人力,但是現在無人機技術已經很成熟。未來,當AGI(通用人工智能)的時代真正來臨,它在各個領域超過85%甚至90%的人類,那么除了最一流的人類仍有價值和話語權,剩下的絕大多數怎么辦?
可惜的是,我們仍然在用老方法應對新問題。特朗普還認為是移民搶了他們的工作,畢竟沒有臉的人工智能沒法被直接看到,技術還在以指數級發展,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政治智慧和技術智能最脫軌的時代。
赫拉利說,總會出現新的工作,可是新工作的學習成本誰來支付?人們本來就不愿意學習,學習成本還變得越來越高。最后還是要同時落到技術與政治,要去加快迭代政治智慧,通過哲學來創造概念,并把新概念安頓進我們的世界中,否則真的要告別智人了。如果我們能做好,那么在后人類的地平線上,我們將再次見到智人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