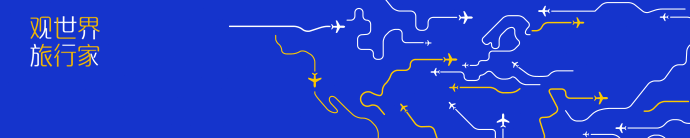撰稿人 | 沈宏非

設想,攤開一張巨大的地圖,席地而坐,屁股盤踞上海(盡量別去想東方明珠三件套等頂尖建筑),面朝正西偏南,兩手撐地,右肘微曲,燈下細看時,發現一左一右,正好撳牢兩個人間天堂。又好像,一手一杯咖啡,一手一盞茶。
更“天堂”的是,左天堂和右天堂,從上海出發,開車都在一個時辰里——如果將目的地鎖定蘇州,恰好也就是從頭到底完完整整透透徹徹喝完一泡茶、一泡好茶的時間。
與天堂左比,天堂右更近,近到置身上海任何一處紅塵鬧市,心血來潮,一打方向盤,即可乘興而去,盡興而歸。不隔夜。
去蘇州,去喝廟茶,廟咖啡。
論茶,蘇州名氣大遜杭州;以寺廟香火之鼎盛以及叢林之壯闊論,蘇更不如杭,不過呢,茶和咖啡,只去廟里喝,不就是圖個清凈么?

如果是秋日,喝“廟茶”首選寒山寺,蘇州頭部寺廟里的頂流。
第一次來,是七十年代初,只見斷壁殘垣,屬于那種“跑不了廟”的那種廟。第二次,大概是2008年,當時辦美食雜志,做一期蘇州專輯,大名單包括當時有名的寒山寺素食。托上面打好招呼后,到得山門前自報家門,知客僧說住持外出未歸請稍候。等候期間,偷聽到兩個小和尚的廣陵腔對話:
“這幾個人來這塊做神尼?”
“不曉得哎,大概是推銷素食的吧”。
反正,我當話頭參了。

25年后重訪,寒山寺不僅早就“城外”而“城內”了,而且簡直市中心CBD了。與其說叢林,不如是園林。曾有人在上海開了個鹽商菜餐廳,名叫“寒山肆”。雖是諧音梗,不過蘇州寒山寺確實是有些“肆”意的。又不過,所謂靜和鬧,虛與實,一體兩面,都是對比出來了。而從寒山寺的鬧猛一腳踏入“寒山十八慢”的靜虛,也只是一步之遙。
“寒山十八慢”設寺內“楓江樓”。起高樓的年代不可考,只曉得樓塌了是在三百年,現樓為1954年修整寒山寺時重建,當時系將蘇州城內修仙巷著名宋宅“花籃樓”移建于此。兩層殿閣,面闊三間,大殿前檐處有雕刻精細的木質花籃一對,故名“花籃樓”。




“花籃樓”上的“寒山十八慢”,名稱來自寒山鐘聲,所謂“緊十八,慢十八,不緊不慢又十八”,門前“四大皆空”,于一汪水池中照映寺院四時光影。
戶外辟“陋室”茶室及讀書抄經之“坐忘茶寮”,有龍王殿、常樂池,庭院圍合,曲徑通幽。
一樓有茶飲、咖啡、甜品,二樓經精心設計,享有“蘇州的琉璃光院”之美譽。



 拾級上得樓來,一時竟覺得“寒山十八慢”在氛圍上似比寒山寺本寺更為wabi sabi:面對一臺靜水,低頭,漣漪蕩漾;抬頭,楓橋在望。全場靜音,唯有水滴聲,緊十八,慢十八,不緊不慢又十八。雖是涓滴,但入耳走心之力,全不亞于寒山寺的金屬鐘聲。
拾級上得樓來,一時竟覺得“寒山十八慢”在氛圍上似比寒山寺本寺更為wabi sabi:面對一臺靜水,低頭,漣漪蕩漾;抬頭,楓橋在望。全場靜音,唯有水滴聲,緊十八,慢十八,不緊不慢又十八。雖是涓滴,但入耳走心之力,全不亞于寒山寺的金屬鐘聲。
其實,與其在茗香里冥想著讓自己“慢”下來,還不如先想想自己究竟是怎么個“快”起來的。




與“慢茶”相比,“快”的是一樓的咖啡,屬于“緊十八”。“寺廟咖啡”正在“活化”著蘇州的寺院,香火繚繞里也融入了一縷咖啡香。其實,寺廟、尤其臨濟宗,本應就是活的,燙的,殺口的。不玩拈花微笑,以“棒打頓喝”為門風。所謂“舌上起風雷,眉間藏血刃”,生龍活虎。寒、拾好基友,更是嬉皮任誕,照樣修成正果。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這個既是躺平,也算修行。茶沒問題,禪茶一味么。但見有寺僧也在與香客開心地對坐咖啡,第一眼似違和,轉念一想,這更沒毛病啊,不能把咖啡不當豆制品對嗎?再講了,咖啡這種東西,有“因”(咖啡因)有“果”(咖啡豆),自帶禪意,倷講啊對?
在胡蘭成的回憶錄里,有一次清晨和張愛玲逛美麗園,大西路,徜徉在“滬西歹土*”上,聽到她滿心歡喜地說:“現代的東西縱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們的,與我們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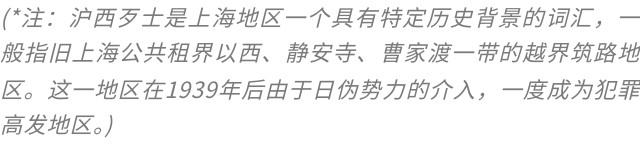 如果可以在半夜穿越到晚唐,和鐘聲一起送到楓橋夜泊船上的,應該還有咖啡香吧。
如果可以在半夜穿越到晚唐,和鐘聲一起送到楓橋夜泊船上的,應該還有咖啡香吧。


檐下“寺貓”,夕陽里精神抖擻,居高臨下,飛檐走壁,雄視有情眾生。此地幸非曹洞門庭,更無東西兩堂相爭,不由為它高興起來。
“鎮守”寒山寺的寒山、拾得兩羅漢,曾有一段經典對話遺世。
寒山問:“世間有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惡我、騙我。如何處治乎”。
拾得曰:“只是忍他、讓他、由他、避他、敬他、不要理他,過十年后,你且看他。”
你且看他,你且喝茶,你且喝咖啡,你且喝著茶喝著茶,看他。

拜過和合二仙,踱出山門,如果寺外仍是早春,如果余興尚存,可西去100里,抵太湖西山島(據說有官人嫌次命,晦氣,于是當地人就很貼心地改叫了“金庭”,不讓近鄰“東山”專美于前)。登縹緲峰,采碧螺春,這大概是蘇州人在杭州人以及全國人民面前最拿得出手的春茶了。
去年清明前,人到了縹緲峰小,卻因腿疾,茶山登不得,只能在山下“水月禪寺”的籬笆墻外,望茶山而興嘆。泡一壺“頭采碧螺春”吃吃,豎起耳朵聽聽空山人語,望望野眼,看貓兒狗兒沒打起來,做了半個時辰的水月寺旁自了漢。
“水月禪寺”,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相傳為觀音菩薩三十六相“水月觀音”造像發源地。自隋、唐至宋、元,毀了建,建了毀,至“史無前例”被毀得最為“史無前例”,淪為豬圈了。目前所見,乃2006年重新之5.0版本,算是中古。









千年來得以續命者,泰半是因為茶。縹緲峰水月塢,碧螺春法定原產地,唐至德二年春,陸羽曾到此地,并有著述:“所謂茶,以成湯者為貴,比之碧螺,最勝。”明人陳繼儒《太平清話》:“洞庭山小青塢出茶,唐宋入貢。下有水月寺,即貢茶院也。”
“小青茶”(洞庭碧螺春茶前身)唐宋兩代被列為貢茶。北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記載,“近年山僧尤善制茗,謂之水月茶,以院為名也,頗為吳人所貴。”碧螺春獨特的螺旋狀外形,據說系水月寺僧人參照了佛像“螺發”,也是犍陀羅風格。
在炒制,殺青、揉捻這些綠茶通用工序之外,搓團顯毫,七萬八千芽頭,造就無數細白絨毛。所謂“銅絲條,螺旋形,渾身毛”,正是碧螺春獨有的識別。
據誰曾有洋盤客人,驚見自己泡出了一杯“綠茶里的Dirty”,便將余茶反復洗刷刷洗刷刷,如倪云林洗蕉洗妓。笑煞了會喝“嚇煞人香”的蘇州人。

從西山返回蘇州,途中陽澄湖畔的“重元寺”不可錯過,尤其是夏季。水月、重元、寒山三剎,皆始建梁武帝時代。規模論,重元寺最巨。如果喝茶喝餓了,可于寺內齋堂齋飯,飯后消食,可在寺旁咖啡茶,觀音閣前,陽澄湖邊有“重緣咖啡”,有茶有咖啡,還有潑天的荷花。
初過重元,時在秋杪,滿目唯見殘荷,后一回,又偏逢“尖角未露”時,悻悻然終于等到今年盛夏,身臨一池連天碧,心曠神怡之余,竟然還,看餓了。




 葉上蓮子、水下蓮藕什么的,自不待言,就連蓮瓣亦可食。古書多有記載,晚近者如《御香縹緲錄》,將蓮花瓣浸過蛋液、面粉后油炸而成。乾嘉年間常見于寺院素食,亦是慈禧愛吃的一種小食。
葉上蓮子、水下蓮藕什么的,自不待言,就連蓮瓣亦可食。古書多有記載,晚近者如《御香縹緲錄》,將蓮花瓣浸過蛋液、面粉后油炸而成。乾嘉年間常見于寺院素食,亦是慈禧愛吃的一種小食。
不過德齡的英文記載似不足為信,三伏天更不宜油炸物,倒是可以扯個閑篇兒:一,曾于某年五月于濟南“燕喜堂”,初食鄧師傅取材自大明湖的一道“炸荷尖”,才知道原來“小荷才露尖尖角”指的不是荷花,而是荷葉(其實長期都因為荷花并沒有長角而感到疑惑)。農歷四月初,荷花未開,最先露出水面的是卷成一團未及舒展的荷葉(即所謂“尖尖角”),摘下洗凈,裹面粉入油鍋炸之,清香,酥脆,最難將息。
百花之中,又以荷花最有佛緣。這個善緣,由佛教和宋儒相繼塑造,后者有《愛蓮說》一百一十九字,將此山龍眼目蓮科水生植物一把拔升至道德人品高度;古印度佛教,則不明覺厲地認為蓮是百花中唯一能花、果(藕)、種子(蓮子)并存者,象征著“法身、報身、應身”的“三身同駐”這一佛性的至高果位。
蓮界至善,皆是人間遺憾。吾等凡夫俗子,有情吃貨,道德高峰無力高攀,更不明“法身、報身、應身”身為何身,有的只是身不由己之肉身,但吃便是了。以身“愛蓮”。這就是愛,這,也是愛。
佛緣之外,荷更有茶緣。今年荷花神誕,在蘇州葉員外的指導下,于“平江頌”復刻古人“菡萏茶”,在另一維度上“吃”到了花朵。
“菡萏茶”(即蓮花茶),典出《考盤余事》,其法,蓮花綻放時,置茶葉于花蕊,蓮花收起后,茶葉被裹在蓮房內,熏蒸一夜之后,次日重放時再取出飲用。《浮生六記》所記蕓娘事茶雅趣,同是此法:“夏月荷花初開時,晚含而曉放,蕓用小紗囊撮茶葉少許,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韻尤絕。”
葉員外認為,熟茶不可用,鮮葉更能吸收花香。因自洞庭西山“水月塢”金海華茶園,新掐芽頭,萎凋兩個時辰,轉至陽澄湖畔“重元寺”荷塘,如法炮制,再五十里送至姑蘇老城“平江頌”茶席,果然“香韻尤絕”。制茶業若也有“生物動力法”,這個就如假包換了,古人、尤其是蘇州的古人,實在誠不我欺。







一葉一豆,皆是鮮活生猛話頭;一飲一啄,豈非任意方便法門?得魚亡荃,見月忘指。不覺坐下地圖不知何時消失,身竟趺坐于“茶蒲團”之上,索性大字躺平,口占寒山體一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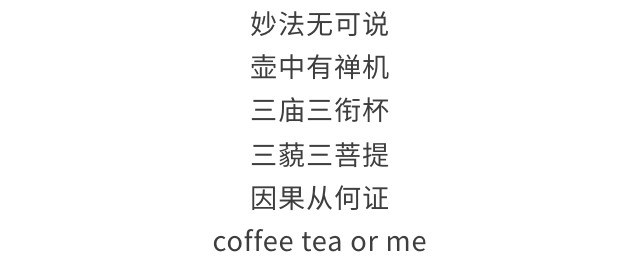




繪畫: 慕容引刀
圖片提供: 沈宏非、李喆、葉文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