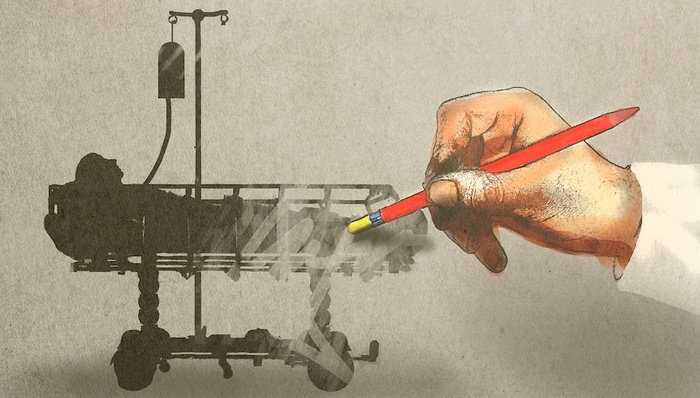【編者按】近日一位名叫“沙白”上海女性在視頻中分享了其罹患紅斑狼瘡病多次發作,最終選擇赴瑞士實施“安樂死”的歷程,引發了一場關于“死亡權利”和安樂死的辯論。《不愿活下去的人》作者凱蒂·恩格爾哈特歷時四年,跟蹤訪談數百位或因疾病、或因衰老、或因難以忍受的精神痛苦而尋求好死(善終)的人,對這一關乎倫理與權利的主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無畏的審視。下文摘自該書,從俄勒岡州的《尊嚴死法》談起,呈現了圍繞安樂死的法律爭議和倫理困境。界面新聞獲出版社授權刊發。
文丨凱蒂·恩格爾哈特
1994年,俄勒岡州選民通過了16號議案,讓該州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通過投票將協助自殺合法化的地方,但現在,為了跟“自殺”撇清關系,在政治游說者和患者的詞典中,這種方式已經改稱“臨終醫療援助”(MAID)或“醫生協助死亡”(PAD)。這項議案遇到了一連串法律挑戰,羅馬天主教會還斥資近200萬美元,發起了廢除這項議案的運動,但它還是于1997年生效。俄勒岡州《尊嚴死法》成為美國和世界的一個歷史和倫理轉折點:是讓這個世界偏向還是偏離烏托邦了,取決于你對這類事情的看法。
一年后的1998年,波特蘭一位84歲患有轉移性乳腺癌的婦女成了美國第一個在醫生幫助下合法死亡的人。這位婦女公布于眾的名字叫海倫,她第一次告訴醫生自己想死的時候,醫生說不想被卷入其中。第二名醫生建議她去住臨終關懷醫院,并在病歷中提及,海倫可能患有抑郁癥。海倫找了第三名醫生;她第一次預約就診時坐著輪椅,身上還連著一個供氧器。她說自己也曾十分享受生活,只是現在已經一天不如一天了。彼得·里根(Peter Reagan)醫生把海倫送到精神科醫生那里,后者花了90分鐘評估海倫的情緒和能力,隨后確定她實際上沒有任何抑郁的跡象。接下來里根醫生給海倫開了三種藥:兩種止吐藥,還有一種屬于巴比妥酸,叫作司可巴比妥。
里根告訴我,在俄勒岡州《尊嚴死法》通過之前,就已經“碰到過特別多的病人請我幫助他們死去。我都拒絕了,因為那不合法。我知道有這個需求,但這個需求讓我覺得很難受,因為自己不能幫助他們而難受”。但里根知道,還是有些醫生在醫院里悄悄幫助了他們的病人。在1996年華盛頓州的一項調查中,12%的醫生說他們碰到過“一兩次或更多次明確請求醫生協助死亡”的情形,4%的醫生說自己收到過“一兩個或更多個安樂死請求”。在提出這些請求的病人中,有1/4的病人得到了致命的處方。在1995年對密歇根州腫瘤醫生的另一項研究中,22%的人承認曾經參與過“協助自殺”或“主動安樂死”。當然,還有杰克·凱沃爾基安(Jack Kevorkian)醫生,他在1990年幫助一名54歲的俄勒岡婦女在他那破舊的面包車后座上自殺,這事兒后來盡人皆知,也讓他臭名昭著。
俄勒岡州的法律要求患者自行服用致命藥物,所以是海倫自己把那杯巴比妥酸液體拿起來送到嘴邊的。她花了大概20秒才把這杯液體全都喝下去。這是一個晚上,她在自己家里,和自己的兩個孩子在一起。喝完那杯巴比妥酸液體之后,她要了白蘭地,但因為不習慣喝酒,在喝的時候還嗆到了。她的女兒貝絲給她揉了揉腳。里根醫生把她的小手握在自己的大手中,問她感覺怎么樣。海倫的回答是她留在這世上的最后一句話:“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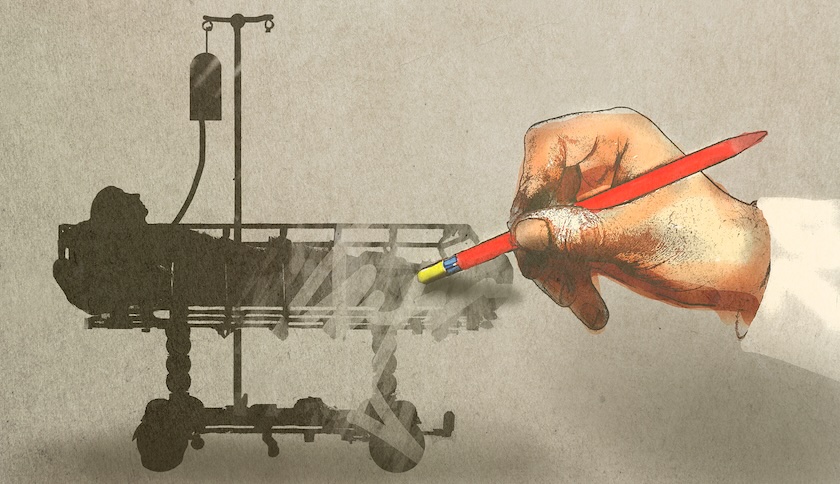
這個開始有點兒不祥的味道。里根醫生告訴我:“事情就這么發生了。”他本來只是波特蘭一名普通的家庭醫生,在他答應幫助海倫的時候,并不知道她的死將是首例。接下來,海倫的故事見了報。《紐約時報》記者蒂莫西·伊根(Timothy Egan)寫道:“當醫生、宗教領袖和政客還在就允許醫生幫助患了絕癥的病人自殺的倫理道德問題爭論不休時,這個問題在今天從抽象討論一下子變成了具體案例。”后來里根的名字也被泄露給了記者,里根開始擔心接下來自己身上會發生什么。人們會往他家的窗戶扔石頭嗎?人們會不會干出更出格的事情,就像他們對墮胎醫生做的那樣?但人們什么都沒做。里根繼續在行醫。
那些反對醫生協助死亡的人從一開始就擔心,任何死亡權都可能會經由一點點積累起來的強制步驟演變成一種死亡的義務——對老人、弱者和殘疾人來說。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的一位教授說的話就很直白:“很多人都在擔心老年人會開著房車在俄勒岡州邊境排隊。”但另一邊的支持者認為,憲法賦予的生命權已經被現代醫學的迫切需要扭曲了。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就算是那些想要自行了斷的人,生命權也已經成了一種可以強制執行的活下去的義務。
按照俄勒岡州《尊嚴死法》的規定,符合條件的病人必須身患絕癥,預后剩余壽命不超過6個月。預后是一門模糊的科學,出了名的不準確,所以必須有2名獨立的醫生意見一致。病人必須年滿18歲,是該州居民,精神上有提出這種要求的能力。醫生如果懷疑病人判斷力有問題,比方說認為病人精神錯亂,就應該送他去做心理健康評估。病人還必須2次口頭提出死亡請求,間隔至少15天,并向主治醫生提交書面請求,簽字時至少要有2名見證人在場。按照法律規定,病人的醫生有義務說明,除了協助死亡之外,還有其他替代方案,比如疼痛管理和臨終關懷,并要求病人不要在眾目睽睽之下結束自己的生命。醫生還應建議病人通知其家人,但這不是強制要求。這項法律的核心要求是自行服藥,就是病人必須自己把藥吃下去,因為允許的只是協助死亡(病人自行服用致命藥物,通常是以服用散劑溶液的方式),而不是安樂死(醫生給藥,通常是以靜脈注射的方式)。
《尊嚴死法》生效后,支持者希望俄勒岡州能給其他州提供道義上的幫助,讓其他州也都通過類似法律。有些支持者將他們的運動看成另外一些偉大的進步運動—廢除奴隸制、爭取婦女選舉權、廢除種族隔離—合理的延續。這個理論認為,嬰兒潮一代目睹了他們的父母死得有多難看,也看到了在醫院里的死亡過程有多漫長,因此會想要另一種死法。但俄勒岡州《尊嚴死法》生效后的鼓與呼并沒能完全展開。1995年,梵蒂岡稱協助死亡“違反了神圣律法”。美國醫學會也反對這項法律,因為“醫生協助死亡跟醫生作為療愈者的角色背道而馳”,也違背了醫生不造成傷害的莊嚴承諾。這種思路認為,療愈,就意味著不可殺人。接下來,有數十個州就俄勒岡州性質的法令展開了激烈辯論,最后還是都被否決了。波特蘭的好多醫生都認為,協助死亡會成為“俄勒岡諸多怪事之一”。
1997年,美國最高法院裁決了2起分別來自華盛頓州和紐約州的協助死亡案件。在這2起案件中,大法官們一致決定不推翻州一級禁止醫生協助死亡的法令。大法官們指出,醫生協助死亡并不是美國憲法中規定的一項受到保護的權利。也就是說,并沒有什么死亡權,也沒有尊嚴死的權利,或者用桑德拉·戴·奧康納(Sandra Day O’Connor)大法官的話來說,甚至也沒有“普遍的‘自殺權’”。最高法院把這個問題退回了“各州的實驗室”。首席大法官威廉·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在由他執筆的多數意見書中,強調了各州在“保護弱勢群體—包括窮人和老弱病殘—免受虐待、忽視和錯誤傷害”方面的權益。他也提到了已經成為世界各地反對死亡權思想支柱的滑坡論,即一旦承認有限的死亡權,就不可能對其加以控制,這項法律會勢不可當地一再擴大,將越來越多的病人都包括進去:生了病但還沒病入膏肓的人,精神上有病但身體上沒病的人,老、弱、殘。批評者警告說,最后一定會出現濫用,濫用在窮人、不情愿死去的人、妥協了的人、感到害怕的人身上,就連害了單相思的16歲男孩都可能會卷入其中。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就曾指出,任何給定的原則都有“擴大到自身能夠推而廣之的極限……的趨勢”。
然而,在其他地方,立法者對神圣性有不同的看法。1995年,澳大利亞北領地擬將安樂死合法化。盡管該法律在2年后被聯邦政府廢除,但全球格局正在慢慢發生變化。1998年,來自世界各地的“自殺游客”開始在瑞士死亡。在那里,協助死亡已經合法化,蘇黎世附近的一家新診所開始接收外國病人。2002年,荷蘭和比利時都將安樂死合法化了;后來,盧森堡也加入了這一行列。小小的比荷盧地區成為醫生協助死亡的全球中心。
大約在同一時間,英國的一項法律挑戰未能推翻該國對協助死亡的禁令。這個案子是由來自盧頓的43歲患有運動神經元疾病的戴安娜·普雷蒂(Diane Pretty)引起的。黛安娜說她想結束自己的生命,但她做不到,因為她脖子以下都癱瘓了。她說,這樣一來,她無法自殺,而這是她的合法權利,法律剝奪了她尊嚴死的權利。
黛安娜想讓她的丈夫殺了她—她想確保當他這么做時,他不會因為謀殺而入獄。她先向英國法院提出訴訟,然后又向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歐洲人權法院提出訴訟。2002年4月,在最后一次上訴失敗的那天,戴安娜在倫敦通過語音模擬器對一群記者說,“法律剝奪了我所有的權利”。一個月后,她在數天的極度痛苦中死去。《每日電訊報》報道,她“以她一直害怕的方式”死去。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尼爾·戈薩奇(Neil Gorsuch)在其著作《協助自殺和安樂死的未來》中指出,允許協助死亡的法律只要存在,就會給倫理道德帶來極大腐蝕,讓我們一頭沖向毫無價值的死亡和強制的殺戮。戈薩奇寫道,沒有比美國死亡權運動駭人聽聞的早期歷史更好的證據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為“自愿安樂死”四處奔走的人,有些也同樣支持優生學,支持強制“愚笨的人”絕育,支持社會達爾文主義,還秉持“種族改良”的思想。戈薩奇警告稱,未來的道德敗壞,只能通過維持“反對由私人有意剝奪他人生命的毫無例外的社會規范”來防止。生命必須保持神圣。
一直到2008年,才有第二個州跟上俄勒岡州的步伐,就是華盛頓州。隨后是蒙大拿州(通過司法裁決,而不是立法)、佛蒙特州、科羅拉多州、加利福尼亞州、華盛頓特區、夏威夷州、緬因州和新澤西州。這些法律各有各的名稱,各自采用了不同的委婉說法:《生命終點選擇權法》(加州)、《“我的護理我做主”法》(夏威夷州)、《病人在生命終點的選擇和控制法》(佛蒙特州)。今天,超過1/5的美國人生活在對絕癥病人來說醫生協助死亡合法的州,他們對此也樂見其成。2017年蓋洛普的一項調查顯示,73%的美國成年人認為,醫生應當被允許“以某種無痛的方式”結束病人的生命,只要這是病人自己想要的,而且該病人“患有無法治愈的疾病”。不過,在問題變成“如果病人要求自殺”,是否應允許醫生幫助病人時,這一支持率下降到67%。語言反映了思想,語言也影響了思想,“自殺”這個字眼仍然很有分量。
在俄勒岡州,這一數字仍然很小:大約每1000人中有3人以這種方式死亡。2019年,290名病人得到了致命的處方,188人通過攝入致命藥物死亡。根據該州披露的數據,我們可以了解到關于這些人的一些事實。絕大多數人都患有癌癥,而其他人則患有心臟病、肺部疾病和神經系統疾病,比如肌萎縮側索硬化(ALS)。患者通常都是65歲及以上的白人中產階級,已婚或是喪偶,受過一定程度的大學教育。他們在精神健康測量方面的得分都很低。他們基本上都有醫療保險,也基本上都已經住進了臨終關懷病房。最近,精神科醫生、學者琳達·甘齊尼(Linda Ganzini)在一次演講中對一群公共衛生專家開了個玩笑:“我一點兒也不知道,在醫學當中,我們一直很擔心的一種情況或者說情形原來是,風險因素一直是富有、白人和有醫保。”甘齊尼指出,需要臨終援助的病人已經習慣了他們的生活方式,所以“專注于控制”死亡。為此,他們在需要挑戰穿著白大褂的醫生時,在需要同根深蒂固的重重障礙折沖樽俎時從不退縮,他們有時間,有秉性,也有資本,可以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并努力得到自己想要的。其他學者還提出了另外一些理論。他們指出,非裔美國人通常都不太可能在生命終點得到照護,比如姑息治療和臨終關懷,并推測這些差別也同樣延展到了協助死亡方面。致命藥物價格昂貴,一般醫療保險也不會包括這一項,所以有時候他們根本買不起。學者堅持認為,有些群體對老人的照護比其他群體更加周到,因此那些群體中想要自殺的老人估計會比別的群體少。他們把這些都歸結為宗教信仰、集體歸屬感和道德價值觀的差異。
在那些協助死亡合法的州,我們確實知道是什么促使病人選擇早死。在查看俄勒岡州衛生部門發布的數據時,最讓我驚訝的是,大部分要求死亡的人據說并沒有處于可怕的疼痛之中,甚至也不是因為害怕未來會遭受怎樣的痛苦。絕大部分人都聲稱,他們最關心的臨終問題是“失去自主權”。也有一些人擔心“失去尊嚴”,失去享受生活中的快樂的能力,以及“失去對身體機能的控制”。在將疼痛納入考量時,他們說的都是害怕未來的疼痛,或是想要避免即將到來的疼痛,再不就是因為此時此地并不知道未來還會有多少痛苦到來而在精神上感到的苦痛。是能好好死去還是會不得好死?這個問題中的不確定性讓它變得迫在眉睫。俄勒岡州的病人必須身患絕癥才有資格申請協助死亡,但到最后他們選擇死亡卻更多的是跟生存有關的原因,是對現代醫學既定邊界之外的痛苦做出的回應。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