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張帆 潘文捷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近年來,一些由女性運營、服務于女性顧客的商業場所和活動空間在國內不少城市出現。全女酒吧、全女民宿、全女健身房……“全女生意”呼應了女性對于安全、尊重和專屬空間的需求,也面臨著外界對其實際運營效果的質疑。
在近100年前的紐約,也有一家著名的“全女酒店”——巴比松大飯店。這座維持單一性別接待史長達54年的酒店,它帶來的改變有多大?這是歷史學家保利娜·布倫感興趣的問題,也是她寫作《巴比松大飯店》一書的緣起。
巴比松大飯店誕生于20世紀20年代的紐約。彼時,《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通過,婦女獲得了投票權。大批女性涌入紐約的新摩天大樓工作,申請上大學的女性人數創下歷史新高。紐約的建筑也在忙著“除舊布新”,各式各樣的公寓式酒店迅速崛起,一批適合女性的女子公寓式酒店應運而生,地處第63街與列克星敦大道交匯處、于1928年開業的巴比松大飯店是其中最富魅力的一家。

在建造者威廉·H·希爾克的設想中,巴比松大飯店將擁有23層樓和720個房間,配備游泳池、健身房、屋頂花園、教學室和圖書館等一切男性專有的用來鍛煉智識與體魄的設備。酒店的名字——取自19世紀法國藝術運動的巴比松畫派——也提醒著外界,這里將為有藝術氣質又不失高雅的年輕女性提供棲身之所。對于入住的女性來說,巴比松大飯店不僅像是一柄安全“保護傘”(嚴禁男人接近臥室所在樓層),還提供按周收費、每日客房服務以及餐廳——這讓她們免于下廚之苦。
正如希爾克所預想的那樣,巴比松大飯店迎來了這樣一群野心勃勃的年輕女性住客:她們是“吉布斯女孩”——來自頂尖秘書學校的學生、“鮑爾斯模特”——為模特經紀公司效力的美麗女郎,以及《少女》雜志客座編輯項目的優勝者、聰慧的女大學生西爾維婭·普拉斯、瓊·狄迪恩、蓋爾·格林、珍妮特·伯羅薇和芭芭拉·蔡斯……這些姑娘有志于成為未來的作家、記者和藝術家。
然而,“巴比松的6月既是一個機會,也是某種程度的‘清算’,要么托舉你在未來歲月揚帆遠航,要么送你更深地劃向抑郁的深淵。”保利娜·布倫在書中寫道。

[美]保利娜·布倫 著 何雨珈 譯
未讀·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24.3
西爾維婭·普拉斯,從巴比松走向自殺
在《巴比松大飯店》中,保利娜·布倫用不小的篇幅講述了西爾維婭·普拉斯及諸多《少女》雜志客座編輯的故事。她在著手研究這家酒店時面臨諸多困難,“關于這家酒店的資料實在太少,”那些曾經入住的女性“既不屬于教養良好的上流社會,也不屬于要靠工會的藍領階級”,關于她們的資料也少得過分。
當《少女》雜志以及客座編輯項目進入她的研究視野,困境得以緩解,“我找到了書寫巴比松大飯店的那條途徑,正如書中的西爾維婭·普拉斯等客座編輯也曾在這里找到了她們的路。”——盡管這條路最終被證明是一場鏡花水月。
1953年5月末,當史密斯學院三年級學生西爾維婭·普拉斯抵達紐約巴比松大飯店時,她一頭金發,準備充分,即將作為“美國的20名優勝者之一”開啟在《少女》雜志編輯部的人生歷險。對于那個時代的女大學生來說,入選《少女》客座編輯項目并獲準入住巴比松,這意味著她們已在職業女性生活中占得先機。她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大學里的灰姑娘,仙女教母……揮舞著她那又長又尖的魔杖說道:‘我會實現你的愿望。’”
作為1953年的《少女》客座編輯之一,西爾維婭具備這一群體的典型特征:曾經野心勃勃,心懷夢想并為之奮斗,隨后擱置夢想,遵循社會期待結婚生子,到頭來發現自己身陷困境,遭遇離婚、抑郁甚至自殺。
大學還未畢業時,西爾維婭已憑文學才華贏得了滿抽屜的獎。保利娜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訪時指出,“但她那時已罹患抑郁癥和其它可能存在、尚未確診的心理疾病,這些病狀在她1953年在紐約期間愈發顯現,這也是她在自傳體小說《鐘形罩》中講述的故事。”
彼時女性承受著社會文化規范的束縛——她們應該上大學,追求某種類型的職業,然后放棄它去結婚……對于這些規范和要求,即便她們不愿順從,也無法勇敢拒絕,如同西爾維婭在《鐘形罩》中所寫:“其實,我什么都駕馭不了……就像一輛麻木的無軌電車。”

西爾維婭在《金鐘罩》中暗示了自己內心的矛盾:“我知道,不管男人在婚前向女人獻上多少玫瑰、熱吻與正式晚餐,婚禮儀式結束后,他私心里真正盼望的,只是讓女人臣服于腳下……”離開巴比松大飯店后,她還是選擇遵循社會規則,在1956年走入婚姻,并于1960年生下第一個孩子。
1960年,作家珍妮特·伯羅薇曾站在西爾維婭家中狹窄廚房的門口與其聊天,她見證了這樣的一幕:西爾維婭——這位曾獲得劍橋富布賴特獎學金的天才作家——邊用左手臂彎抱著剛出生5周的女兒,邊用右手晃動著鍋子,最后,她似乎實在難以擺平,把嬰兒抱到客廳,直接“硬塞”給了丈夫。
1963年的一天清晨,時年30歲的西爾維婭把頭伸進烤箱,打開煤氣,再次試圖自殺。她那時剛與詩人丈夫分居,住在英國倫敦的公寓里。為了保護在不遠處熟睡的兩個孩子,她用濕毛巾封住了廚房的門。這一次,她成功了。
全女空間沒有解決父權制的核心問題
在《巴比松大飯店》中,保利娜·布倫問道:“為什么我大學畢業來到紐約后,會希望有(巴比松大飯店)這樣一個地方存在呢?為什么支持女性抱負、只允許女性進入的空間還在不斷涌現呢?”
在城市中,女性為何感到恐懼?在《女性主義城市》一書中,作者萊斯莉·克恩指出,每個女性都擁有一張關于恐懼和安全的動態的心理地圖,這張地圖的層次“既來自危險和騷擾的個體經歷,也來自媒體、謠言、城市迷思和充斥在所有文化中的古老而寶貴的‘常識’”。
克恩認為,這張地圖“很少包括女性面臨暴力最多的危險場所——家庭以及其他私人空間”。與此相反,“威脅被外化到城市環境中,進入公園、小巷和室內停車場。”把女性的恐懼引向外部的目的,是為了服務于“異性戀父權制的資本主義體系”。在這一體系中,男性作為受益者有效地維持了現狀,而女性的生活及對空間的使用則被恐懼所限制。恐懼也塑造了女性對工作和其他經濟機會的選擇,使女性依賴男性作為自己的保護者。最終,女性“被束縛于家庭的私人空間里,并對核心家庭制度中的家務勞動負責”,克恩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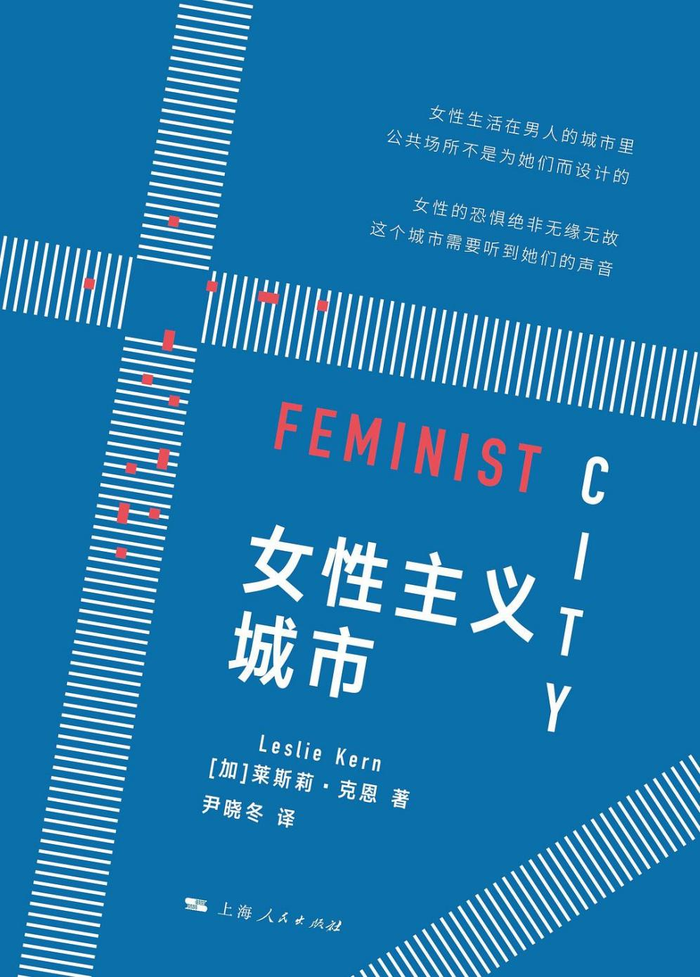
萊斯莉·克恩 著 尹曉冬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7
在《女性主義城市》中,克恩還提到了一些城市中被指定使用的女性專用車廂:“在世界各地,公共交通系統是對女性進行騷擾和侵犯的溫床。”
“女性必須小心嗎?可悲的是,是的。”保利娜·布倫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十幾歲的女兒總是在紐約到處跑,我們住在曼哈頓以外的布朗克斯——這意味著她必須大量使用公共交通。”
僅僅通過專用車廂把女性隔離,能夠讓男性改變他們的暴力態度和行為嗎?正如建立類似巴比松這樣的全女飯店,能夠讓西爾維婭們最終不被囿于廚房和嬰兒床嗎?在布倫看來,答案是否定的:這些舉措都沒有解決核心的父權制的問題。
保利娜·布倫于今年9月出版的新書She-Wolves: The Untold History of Women on Wall Street著力于講述那些何闖入華爾街男性俱樂部的女性的故事。
相比《巴比松大飯店》中的年輕女性,保利娜·布倫任教的瓦薩學院教授的女學生們對于生活有著更多的掌控感。“她們的世界觀要廣闊得多、開放得多;她們不會用單一的標準去評判自己和他人。對于結婚或生孩子,她們沒什么壓力,也沒人在意性取向或性別認同。”保利娜·布倫告訴界面文化,“不過,當我們討論貝蒂·弗里丹關于20世紀50年代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階級女性遵循傳統、放棄事業并在家照顧孩子的經典之作時,她們也擔心自己會屈從于那種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