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丁欣雨 記者 黃月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黃月
按:當生活被“努力奮斗,不要停下!”的打雞血式號召和眼花繚亂的娛樂產品環繞的時候,很多人卻陷入了意義荒蕪。
國慶假期已近半,你是如何度過的?要知道,在“旅游出行”“放松消費”成為代名詞以前,假期的誕生其實別有一番文化語境。無論中外,除了頗具民政意味的假期,最早的假期也往往依靠特殊事件成形,慶典和儀式是當天的重頭戲,人群簇擁起來,渴望與超自然精神聯結,祈求降下福祉,人世間風調雨順。
近代社會的發展刺激著生產與消費、工作與休閑愈發對立,在被工作占據的人生里,假期只剩下“不用工作”的簡要含義了,它圍繞工作而存在,曾經豐富的自足意義漸漸被遺忘。與此同時,在全球勞工近一個世紀的抗議和爭取后,定期休假制度終于建立,人們的休閑方式也相應地發生著改變。“回到家中”是人們減緩疲憊的一種辦法,即使在公共場合,人群也分散成更小的單位,這與初期人們相聚一堂的虔誠景象大有不同。
當“節日”包含的文化意義不再突出,休閑生活被消費和層出不窮的娛樂產品包圍,人們能休息得更好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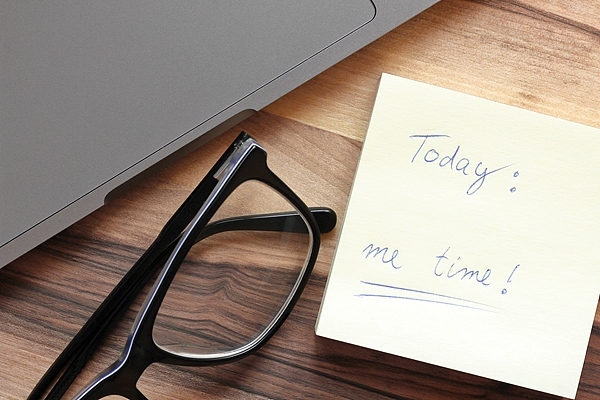
休息日的由來:超自然聯結與重大儀式

早在很久以前,人類就學著如何依循自然風光的流轉來劃分時間。日升日落為一“日”,月行圓缺為一“月”,四季變換為一“年”,唯獨“周”是由人類發明的時間段落。
城市歷史學家維托爾德·雷布琴斯基在《等待周末:雙休日的起源與意義》一書中探討了“周”這一概念的發源,7天制的“周”被推測與“行星周”的說法相關。占星術主張,行星的移動反映了諸神的種種活動,而人間的每樁事件莫不受這些星體和其他星辰位置的影響。一星期的每一天被認為是由一名神衹掌管,因為古人能在夜空中觀測到7個明顯在移動的星體,故一星期劃分為7天。
由平日對“周”的稱呼得知,不只是“星期”,人們也常有“禮拜”的稱呼,而后者則隱含著宗教的意味。有證據顯示,在公元前140年,猶太人復興的時代,采取7天一循環、在每個第7天守安息日的習俗就已經形成了制度化。盡管此后,7天制的“周”受到普遍接納,但一周當中每一天的意義卻因地而異。不同的宗教派別往往采用別具一格的計日法,以此自別于其他信仰,例如伊斯蘭教的圣日是周五,基督復臨派規定周六為圣日。當天是神明指定的休息日,工作被免除,有些教徒也會舉行慶典和禱告,宗教的神圣性因此得到有韻律地重溫。

[美]維托爾德·雷布琴斯基 著 梁永安 譯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22年
不用工作的日子不僅是宗教的恩賜,也有其他因素的考量。“不用工作”的另一面是“禁止工作”,特殊事件諸如瘟疫、自然災難、出生和死亡的結果、重要狩獵出發前,都有可能產生某種禁忌。為數龐大而繁復的禁忌降下懲罰威脅,抑制人們的日常生活。雖然能休息,但在毫無節慶氣氛的禁忌日里,人們只好郁悶地留待家中。
約定俗成的假日慣例從此時開始慢慢建立,它固然使工作與休息的界限有了雛形,但日子本身的自足意義是一切的出發點。超自然關懷為人們生活的重復節奏提供架構與尺度,人們的日常生活也受到超自然力量的感染或牽制。“休息”包含減輕疲勞的生理需求,但不能忽視的是民眾的“敬”與“畏”,心靈上的默觀呈現為群體性的重大儀式。儀式提供一片空間和一段時間,人們停留于其中,暫時擺脫混亂的俗世,得以“神馳”,走向無形的愛的世界。
中國有記載的公休制度最初出現在漢朝。古人稱放假作“休沐”,是因為秦漢時期人們的生活條件有限,沐浴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搓洗干凈便成為休假日的一項重要內容。潔身凈體、放松身心的天然快感足以惹得人們的重視,更何況沐浴在中國也很早就納入循禮的范疇,更需奉作鄭重的儀式來對待。漢朝施行“五日一休沐”,至于傳統節日,冬至“致天神、人鬼”(《周禮·春官宗伯第三·司巫神仕》)的祭祀活動,歲終的“大祭,縱吏民宴飲”(蔡邕《獨斷》),皆反映出節慶期間,民間與眾人、與天神,狂歡般的交流場面。

休假制度標準化的過程,也是休閑圍繞工作被改寫的歷史
雖然形成了頗有節律的休息規定,回望整個18世紀的西方世界,工作與娛樂的界限依然不算明晰。很多人的生活模式以工作與休閑的不規則交替為特色,歷史學家E.P.湯普森稱其為“一回合工作與一回合閑散的來回交替”。人們并沒有將每周一日的定期休息奉為圭臬,大多數時候,他們工作起來會很賣力,一天工作時長甚至超出常規的10小時標準,但一旦賺夠錢就允許自己放假,盡情享樂,直到錢花光為止,如此循環往復。因此即使在工作日,曠班也是常有的事。
為了解決曠班導致生產進程被耽擱的問題,雇主們開始訂立職場紀律,雇員則希望求得更短的工時作為接受固定出勤的條件,其中也包括減少每周工作日數的呼吁。到了1907年,經過幾次大罷工,八小時工作制在美國率先落地。而讓兩天制周末得以在此地先行實現的原因,是1929年爆發的經濟大蕭條。縮短工時被當作緩和高失業率的方法——如果每個人都少做一點,那么就有更多人有工可做。最終,新政通過1938年的《合理勞動標準法》在全美范圍內做了強制規定,即一星期的工時最高不得超過40小時。到1940年,人們對一天工作8小時已經習以為常,周休二日的制度亦水到渠成。
但還有另外一個緣由暗中刺激著人們對于勞資協議中工作模式標準化的欲求,雷布琴斯基指出,當時生產的發展使人們的財富大大增加,再加上企業主的營銷技巧和廣告宣傳從中推波助瀾,可供娛樂的消費項目多到令人目不暇接。18世紀見證著雜志、咖啡館和音樂廳的井噴式出現,職業運動比賽和假日出游也被納入到休閑產業當中。人們改變了以往的消費習慣,想買的東西越來越多,于是儲蓄和固定薪水被看得更重,人們自愿以自由來換取雇傭的穩固性。在這個情況下,自由時光和金錢形成了一組看似彼此沖突的關系,休閑與工作也漸漸分離,甚至其地位都在發生倒轉,后者的吸引力取代了前者。
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出于實效性的動機,人們將西方歷法也當作現代化改革中的一項,中國才正式接受7天的“周”制度。1995年5月1日起,中國開始執行雙休日制度。經2013年的第三次修訂,《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使我們如今看到的國家法定節假日模樣基本成形。

假期制度的規定是一個多世紀以來全球勞工爭取的結果,同時也側面反映出,世界正在被工作主導。所謂“新教徒式工作倫理”應運而生,工作本身的價值被拔高。這種倫理觀強調紀律和規則性,有意義的工作是最高級的人類活動,工作的減少會讓人類生活的質量大幅降低,不好動和懶散的工作態度會被責難。
與此同時,由于工作的物質報酬也越來越與商業化的休閑掛鉤,人們同樣渴望為了更好的消費努力工作。在雷布琴斯基的梳理中,除了商業化趨勢,休閑越來越接納全民的參與,撇除了階級與性別的禁錮。也在同一時期,中產階級選擇把更多閑暇時間消磨在家里,投注大量金錢在家居與裝潢上,戀家風氣盛行,私人聚會大規模出現。
不僅如此,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擴散流布到更大人群的范圍內,對大眾休閑提出了更有條理和教育性的要求。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代中葉就曾經有“理性娛樂運動”的倡議,原本局限于中產階級范圍內,他們呼吁在城市里籌建流動圖書館、文學社團和大眾講座,但后來把注意力轉移到了一般大眾身上,希望大眾的娛樂也應注重自我提升,而非終日流連酒館或賭坊。
許多要素疊加起來,曾經占據假日和節慶的群體儀式已不再是主流,相反,眾人的休息時間被分割成團團碎片,總體呈現出有點矛盾的畫面,雷布琴斯基在《等待周末》中就重點關注了一幅由法國畫家喬治·修拉于19世紀80年代創作的布面油畫作品《大碗島的星期天下午》,當時的大碗島還是個未被都市化開發,遠離工業污染的城郊公園。畫中的草坪上坐滿了人,階級和性別的限制被打破,但人們并不互相理會,或是看似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他們混雜在一起,卻又各自疏離。至此,節假日的面貌相比從前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轉型。

神圣時間不再,閑暇意義何來?
新教徒式工作倫理和中產階級休閑觀甚囂塵上,時間的意義也在悄然間發生改變。安東尼·吉登斯從人類的角度將時間分成了三種視角加以理解:日常生活的時間結構、生命作為整體的“生命時間”、時代和代際統領的時間。然而個體的存在有限,如何調和短暫的生命時間與前景無限的世界時間的矛盾,那就需要第四個時間層面——神圣時間——的出現。
所謂“圣潔的時間”凌駕于生活和歷史的線性時間上,是永恒的循環,具有另一個或更高級世界的特性。它也把日常生活外的節點聯系起來(如特殊節日的儀式與慶典),日常日子被分成若干個“暫停”,有了按序發生的流程。四種時間共同作用,才能真正實現意義完整性。
而現在,正如韓炳哲在《時間的香氣》一書中談到的,工業化的浸潤使時間節奏變得機械,為了高效地利用時間,它命令人按照機械的定調來安排生活,人幾乎受控于勞動。半個月前,中秋節恰好是調休安排的三天假期里的最后一天,為了工作日白天能按時回到崗位,本應照亮闔家團聚的圓月,見證了更多人離鄉上路的奔波。在被工作支配的人生里,假日自足的人文意義尚且不被重視,其“神圣時間性”就更難再現。毋寧說,假期如今已經淪為勞動的間歇,是一種為了恢復勞動能力,從而重歸于勞動的停頓,也是人們終于不被打擾、能夠“隱身”的稀缺資源。

[德]韓炳哲 著 吳瓊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4-5
沒有了神圣時間的調和,也沒有了完全的精神放松,因為休閑的含義幾乎被消費所填滿。工作的初衷原本是為了更好的生活,但商品創造的需求不斷,人們不得不反復回到辛苦的工作中,花費時間與精力,休閑的目的最終很難達到。德國學者約瑟夫·皮珀在《閑暇:文化的基礎》中將“工作者”比作西西弗斯。希臘神話中,西西弗斯遭天神處罰,推巨石上山,到山頂巨石又滾下,一切從頭來過,如此反復不已,永無止息。現代人也正如西西弗斯一樣,不眠不休地勞碌工作,卻無法獲得內心的滿足。
更有甚者,“享受閑散”對他們而言是不知所措的。亞里士多德曾經主張,人生目的是快樂,而快樂是建立在休閑上的,“我們工作,是為了得享休閑”。但休閑在被無數次偷換成“懶惰”的語義后,變得惹人生厭。即使在不用工作的假期,很多人也渴望找些事情來充實和提升自己,否則就背上浪費時間的內疚,進而生出煩悶、空虛和絕望的情緒。
皮珀認為,無論是古時人們在節慶儀式上自發地與信仰崇拜聯結,又或者是閑暇的最初本質,都飽含著無功利性,在物質貧乏的年代,人們與世界共同體驗一種和諧,并渾然沉醉其中,感受無目的的盈余。但當生活被“努力奮斗,不要停下!”的打雞血式號召和眼花繚亂的娛樂產品環繞的時候,很多人卻陷入了意義荒蕪。
《我們為何無聊》將無聊的心理狀態解釋為“沒有含義、沒有方向的渴求”,今天的人們似乎很難真正享受“無事可做的自由”,但假期恰恰允許了一段供自己支配的休閑時光,即便它需要用工作時光交換,但它給予我們內省和撫慰的機會,依然值得我們翹首以盼。
參考書目(按文中引用順序):
[美] 維托爾德·雷布琴斯基《等待周末:雙休日的起源與意義》,梁永安 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2年
[中] 李紅雨《說說中國古代的公休假》,豆瓣閱讀,2017年
https://read.douban.com/ebook/28960563/
[德] 哈爾特穆特·羅薩《加速:現代社會中實踐結構的改變》,董璐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德] 韓炳哲《時間的香氣:駐留的藝術》,吳瓊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
[德] 約瑟夫·皮珀《閑暇:文化的基礎》,劉森堯 譯,新星出版社,2005年
[加] 詹姆斯·丹克特、約翰·D.伊斯特伍德《我們為何無聊》,袁銘鈺 譯,譯林出版社,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