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期主持人 | 潘文捷
文案整理 | 實習記者 李雨桐
真人秀節目《心動的信號》第七季日前開播,嘉賓們的“Strong”(死裝)表現成為了輿論的焦點。為了塑造精英形象,節目中的嘉賓言行舉止太過刻意。不是在說話的時候夾雜幾個英文單詞,就是頻繁提及海外母校以彰顯自己的精英身份,高學歷人群戀愛成為了觀眾的吐槽點之一,有網友甚至大聲疾呼“天降二本戀綜”。
職場類綜藝節目卷學歷可以理解,為什么戀綜也卷起了學歷呢?過去有不少面向普通人的戀綜,從1988年《電視紅娘》開播,中國婚戀類節目經歷了30多年的發展。《凡人有喜》《相親才會贏》里面都是最接地氣的普通人,有大量自身條件一般但自信滿滿的嘉賓。《非誠勿擾》更是通過自我介紹、游戲才藝展示等速配環節,大幅提升了江蘇衛視的收視率。

現在流行的戀愛觀察類綜藝始于2017年韓國Channel A電視臺首播的Heart Signal,這一節目模式隨后被騰訊視頻引進,并在2018年推出了中國版《心動的信號》。這些節目在戀愛情節之外加入了推理的元素,讓嘉賓猜測素人的關系走向,嘉賓的差異化和節目的主題是吸引眼球的關鍵。在嘉賓的差異化方面,節目中出現了不同人生階段的嘉賓。比如韓國的《少男少女戀愛》以高中生為主角,中國的《沒談過戀愛的我》關注“母單”戀愛,《半熟戀人》關注年齡30+群體的戀愛,《當我們遇見你》則聚焦離異中老年的單身困境。
韓國戀綜很擅長使用主題設定,比如《換乘戀愛》以前任關系為核心,讓分手的情侶們聚在一起,回顧過去的戀愛,并面對新的緣分;《單身即地獄》設置的情景則是俊男美女被困地獄島,逃離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每晚與某人成為情侶;《著了魔戀愛》用戀綜加算命的方式吸引觀眾。
01 戀綜嘉賓的“Strong”感從何來?

尹清露:我寫過一篇關于戀綜的文章《戀愛綜藝如此流行,我們還能分辨出愛情在其中的真與假嗎?》。當我們習慣了愛情的市場化,戀綜中“卷高學歷”、“經營人設”的情節基本上是一定會發生的了。戀綜中嘉賓們比拼的其實是情欲資本,即一個人可以引起性反應的能力。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那情欲資本無形中會跟其他的資本勾連起來,比如學歷、社會地位等。一個擁有較多真實資本的人也會被認為擁有較多的情欲資本,也就是更加性感,所以很多人會覺得清華畢業生要比二本畢業生更性感。
那篇文章提到了伊娃·易洛斯的一個觀點,現代愛情中有兩種文化結構在起作用,一種是基于情感自我調節和最優選擇的理性模型,另一種是基于情感融合的強大幻想。一方面愛情已經被祛魅了,很多人認識到它本質上是一種遵循經濟關系、交換邏輯的關系,另一方面大家又想去相信愛情中很真誠很純粹的部分,相信“沒有道理的喜歡”。
我們一直生活在這個永恒的悖論之中,戀愛綜藝展現的也是這種悖論以及悖論的博弈。但有時候它會更凸顯出前者,讓觀眾感到格外不適,很生氣愛情怎么能夠是這樣物質的。一方面,這兩年國內外都出現了很火爆的戀綜,這種資本博弈被推到了更多人的面前;另外一方面,炫富的內容也越來越不受歡迎了,現在流行的可能是像普通人于文亮這種凸顯日常生活點滴的內容,而不是《和卡戴珊一家同行》了。我們不太奢望自己能夠變得富有,也不會覺得有錢人跟自己的生活有太大的關系。
丁欣雨(實習記者):網友吐槽“Strong”的原因也可能在于,從嘉賓的行為風格當中窺探出了一種明顯指向社會地位的氣質,這種氣質被社會學家布迪厄稱作“趣味”。他認為任何文化實踐的參與都帶有階級屬性的色彩,而個人的審美趣味根源于與階級教養和教育相關的社會地位。這里面既包含了先天出身上的不平等,也包含日后教育會拉大這種不平衡的可能,所以,個體累積的文化資本就帶有鮮明的等級性。而通過消費,資本的象征性價值會被顯示出來,傳遞社會等級結構的存在,進而成為區隔大眾和精英的標志。
圍繞“趣味”存在一條鄙視鏈,形成了一種劃分高下的價值判斷。精英文化通常被認為是崇高的、高雅的,大眾文化往往跟低級、粗礪、庸俗的形容掛鉤,很容易引發不滿。上層的少數人對于符號的稀缺性的長期壟斷,對于本不存在于這個體系內的人群的無情排斥,讓中產階級對于真正實現階級躍升的難度感到焦慮。
《心動的信號》這一季被吐槽最多的橋段,是幾位嘉賓在討論最喜歡的英國城市時本來已經說出了中文,隨即又改成了英文稱呼。但鑒于節目中有來自中國香港地區的嘉賓,內地和香港地區的翻譯體系存在差異,同一個英文單詞音譯過來的中文也不大一樣。如果在他們都共同知曉某個英文單詞意指的前提下,說英文反而可以節省翻譯的過程,是更加高效的溝通辦法。
王鵬凱(實習記者):我也有這個感受。我之前在香港地區交流的時候,室友是澳門人,他的普通話不太好,但是我又不會說粵語,所以我們在交流的時候會用一些共同的英文單詞來讓彼此相互理解。感覺在香港大家會默認各自母語不一樣的情況下,用英語會更加方便交流。《心動的信號》這個場景應該不是為了特意去炫耀什么。

董子琪:在約會這種場合里面,語言還是蠻重要的,會影響到對方對你的第一印象。
丁欣雨:香港人雖然有說話夾英文的習慣,但他們日常也會上普通話的課程,戀綜里的那兩位香港嘉賓對于內地人們日常溝通的話術還算比較了解,揀選語匯的過程是在對不同的身份做出挑選。文化歷史學家沃倫·薩斯曼認為,在19世紀,“自我”還是作為一個整體性的性格概念被呈現出來,從20世紀初葉以來,自我協商與呈現方式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為了給他人留下一個好印象,或者是便于自我形象的管理,“自我”有史以來第一次成為了某種可以被組裝和操縱的東西。在他看來,在強調刻意的自我管理和形象塑造以便取悅和吸引他人方面,消費文化和時尚產業功不可沒。“自我”需要有能力對不同的社會環境產生敏銳嗅覺,據此扮演不同的角色,以便應付自如。其中就包含著在“自我”的身體、言語模式、舉止和著裝方面進行有意識地選擇和搭配。
戀綜嘉賓們從中文切換到英文的行為本身可能也考慮到了當下的語境,覺得此時使用英文會更得體,或者更能突出一種身份,展現情欲資本。但如果將這樣的細節解讀作“Strong”,觀眾所代表的社會心態縮影也值得考究。
潘文捷:前幾天看到一個新聞,講的是現在很多高校中研究生數量超過本科生,出現了本研倒掛的現象。在學歷膨脹如此嚴重的情況下,高學歷的精英身份好像沒有過去那樣的含金量了,社會上對他們的評價也從肯定崇拜逐漸衍生出了質疑。
王鵬凱:觀眾對于戀綜里面的高學歷精英人設基本上已經脫敏了,有人還會嘲笑那些英國留學生是“一年英水碩,一生英倫情”。但我也注意到,《心動的信號》中的幾個嘉賓的家庭背景確實是富裕的,觀眾對于他們的評價就會和對高學歷人設嘉賓的評價不太一樣。這或許也反映出,觀眾們已經不再期待靠讀書或者靠高學歷去成為精英,換取階層躍升和財富積累,而是會更加崇拜來自家庭的既有財富積累。
尹清露:現在留學生都自嘲自己是“留子”,這個稱呼感覺包含了了很多貶義和不值一提。
董子琪:但當一個人以“留子”自嘲的時候,其他人還是會覺得在“凡爾賽”,因為大部分人還沒有機會或者是條件去留學,當“留子”。
02 “用過即棄”是戀綜明星的宿命嗎?
董子琪:我以前看了很多期《非誠勿擾》,在此之前的小時候還看過《非常男女》,是鳳凰衛視引入的一檔古早的中國臺灣地區相親綜藝。《非誠勿擾》采取的是速配模式,節奏非常快,先用VCR放一下男女嘉賓的情感經歷,然后看每個人有什么要求,最后如果能看對眼,三觀相符,差不多就算牽手成功了。
我對節目中關于戀愛的文本更感興趣,在最后的選擇環節,男女嘉賓都會問對方一些問題,比如男嘉賓可能會問女方“你介意跟我媽一起住嗎”,女嘉賓可能會問男方“我可不可以跟你異地呢”,這些問題感覺都非常簡單。現在的戀綜好像傾向于慢慢展現每個人到底有什么經歷、有什么特別之處,雙方互相了解的部分似乎慢下來了。
我還看過一個節目叫《中國式相親》,節目的模式是家長來選,孩子則在觀戰間看,家長選完之后孩子再出來發表自己的意見。在過往的這些速配相親節目中,我沒覺得學歷是個很重要的因素,感覺那時候很少有人提這件事。
徐魯青:我也看過《中國式相親》,父母的評價標準是身體健康,看上去是不是姿態宜人的,還有年齡這一關,女孩要盡量小一點。有一次我在賓館百無聊賴打開電視,正好看到一個地方臺的相親節目,機制是男方從幾個女方里挑選亮燈,最后一關留給男方父母做出選擇,父母會坐在最重要軟皮沙發席,偶爾插幾句評價女方的話,那天晚上我看這個節目看了好久,又氣又覺得很好笑。

董子琪:《幸福三重奏》是一檔講夫妻感情的綜藝,當時有三對參加,現在有兩對都已經離婚了。當時覺得最無聊的是福原愛那對,因為他們兩個人總是在秀恩愛,類似于要集齊100個吻這樣,沒有情節,他們吵架的時候會好看很多。戀綜好像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進入名人生活的途徑,這種進路(approach)是人人都可以挑選的。
在港臺情歌流行的時期,音樂就是一種通向戀愛想象的途徑。張韶涵的歌曲是校園戀,蔡依林的《布拉格廣場》是跨國戀,《愛在西元前》就是穿越時空的戀愛。我之前看的一本書講到了曲詞和歌手形象的關系。比如林夕的詞和王菲是互相成就的,王菲的形象很貼和歌詞;還有些歌是專門為梅艷芳打造的,因為只有她能夠演繹出來這種楚楚動人的、孤獨的都市女性形象。這段時間大家可能是通過這些歌曲來想象他人的愛情,擺正自己的位置,讓女性擁有一個自我演言說的空間。
在《幸福三重奏》中,鏡頭會直接拍嘉賓們的床,這是很近距離的揭示。綜藝之所以讓人感到刺激,是因為它是真人真事,但當鏡頭距離過近的時候,也會帶來一種對于光環、感情、人格還有戀愛美感的消耗。
潘文捷:《娛樂新聞小史》一書講到了真人秀明星的經濟學。作者解釋道,傳統的名人成長周期比較長,成本很高,影視行業需要一種傳統名人的廉價替代品,所以出現了平民名人,其中就包括真人秀明星。真人秀明星有幾個特點,一是普通性,這些明星不需要有傳統明星那樣的天賦、技藝和成就;第二是相似性;第三是短暫性,他們不能長久立足,因為他們彼此是高度相似的,所以很容易相互替代。參加真人秀的素人本質上是一種快消品,而不是耐用品,是名人產業的配飾,他們在制造工藝上就包括了計劃性過氣的環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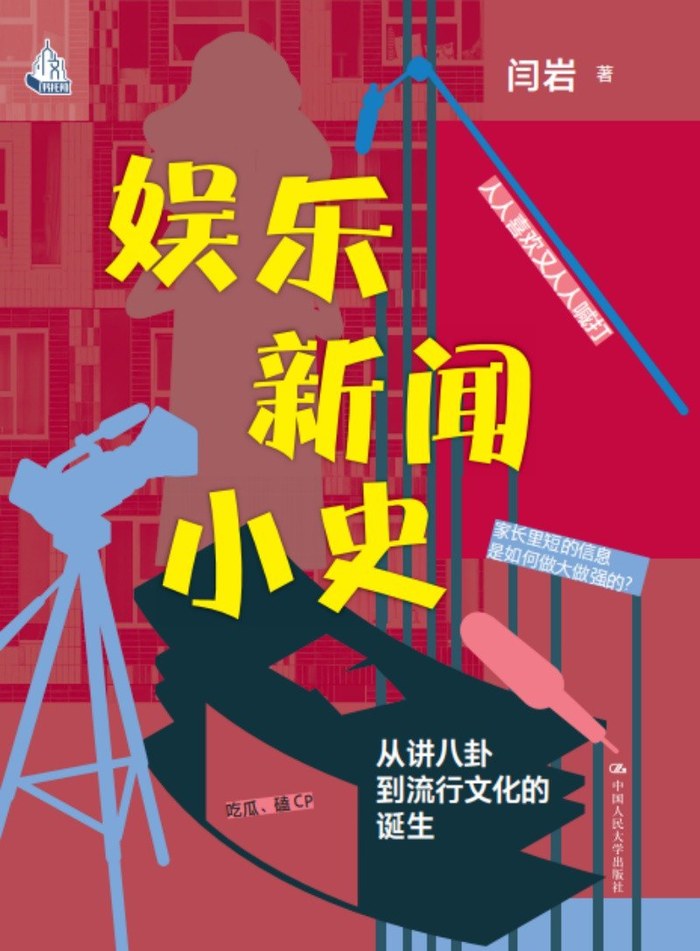
閆巖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4
很多關于戀綜的討論都是在說女一男一怎么樣,素人的名字并沒有被記住。對于這些素人來說,他們可以短暫成名、變現、被消遣,成為一個可供談論的符號。制作真人秀節目的直接原因是行業需要壓縮成本,而素人們的出場費往往都比較低。加之真人秀明星是快消品,所以一年可以推出好幾個戀綜。戀綜的嘉賓們在其中處于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
尹清露:那這些明星豈不就是娛樂圈中的實習生?用過即棄。
Lauren Tsai是從戀綜《Terrace house》出來的比較有名的素人,長得很漂亮,是一名插畫師,也是一名模特。她的成長路線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素人明星計劃性過氣的定律。很多戀綜最后成名的都是CP,有自己的CP粉。但CP綁定是不穩定的,分手之后粉絲也會流失掉。但Lauren比較聰明,在節目剛開始的時候,她也試圖和喜歡的男生組CP,但那個男生可能不是特別喜歡她,所以后來Lauren Tsai基本沒有在談戀愛上太費心了,自己在房間里面畫畫,相當于把戀綜變成一個展示自己畫技的一個平臺。后來她變得有些名氣了,會更接到更大牌插畫或者展覽的訂單,包括Vogue也經常邀請她做拍攝。她可能算是打破了計劃性過氣的魔咒,很有趣。
這個例子也說明,戀綜或者說素人綜藝這個空間的意義是游移的,會隨著素人明星或者參與嘉賓的一些表現而出現各種偏轉,嘉賓需要自己摸索出奇制勝的道路。戀綜綜藝和拍戲是很不一樣的,在綜藝里,扮演跟真實的邊界很模糊,我們也不知道嘉賓到底是在立人設還是在展現真實性格,但我們知道拍戲一定是演的,演員不用對戲里的人設負責。
所以,如果在綜藝里的人設和現實差異很大的話,塌房也會比較徹底。宋智雅被扒出穿香奈兒假貨之后就徹底塌房了,因為她之前立的圈粉人設是一個很有錢的富家女。但Lauren Tsai是有一技傍身的,而且她也不“strong”,去堆砌很多學歷和身份,所以她的粉絲還是比較牢靠的。

王鵬凱:我不算是傳統戀綜的受眾,之前只看過《再見愛人》團隊制作的另一檔戀綜《春日遲遲再出發》,這檔節目主要呈現的是八名尚未從前段失敗婚姻走出的單身男女結伴而行,在陪伴的過程中重新收獲心動的勇氣。在節目中,大家有很多時間去講述過去在情感中受到的創傷和經歷,也包括自己個人的成長歷程,彼此之間會相互關懷治愈。整個節目節奏很慢,沒有人會急著組CP。
這一次看《心動的信號》,我會覺得節奏真的很快。還沒相處幾天,就已經基本確定誰和誰是一對了。可能現在的戀綜相比于《非誠勿擾》這種傳統戀綜是放緩了節奏,但我感覺它相比于前兩年的素人戀綜又是在加快的。
尹清露:我也覺得違和感特別強,怎么可能剛認識一兩天就真的心動了呢?之前看的《心臟信號》好像也是這樣,如果嘉賓進去之后沒有及時跟別人配好對,ta在生存游戲中就輸掉了。后面的《單身即地獄》也是以這個為賣點。
戀綜中還有一些很戳觀眾的點,比如有人在節目開始以后會很心急地想要配對,觀眾反而會覺得這人怎么這么心急。我記得《單身即地獄》里面有一個女生叫姜素妍,她就比較心急,比如說第一晚上跟這個男生搭配了,后面幾晚她會一直依賴這個男生。但這個戀綜的規則是不停更新配對,并重結新的配對。她好像成為了那個沒有習得愛情游戲的人,反而是像宋智雅那種根本不在乎跟誰配對的人,站在了食物鏈的頂端,每晚都有人和她配對。這里也能看出來很多和人性有關的東西。
03 戀愛導師能解決親密關系中的所有問題嗎?
丁欣雨:《心動的信號》系列更關注對于人際交往中蛛絲馬跡的推理,所以稱其為“信號”,很多時候只是相對曖昧不清的線索,并非完全實質明了的感情。
戀綜也有加花字的習慣,我觀察到本季《心動的信號》里彭高看到翁青雅會緊張,說話支支吾吾,觀眾明明能夠看出來,但節目一定要加上“結巴”“緊張”的花字來標注。彭高在對青雅笑的時候,即使所有觀眾都看出他在笑,節目組也要另外加上“笑”的花字。戀綜想把嘉賓所有動作細節都通過添加花字來放大,讓觀眾感到嘉賓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是情流暗涌,這種刻意的做法有過度解讀的嫌疑。
潘文捷:《倍速社會》講到大家現在不想要那種看不明白的東西。用花字直接告訴觀眾到底發生了什么,也呼應了信息即時性的需要。
我在微博看到過一條有關《心動的信號》的熱搜,是講“言承旭自曝心動女生”,場外嘉賓通過講述自己的戀愛心得,也可以獲得相應的流量和關注。這種戀綜好像塑造了一個雙贏結構,一方面是素人得到關注,另一方面作為場外嘉賓的流量明星還可以再炒一波話題。
丁欣雨:《再見愛人》是另一檔婚姻紀實觀察類真人秀,它著意探討親密關系中暴露的問題和難解的矛盾。在節目中,正片內容是離婚嘉賓或瀕臨離婚的嘉賓共同旅行,場外也設有觀察室,觀察室里的明星嘉賓大多有著不同的婚戀背景。既有母單solo、離婚人士,也有家庭幸福美滿的人。不僅如此,節目也會邀請有社會學以及其他知識背景的公眾人士做觀察員,圍繞節目展開親密關系議題的分享。

董子琪:原來《非誠勿擾》里面也有社會學方面的老師,從專業角度進行點評,或者給男女嘉賓一些建議。這些建議聽起來都很扎實,比如要增進彼此的了解,要互相更好地溝通,要攜手在人生中共進。他們有時候會扮演類似智者的形象,幫嘉賓點明“愛情迷津”。當時覺得他們給的建議都很有道理,現在也會懷疑,他們真的能解決親密關系中的所有問題嗎?
這種導師的形象在這幾年的戀綜中也有體現,比如在《我家那閨女》《我家那小子》中,節目設置了一些觀察員的角色。他們會從自己日常生活的角度來提出一些建議或者是評價,原先由一人承擔的智者形象平均分給了這四五個人。這讓我覺得好像觀眾看個戀綜,都需要依賴這些“情感導師”的意見來確認自己對場內嘉賓的理解是否正確。他們的意見很多時候也很容易引導大眾的看法,比如“果然,就是不能太過信賴他人”、“果然,不能對他人托付所有”、“果然,做人就是要留一手”,感覺很像情感厚黑學。
徐魯青:最早對情感觀察員的印象是《非誠勿擾》里的樂嘉,后來看《再見愛人》觀察員的角色就占比好大,沈奕斐由此被大眾熟知,她是一位專門研究愛情婚姻的社會學學者,再搭配一個心理學家,看上去能分析得比普通觀眾更多更透。如果我是節目里的人,肯定超級緊張,一舉一動都要被四五個人圍著分析潛意識和原生家庭,那種分析和闡述有段時間讓我很厭倦,好像情感表現變成了一種病理分析對象。

丁欣雨:《心動的信號》也有地域上的特色,每一季都會在不同地區錄制,之前有上海、北京、深圳,這次是在大灣區。在大灣區,大家生活節奏很快,尤其是在港珠澳大橋建成通車后,大灣區居民只需要1.5-2個小時就可以見面,時間的縮短幾乎消弭了以往由于距離導致的異地障礙。這季節目的快節奏也可能為了符合這個城市群的生活節奏。
印象最深刻、百看不厭的應該就是初相識時的一見鐘情橋段吧。比如《心動的信號》第四季陳思銘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對方彬涵的興趣,以及本季當中彭高在第一次見到青雅后立即明確心意,開始“打直球”。一見鐘情的確是一種非常獨特美妙的情感,非常符合浪漫愛的概念,它的由來不是基于對他人任何累積性的了解,是非理性、沒有辦法被解釋的。它把他人辨識為特殊的唯一存在,甚至對他人性格產生一種偏向直覺的把握,也很篤信這份直覺。
但也是在看這季節目的時候,我突然感覺出一絲不對勁。在彭高正式見到青雅前,已經有很多觀眾根據他們倆的外形、性格還有其他條件的匹配程度開始磕CP了。這個禮拜節目播到新的女嘉賓王琪入住心動小屋,觀察室里的饒雪漫立刻感覺她跟一位叫TOMO的香港男嘉賓很般配,直接把兩個人的CP“鎖死”。我頓時有種出戲的感覺,因為我意識到,在這種類似命中注定的浪漫情節背后,其實是節目組在茫茫互聯網中費心評估和挑選的一系列過程。選角導演已經提前為嘉賓考慮了彼此是否門當戶對,以及他們間的互動會不會產生令觀眾期待的的化學反應,最后基于對他們可能產生浪漫愛情幾率的預設,才敲定了嘉賓人選。本來在我看來非常自然、仿佛天降神諭般的愛情,其實真的潛藏著上帝視角,也就是節目組理性的計算。
潘文捷:在有這么多準備的情況下,戀綜節目還是出現了很多素人塌房的情況,之前還看到有一個報道說戀綜的素人塌房已經流程化了。報道中講的是一個2022年的戀綜,叫做《怦然心動的20歲》,被譽為“早上官宣,中午出道,晚上退圈”,創造了素人戀綜史上的最快塌房記錄。其他戀綜也有很多塌房的情況,比如有《沒談過戀愛的我》,在節目剛要播出的時候,網上就曝出里面的男一談過三個女朋友。戀綜的真實性真的很堪憂。
董子琪:在現實中我們不會去世界各地,窮盡各種資料來尋找所謂的“全天下最適合我的人”,最美妙的感情就像簡·奧斯汀在小說里寫的那樣,隔壁的莊園來了一個人,這種機緣是天成的。
戀綜劇本對素人的操控是很有風險的,因為人很復雜,不太會符合別人的設想和心意。
尹清露:我之前有一個觀點,那些有固定伴侶的人,如果是在社交軟件上劃到自己的伴侶,那TA大概率并不符合自己的擇偶標準、顏值標準等等。只有在真實的生活中相遇,你們才會相愛。
潘文捷:有篇報道標題是“韓國戀綜大火背后竟是不婚盛行”,講的是雖然戀愛綜藝越來越多,但與此同時,大多數觀眾的綜合生育力創了歷史新低,單身人士越來越多。這感覺好像是一個完全相反的社會現象。
尹清露:夢女也是如此。我看有人問“夢女現實中會有喜歡的人或者是對象之類的嗎?”夢女回答說,如果你真的夢到了一個如此完美的人,你根本不會對這些現實中的男性產生興趣。
王鵬凱:之前的文化周報提到一個現象,最近幾年情色電影重新回歸熒幕,背后對應著一種心態,就是年輕人看起來似乎對兩性關系或者對情愛特別冷淡,但其實反過來他們會更期待在屏幕中看到親密關系的呈現。
丁欣雨: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在《親密關系的變革》中寫到,狂熱地消費浪漫小說和愛情故事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消極性的見證。個體在夢境幻覺中追逐在日常世界被否定而無法得到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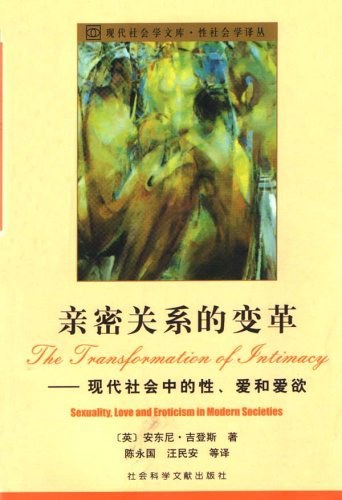
[英] 安東尼·吉登斯 著 陳永國 汪民安 等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2
對于喜歡看戀綜的觀眾而言,他們可能沒法在每天下班后有精力和余閑去建立、發展和經營一段親密關系,也沒有機會走入一個能與很多陌生人共同居住、集中接觸交往的空間,這些是親密關系存在條件的一種欠缺。但更主要的是,浪漫愛情究竟存不存在,又有多大概率能降臨在對它有所向往和期待的人們當中呢?多數人可能在現實的受挫中感到理想愛情的虛妄,所以在一段真實關系開始前,往往就先表現出退縮和怯懦,此時看別人談戀愛正是一種無痛就能體會到甜蜜情感的代償機制。
戀綜在中國層出不窮也意味著它可能擁有正向的社會價值,符合當下的政策轉型,在越來越多人結婚年齡推遲,結婚率也有所降低的時代,戀綜渴望用榜樣的力量讓觀眾相信愛情。但如果發現人們喜歡看戀綜的原因反而是出于不想或者不敢親自投入戀愛,就會感到這是一件有點諷刺和吊詭的事情。
王鵬凱:社會學家伊娃·易洛思有幾本著作都在討論情感的資本主義化,她有一本沒有被翻譯的文集叫《情感作為商品》(Emotions as Commodities),書里進一步討論了這個話題。她認為情感資本主義化的具體表現是情感被作為了一種商品,而這其實是一個被表演的過程。在情感關系中,人會去購買一些東西來獲得對應的情感體驗,也會將一些情感體驗作為商品去販賣。比如說戀綜里面的嘉賓送禮環節,送禮物就是一個很典型的通過商品去傳遞情感體驗的過程。
易洛思認為,在這個過程中,人在追求的東西就是authenticity,可以翻譯成“本真性”。其實看戀綜的人也在追求“本真性”,真人秀雖然在強調“真”,但這個“真”其實是被表演出來的,只是一個在情感上能被感受的“真”。它是通過一系列的行為,比如說商品的購買、人設的建立、流行文化的一些表現所表演出來的。在這個背景下,戀綜嘉賓的塌房會顯得很脆弱,因為他們打破了觀眾對于他們的期待和情感投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