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娛樂硬糖 劉小土
編輯 | 李春暉
長沙各小學開始抵制煙卡了。所謂卡牌,是商家正版販售的動漫IP卡片,通過盲盒抽卡、卡牌分級帶來包括收集、賭博、社交等多重滿足。煙卡則是用煙盒疊成的“自制卡牌”,除了可以就地取材、拍卡贏取,其余玩法基本相同。
硬糖君是今年3月發現周圍的小孩都在玩煙卡,詢問了長沙幾所中小學的老師,才知道學校里已經展開“禁煙卡”運動。半年后,幾位老師告訴硬糖君,不同區域學校禁煙卡的效果大不相同。
融城小學(化名)禁煙卡的最大阻力,正是來自學生家長。
該校幾位班主任告訴硬糖君,他們曾多次通過家訪和班會,向學生家長科普玩煙卡的危害,還與一些過度沉迷的重點對象進行一對一談話,但都收效甚微。“家長態度敷衍、意識不到嚴重性,小朋友更加有恃無恐了。”
在長沙兩百多所中小學里,融城小學的綜合排名相當靠后,主要吸納鄉鎮務工人員子弟,因此能拿到大量貧困生指標。相較其他實力雄厚的學校,它的硬件設施其實并不差,但內里明顯不同。這一點直觀體現在艱難的禁煙卡運動里。
趙長生(化名)是融城小學的“煙卡王”。是他最先將這個游戲帶到學校,不只在班內培養一批徒子徒孫,還在外班、外校揚名立萬。但更讓老師頭疼的還是趙長生的家長。他們無條件支持小孩玩煙卡,認為這只是一種免費娛樂,還會主動幫忙收集煙盒。
然而你也不能說家長的選擇有什么錯。這很容易讓人想到《了不起的蓋茨比》開篇的那句忠告:“每當你想批評別人的時候,要記住,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擁有的那些優勢。”
受限于家庭條件,他們的小孩無法擁有豐富的文娛生活,很難在學校這樣的公共空間找到歸屬感和存在感。煙卡的出現,讓這樣的中小學生也找到了一條鏈接現實、鏈接集體的捷徑。煙卡,是小孩自己發明的社交平權。
隱形學生,走向集體
趙長生并不是典型的問題學生。他性格靦腆、不善言辭、成績中規中矩,總結下來就是班里沒什么存在感的小孩。因此,當班主任得知他是班里最愛組織玩煙卡、且是擁有最多煙卡的同學時,非常震驚。
據趙長生回憶,今年春節時,他逛公園看到小孩扎堆拍煙卡,自己就產生了興趣。趁著放假,他搜集了大量煙盒制成煙卡,返校后開始四處推廣這種新游戲。最初通過出借的方式讓同班同學試玩、陪玩,直到大家慢慢開始主動收卡,他才進一步科普更專業的玩法和規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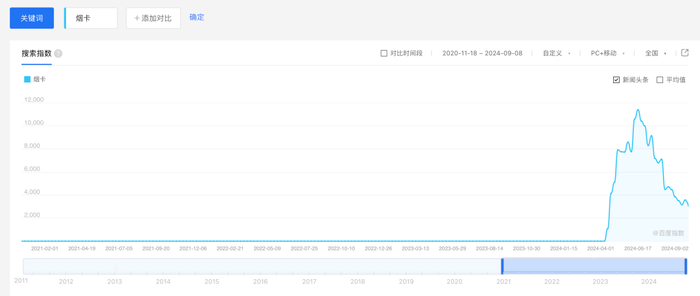
就這樣,班上玩煙卡的人越來越多,“他們都來找我借卡、換卡。”如此普通的自己,突然得到了大量的目光甚至擁護者,這是趙長生讀書三年來從未有過的待遇。他不知如何描述心理變化,只是反復強調“巨開心巨開心”。
被“粉絲”和快樂包圍的趙長生,開始在學校組織拍煙卡比賽,讓更多人沉醉在這種激烈競爭里。很多老師也告訴硬糖君,競技取代收集的過程中,零散的煙卡玩家聚成更大群體,拍煙卡迅速成為學生們一項日常的固定游戲。
同學們拍煙卡的水平大不同,內部也逐漸形成等級之分。就說趙長生,他展現出極強的游戲本領,在融城小學擁有絕對的江湖地位。他的活動范圍不局限在自己班,常常代表同學、隊友去跟其他班級比賽,連勝七十多場的戰績至今無人能破,在整個年級、乃至整個學校負有盛名。

對趙長生來說,想在考試或才藝上擁有這般影響力,幾乎沒可能。他終于成為同學們討論、比較、追趕的對象,還得到了一些正向的區別對待。為了維持這種榮譽,趙長生有段時間一回家就練習拍煙卡,一度練出了腱鞘囊腫。
一句話,煙卡是小孩自己開辟的一條新賽道,用來獲取他在傳統賽道無法取得的社交威望。
自從迷上拍煙卡后,趙長生也變得樂觀開朗了。他告訴硬糖君,許多同學爭著跟自己玩,“有些人還叫我師父、師爺”。幾位班主任也反饋,這正是禁煙卡運動的一大分歧點:一些學生確實從游戲里得到了積極反饋,強令禁止會讓他們產生抵觸情緒。
對于家長來說也是如此。無論老師如何溝通、解釋,趙長生的爸爸對禁煙卡都拒不配合。他的理由很簡單:
“我一個保安,沒什么文化,也沒什么能力,小孩以前可能覺得這工作沒面兒,跟我沒什么話說,也不讓我參加家長會。現在他主動找我收煙盒,還帶同學朋友一起來我們市場。他快樂我就快樂,玩個游戲哪來那么大危害。”
制定秩序,破壞秩序
哪座城市是煙卡游戲的發源地?媒體報道里,普遍的說法是在湖南、廣西、海南等地的中小學生中流行。但趙長生堅定地糾正,“肯定是湖南先玩,其他學校再學我們的。”
他給出了兩個理由。一是,和天下、芙蓉王、精(軟)白沙等煙卡的數量最多,這些香煙品牌的產地都是湖南。因為擔心影響本地煙卡的優勢和重要性,他們甚至會設立比賽參與門檻,把那些外地香煙品牌排除在外。“我搞不到,就讓大家不要跟有那些煙盒的人玩,反正我們人多。”
二是,除了蝴蝶拍、蚊子拍、單手拍這些常規玩法,他們曾自創了雞爪拍、超遠炮、蛤蟆拍等新招式。“我刷視頻發現,外地學生都在學我們的姿勢,那我們肯定是最專業的、最權威的。”
趙長生非常在意誰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比如說,每一張煙卡都有嚴格的等級劃分,通常是按普通、高級、稀有升序排列。但在融城小學,煙卡玩家使用的是傳說、史詩、神話這套說法,這是趙長生從武俠小說里學來的,“大家都愿意聽我的”。
但商業煙卡的出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趙長生們”的優越感。首先,他們辛苦收藏、贏取的稀有卡片變得不再珍貴,這些都能在電商平臺輕松購得。十幾塊錢就能買一百張,什么款式都有,很多店鋪的拼單量多達幾百萬件。
融城小學門口的小賣部,成列擺放著和天下、黃鶴樓等珍稀煙卡,這些讓趙長生引以為傲的東西被明碼標價出售。稀缺煙卡的含金量驟降,“那些實力不如我的同學,花三五塊錢就能買一張史詩級煙卡,氣死了。”
趙長生很清楚,同學們喜歡跟他一起玩,主要是想從他手里贏走一些煙卡。而當其他同學也有了高級別煙卡、且輸多勝少時,大家自然更愿意挑戰這些弱一點的人民幣玩家。煙卡倒爺的出現,讓趙長生慢慢失去了操縱這場游戲的快感,他的地位和信心都在坍塌。
但當市面開始出現大量盜版、印刷的煙卡,局面再次發生逆轉。趙長生抓住這個機會,整理總結了一份煙卡鑒定資料供同學們傳閱學習,并展開了大規模的抵制劣質煙卡運動。打起維持圈層純潔性的大旗,他暗戳戳地排擠了鈔能力玩家。
趙長生再次奪回領導地位。加之熱心網友倡導禁煙卡,電商平臺下架相關產品,也讓煙卡重回原有價值框架。
趙長生告訴硬糖君,帶頭孤立盜版煙卡玩家時,自己心里其實并不好受。“我以前沒有錢,也買過奧特曼的盜版卡片,有同學笑話過我,挺難過的。”屠龍少年終成惡龍的俗套故事,也有卡牌版本。
小孩都能玩什么?
自打互聯網掀起禁煙卡的輿論巨浪,不乏吃瓜群眾提供解決方案。其中呼聲最高的,說可以保留這種兒童文娛活動,只要把煙卡換成其他“健康的卡牌”。老一輩玩的水滸卡,就沒啥副作用嘛。
殊不知,并不是市面上沒有選擇,而是小孩子沒有選擇權。
奧特曼卡、小馬寶莉卡算是健康的卡牌嗎?有數據顯示,相關公司一年能賣出幾十億的集換式卡牌。硬糖君也逛了融城小學周圍的大小商城,都有出售葉羅麗、奧特曼等卡牌,定價在幾塊、十幾塊不等。粗略估算,集齊某一個系列的卡牌花費動輒幾百上千。
而卡牌公司品類煥新的速度越來越快,某些產品剛買到手可能就過氣了。與此同時,在盲盒玩法的催化下,拆卡早已變成一種易上癮的游戲。這些都意味著更大的投入成本。
在迷上煙卡之前,趙長生也希望擁有一套奧特曼卡牌。但無論他如何苦苦哀求,爸媽的回答始終是“浪費錢”。趙長生的爸媽告訴硬糖君,他們也想支持小孩的興趣愛好,“收入只夠日常開支,實在沒能力由著他玩。”
相較于無論什么樣的成年人可能都在刷抖音、看劇綜、打游戲,今天的兒童娛樂可能更貧乏、也更割裂。
中小學生探索和社交的欲望強烈,與之匹配的文娛資源卻很有限,他們的訴求根本得不到滿足。尤其在低線城市,家境普通乃至困難的小孩只能把時間消磨在互聯網,分享熟齡用戶的文娛內容。
線下娛樂的豐富程度,則與家庭背景緊密相連。融城小學的一位班主任告訴硬糖君,她之前去北京參加培訓,聽很多一線城市的老師說起帶學生去迪士尼、環球影城做社會實踐,“但凡要交錢的活動,我們那里的家長都非常不愿意、非常抵觸,甚至懷疑學校亂收費,我們現在都不怎么組織外出游戲了。”
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什么煙卡在低線城市更流行。這種低成本游戲的出現,讓那些無法支付昂貴文娛消費的中小學生,也擁有了自己的社交主場。
如今的高性價比兒童娛樂實在太少,學校為了避免意外傷害也在減少中小學生的社交活動。硬糖君上小學時,老師帶我們找片荒地種樹都覺得好快樂,現在學生去郊區體驗農作都得花上幾百塊。
曾經的趙長生,沒有跟集體、社會鏈接的通道,也沒有發現自我、證成自我的方式。玩煙卡不利兒童身心健康,但沒什么東西可玩,是另一種精神摧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