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陳璧君 記者 尹清露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按:“正面連接”的報道《從家中偷走一個11歲女孩》日前引發廣泛關注,也再次激起了關于“兒童之惡”話題的討論。那些孩子為什么會親手領著他們的“朋友”走上被侵犯、被強奸的道路,他們自己又遭遇了什么?近幾年來,每每有殘酷的校園霸凌、未成年人傷人甚至殺人事件發生,類似的話題一再被提起。是今天的孩子變得更道德敗壞了嗎?為什么會這樣?我們的社會出了什么問題?如何才能規避這一切,孩子應該受到怎樣的教育或怎樣的懲罰?而因倫理和隱私方面的復雜考量,對這些惡性事件背后真實的兒童困境的分析往往浮于表面,這不僅無益于困境的解決和兒童的福祉,也加劇了成人對兒童心靈的誤解和偏見。
我們都曾是兒童。從童年到成年是天然的還是人為的過程?對兒童來說,那些成年人難以理解的游戲僅僅是一種消遣嗎?兒童世界的暴力與創傷歸根結底是成人世界造成的嗎?成人又應該怎樣看待所謂“童真”呢?西班牙作家安德烈斯·巴爾瓦(Andrés Barba)的文學創作,在某種意義上拋出的就是這些問題。
巴爾瓦的小說展現了神秘的、野蠻的甚至駭人的兒童世界,顛覆著成年人對純真童年的扁平幻想,也挑戰著現代人未經審視的生活態度。在《光明共和國》里,小鎮褪下平靜的表象,森林中的孩子們來路不明、行蹤詭秘、持刀殺人,社會規范和道德秩序逐漸崩塌;在《小手》里,小女孩在孤兒院被殺死,而她們只是在實踐著屬于自己的“愛的游戲”。這兩部小說向成人讀者拋出了尖銳的問題:當一個社會無法接納、拒絕承認甚至是忌憚恐懼于兒童的天性,身處其中的人是否都應為此負責?

巴爾瓦的創作幾乎總是概念先行的,對語言哲學的敏銳洞察與他的現實關注密切交織,于是有了一個個烏托邦的又或者是反烏托邦的世界。從這一點看,他的寫作同時有著很強的行動性,在兒童文學里創造游戲的花園,給予孩子真正的玩樂時光,在政治寓言和奇幻敘事中締結承擔的、反思性的思想主體。正如他自己所說:“沒有新的語言,就無法創造一個新的社會。”
01 兒童的暴力令人震驚,因其動搖了成人對童年的美好幻想

界面文化:你的許多小說都深入探討了兒童的精神世界。此外,你還創作了4部兒童文學作品。你為什么如此關注兒童群體及童年主題?
巴爾瓦:童年在世界各國的文學史上都是一個母題。童年凝聚了社會所定義的童真、純潔的力量,吸引著成人的關注,也會引發社會的情緒。不僅是童年的概念本身,社會文化對童年的整體情緒和態度也值得關注。
西方社會文化對兒童和童年的態度總是自相矛盾。一方面,童年被視為如天堂般沒有義務或規則、只有純粹的快樂與本能的階段,成年人對此羨慕不已;另一方面,成年人又恐懼童年,因為孩子們是如此純真且富有能量,我們難以真正洞悉他們的內心。
界面文化:你在一次訪談中提到,“童年”這個概念本身就是非自然的產物,“童年是快樂無憂的”這種看法也是非常現代的。這讓我想到尼爾·波茲曼的著作《童年的消逝》,他認為印刷技術普及導致知識的口語傳播形式被文字讀寫取代,“童年”就產生于這種人為的文化鴻溝中。你認為當下社會對“童年”的看法是否存在著類似的鴻溝或誤判?你創作兒童文學作品時,是以成人的視角還是以兒童的視角來創作的呢?
巴爾瓦:社會創建了教育體系和各類機構,期望盡早將他們培養成公民和成年人,童年與成人之間的文化鴻溝也就被人為地消除了。當某件事物像這樣引發兩種迥異的社會心理,一邊羨慕一邊恐懼,就說明我們無法與其中蘊含的能量和諧共處,這尤其體現在童年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方面。
另外一個我很關注的元素是暴力——不是成人對兒童的暴力,而是發生在兒童之間的暴力。實際上,暴力似乎也是童年階段的一種自然狀態,但我們為童年構建了一種如天堂般的幻想,認為那是不可觸碰的幸福與純真。看到孩子們表現出眼神、肢體上的沖突行為時,我們往往感到震驚和緊張,因為這動搖了成人對童年的美好幻想。當然,我在想象兒童之間的暴力和交往過程時,因為沒有辦法真正走進它,本質上也是一種虛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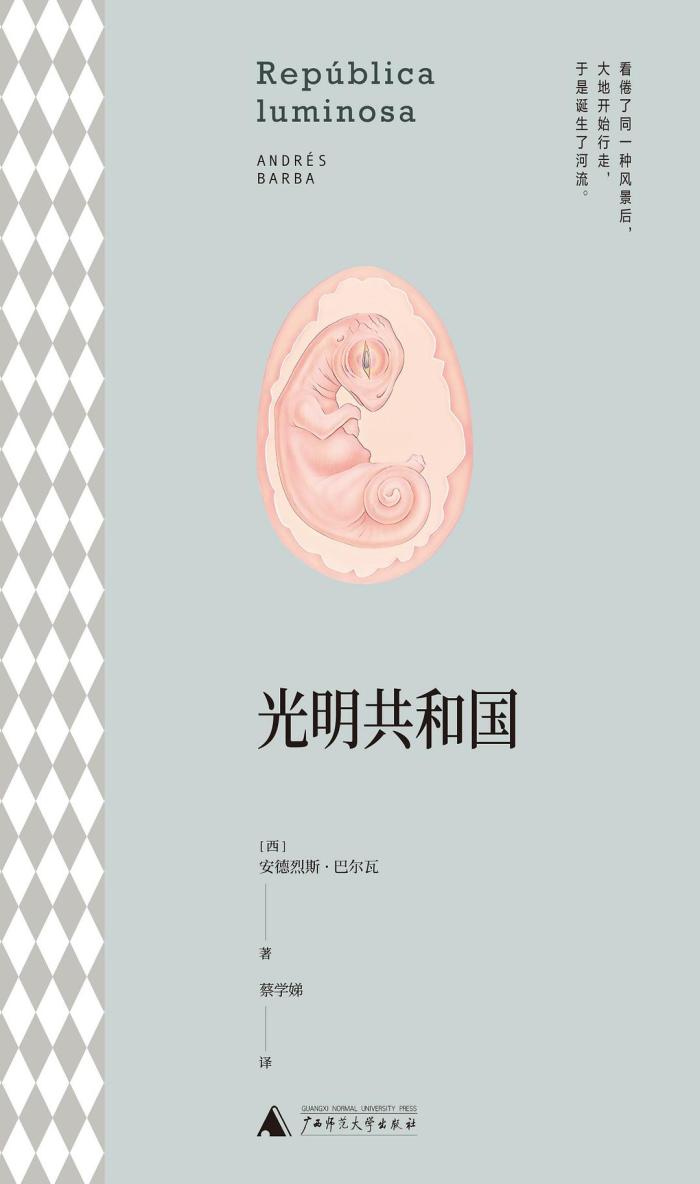
[西] 安德烈斯·巴爾瓦 著 蔡學娣 譯
理想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0-4
界面文化:在《光明共和國》《小手》《消磨》里寫到的童年暴力和創傷元素,是你創作兒童文學時會規避的嗎?還是說,你會將這些元素以某種變形融入到兒童文學寫作中?
巴爾瓦: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認為每個創作者都需要思考一個問題——創作兒童文學的目的是什么?為了娛樂還是為了教化?這兩種目的在某種程度上是此消彼長的,如果將兒童文學純粹視為娛樂,它的教化功能就被削弱了。
這也與另一個問題相關聯:我們應該告訴兒童什么?是否應該幫助他們理解這個世界?我們是為兒童提供工具,使之有能力理解和應對世界,還是讓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和節奏來理解世界?
我想舉個例子,我寫的第一本書講了一個非常簡單的故事:在一個小村莊里,天上的星星突然暗滅了。村里的智者說,其實星星并沒有消失,天空中有一個開關,只要搭起梯子爬到最高處打開開關,就能重新點亮星星。于是眾人把家里的梯子貢獻出來,想共同建造一個長梯。但有一位老人拒絕為集體做貢獻,他說星星亮不亮和自己一點關系也沒有。但后來當一個孩子和他建立了私人的友誼,他就愿意把梯子以個人名義借給這個孩子,如此,村里人實現了集體的愿望。對這位老人來說,個人之間的愛是超越了共同體的愛的。當我把這本書給一位西班牙的兒童文學編輯時,她不認同我撰寫的這個結局,認為共同體的利益應當是高于個人的。這就引發了一個教育理念上的沖突:我們應該教育孩子們重視怎樣的價值觀?是以真理為導向,還是以道德為導向?這樣的沖突在創作兒童文學時是常常會遇到的。
界面文化:西方社會文化給人的印象通常是個人價值優先于集體價值。在這個例子中卻反過來了。
巴爾瓦:是的,這確實很少見。但這個例子很好地展示了在兒童文學創作中,作者的個人信念與想給兒童呈現的“應然”世界之間的沖突。創作者有著自己對現實的看法,但他們認為孩子應該學習的觀念可能與此不同。
英國作家羅爾德·達爾(Roald Dahl,代表作為《查理和巧克力工廠》)影響了我對兒童文學的看法:對兒童文學來說,最重要的應該是讓孩子們感到興奮和愉悅。兒童最重要的驅動力就是快樂,如果閱讀本身不能帶給他們快樂,他們永遠不會主動接觸文學,只會在家長或學校的要求和逼迫中讀書。我想創造一個令人快樂的花園,邀請孩子們過來玩一玩,就是我寫兒童文學的最大原則。
02 游戲于成年人是消遣,于兒童則是一種生命形式
界面文化:小說《小手》取材于真實故事。在新聞報道中這類故事通常會被描述得很恐怖,但你卻書寫了兒童群體內部的隱秘世界,這個世界將游戲中的暴力和真正的暴力區分開了。小女孩瑪麗娜受到了其他女孩的暴力對待,但在她發明的洋娃娃游戲里,是她教大家表達對彼此的愛。“游戲”在這里意味著什么?你認為“游戲”能治愈“暴力”嗎?
巴爾瓦:這個故事源自巴西作家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代表作有《星辰時刻》等)的作品,這是作家的女仆分享的親身經歷。女仆曾在孤兒院生活,她們中的一個女孩死去了,其他女孩把尸體當成洋娃娃“玩耍”了一個禮拜。這個故事讓我印象深刻,初聽時我感到一種復合性的恐懼與驚奇,無法確定這種感受是恐懼還是迷戀。
后來我逐漸意識到,我對這個故事的恐懼正是來源于成人視角,而對它的迷戀則來源于孩子的視角。從成人世界來看,這是一種令人想要規避的野蠻和暴力。但在兒童的世界里,這實際上是一則關于“愛的游戲”的故事。
這個故事里有兩個重要元素。一是“失樂園”,那些女孩生活在一個封閉的孤兒院中,瑪麗娜這個新來的孩子就像是來自新世界的使者,會在孤兒院這個舊世界引發對比、沖突、悲傷,但也會激發新的事件。

[西] 安德烈斯·巴爾瓦 著 童亞星 劉潤秋 譯
理想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0-4
第二是游戲,兒童和成人對游戲的態度是不同的。成人玩游戲通常是為了消遣時間,他們往往也認為兒童的游戲只是“弄著玩兒”。然而,兒童對游戲是非常較真的,這不啻為一種生命形式,他們在游戲中投入了全部的心力,就像我們在生活中體驗生與死,兒童把這些體驗帶到了游戲中,所以在游戲中才會出現殺人或死亡,對他們來說游戲是生死攸關的。因此,游戲在兒童的生活中是極其嚴肅的,這也是為什么我們需要從兒童那里學習游戲的真正意義,重新看待游戲和我們的生命。
界面文化:“失樂園”這個概念非常有趣,它是否根植于《圣經》的宗教文化?在中國文化中,我們幾乎不會把孤兒院與“失樂園”聯系起來。
巴爾瓦:“失樂園”是指《圣經》里亞當和夏娃的伊甸園,一個原本無憂無慮的所在。亞當和夏娃因為偷吃禁果被迫離開天堂的時刻,也是他們意識的開端,完全無憂無慮的生活狀態就此結束,他們開始體驗人間疾苦。對我來說,天堂是一個封閉的、自給自足的圓形結構。在這個“圓”之中,我們無需在自身與他人之間反復比較,也就更為幸福。
我覺得現代人使用社交軟件也是一個不幸福的來源,因為總是會拿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比較,所以它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失樂園”。當一個封閉的“圓”被打開,天堂就結束了。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離開天堂意味著意識的開始和天堂的結束。

界面文化:除了創作小說,你也是一位多產的翻譯者。語言和哲學的學術經歷對你的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比如在《光明共和國》中,32個孩子自創了一種新語言,你寫到,孩子們的出發點似乎“完全是游戲和創造的沖動”,而非“索緒爾關于語言符號具有任意性的理論”,這看起來就好像含有你對自己所學的一種“反叛”和反思。
巴爾瓦:哲學和語言學的學習經歷確實對我的寫作生涯有很深的影響。我的創作幾乎總是“概念先行”的,或者說以概念為導向,而非簡單地構思一個故事。有些作者更關注敘事或情節的發展,而我不論是寫小說還是隨筆,通常都源于一種哲學上的疑問,想要探討一些概念和想法。
例如,我構思《光明共和國》時主要思考的有兩個問題。第一,什么是童真?第二,如何看待社會或集體的共罪及其應負的責任?在這部小說中,政府的追捕使孩子們全部喪命,那么政府應該如何處理這種集體性的罪責,是接受認領這份罪責還是否認它?
拋開這本書的內容來看書名,“光明共和國”本身就是兒童想要創造的一個新世界,也可以說是天堂或烏托邦。在創造天堂時首先需要一種新的語言,所有的烏托邦都需要語言的發明。比如,一對戀人相愛時往往會為對方取一個獨創的小名,在此之前戀人從未被這樣稱呼過,這就是創造新語言的一種體現。我們在創造新的語言和詞匯時,也在以某種方式重新定義現實,現實和語言之間是雙向的互動,這就是小說里這群孩子們通過發明語言來構建新社會的原因。沒有新的語言,就無法創造一個新的社會。
03 每個人都深切地渴望被愛,而兒童獲得愛的渠道閉塞又狹窄
界面文化:我在你的作品中確實發現了許多烏托邦式的概念。例如在《消磨》中,當女孩進入青春期,她對自己的身體變化非常敏感,生活瑣事也越來越令她難以忍受,于是她逃到了公園里。公園可能就是她的一個烏托邦,一個屬于她自己的空間。之后,她又因為拒絕進食被關進了一個治療厭食癥的封閉式診所。
巴爾瓦:我寫這個故事時最關心的就是厭食癥這個現象。從病理學角度來看,厭食癥是一種有害健康的、需要介入治療的疾病。但從哲學角度來看,厭食癥的體驗類似于苦行,是對純凈和神性的追求和對動物性的剔除,例如拒絕進食或者吃素,這些行為都是對世俗世界的否認,厭食癥在某種程度上幾乎可以被視為一種宗教性的審美追求。
因此,這里有幾個重要的概念:首先,什么是正常?厭食一定是一種疾病嗎?那么與之相對,什么才是真正的健康呢?其次,我們是否應該保護那些想要自我毀滅的人?自我毀滅是否也能夠成為人面對生活的一種選擇?
在這個關于厭食癥的故事中,標題“消磨”并不單單指厭食癥對女孩體重與體型的消耗,也指向女孩在家庭和診所中體驗到的愛。女孩通過厭食癥為自己建立了一個自我隔離的堅固結構,診所里結識的朋友給予她愛和陪伴,打破了厭食癥的隔離。但是,無論是家庭里的親情,還是在診所建立的友誼,這些愛的關系總是極其脆弱的,最后都慢慢地消磨掉了。
界面文化:最近有一篇報道講述了一個11歲的中國女孩的故事。她在接受義務制教育時成績不好,父母在學校的勸退下讓她輟學。女孩的父母忙于生意疏于照料她,她被關在家里更加身心孤獨,于是通過互聯網結交到了一群處境相似的朋友,這個小圈子卻又把她帶進被暴力、被性侵和被迫賣淫的深淵。女孩的悲劇是多方面的,缺乏愛和陪伴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巴爾瓦:這是一個悲劇。不論是這個事件里女孩遭遇的暴力,還是其他類似的令人感到恐怖的兒童事件,它的恐怖性就在于兒童獲得愛的現實渠道是如此閉塞和狹窄,以至于愿意通過如此令人絕望的方式得到哪怕是一點點“愛”。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深切地渴望被愛——不是狹義上的男女之愛,而是廣義上的交流和關愛,在所有由人類造成的痛苦中,都深藏著對愛的渴望。因此,我們更應該對這些兒童給予同情和關注,而非不解甚至鄙視。
界面文化:《消磨》是《正當意圖》這組短篇故事中的一篇,《正當意圖》的四則故事《血緣》《消磨》《夜曲》《馬拉松》代表著什么,“正當意圖”這個詞指的是什么?
巴爾瓦:讀者可能會發現,在《正當意圖》的四個故事里,每個主人公都有些病態,各自膠著地處在他們人生中的某一個階段,將自己的全部意志、愿望或愛投諸單一的點。比如說《馬拉松》里男主角就把生活的精力和關注點都放在跑馬拉松上,《消磨》里的女孩也是這樣,她全心全意地用厭食來對抗世界,將厭食作為一個正當意圖來堅守,即便在家人看來她這么做毫無必要。
這樣的形象似乎同時具有愚蠢、執著、神性的特點,就像圣人和愚人也是相似的,他們都把自己的執念置于生活的最中心,一切都圍繞其打轉。所以,我在小說中非常關注事物辨證矛盾的兩端,會書寫事物之間相反又相似的特性——就像厭食癥一樣,它是一種確鑿的疾病,但同時也包含著徹底的解放的一面。
04 疫情讓很多人經歷了幽靈般的生活
界面文化:你在2023年的新作品《前世的最后一天》(El último día de la vida anterior),里講了一個關于“鬼魂”的故事,這和你以往的虛構方式好像不太一樣。能聊聊你構思這個故事的動因嗎?
巴爾瓦:《前世的最后一天》目前還沒有在中文世界出版,這部作品的創作源于一種特別的圖像感受。我寫每本書的動因都不同,有些書源于概念性的構思,比如我寫《光明共和國》是想創作一部政治寓言。《前世的最后一天》的靈感則源于一幅圖像,它也和我寫作的母題有關:在一座房子里,一位女性通過房間內的鏡子看著她自己。我想象她通過房間的鏡子能看到自己前一天所做的事情,她日復一日地進入這座房子去觀看前一天的自己,并為后一天的自己預設前一天的行為“腳本”。我們通常無法從外部看自己,所以,偶爾在錄影中或者鏡子里看到自己時,我們會有一種新奇的、陌生化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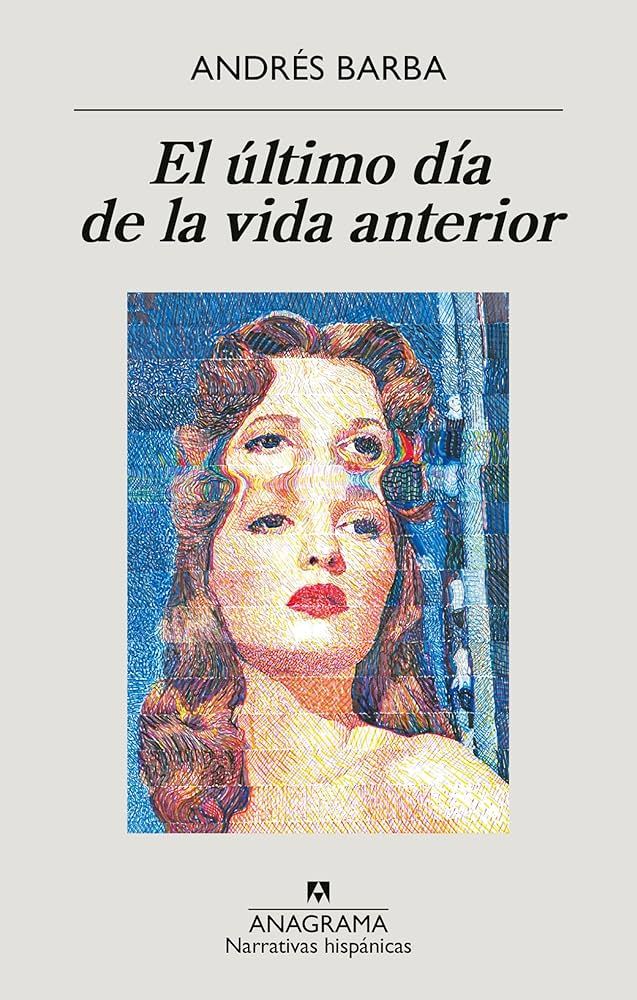
疫情期間,這種感受變得尤為強烈。大家都被困在家中,仿佛成了自己生活的幽靈。我們的真實生活仿佛在外面發生,而我們自己則如同生活在一個虛幻的世界中。看著鏡子中的自己,我們常常無法認出自己是誰,這種隔離的、停滯的、不真實的感覺與書中那位女性的經歷相似。因此,我覺得這幅圖像和疫情期間的共同體驗非常契合,疫情讓很多人都經歷了這種幽靈般的生活。
界面文化:“鬼魂敘事”有著深厚的文學傳統,拉丁美洲文學中不乏類似的講述方式,這和你的寫作是否有內在關聯?
巴爾瓦:一方面,我的創作受到英語文學的影響,英語文學中也不乏鬼魂敘事的傳統。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兩位英語作家是狄更斯和亨利·詹姆斯,尤其是后者。所有寫出偉大的鬼魂故事的作家幾乎都是現實主義作家,現實主義和鬼魂敘事在某種程度上緊密相連。鬼魂故事要講得有效,就必須非常真實,內部必須有很強的現實邏輯性。
另一方面,我確實也受到拉美文學的影響,尤其是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文學,即拉美文學里靠近阿根廷、烏拉圭這一區域的文學,以博爾赫斯為代表人物。博爾赫斯和卡薩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阿根廷記者、小說家、翻譯家)曾編纂過一本幻想文學故事集,幻想文學幾乎成為了拉丁美洲文學的標志。
拉美文學中的鬼魂敘事與英語文學有所不同。如果說英語文學常常嚴格區分鬼魂世界和正常的生活世界,二者之間有一條明顯的分界線,鬼魂被視為現實中的“異物”,那么拉美文學中的鬼魂世界和活人世界是平行的,死者的鬼魂能與生者共存,且被視為現實的自然延伸。這和東方文化對鬼魂的看法也有相似之處,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界面文化:中國文化中確實有著豐富的鬼魂和靈異故事的傳統,鬼魂被視為現實的一部分,有時它與一些災難或困境相關聯,民間相信這些靈異現象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或引發不幸。我們也會從道德的角度來理解鬼魂的存在,比如說你做了背德之事,鬼魂就會扮演懲戒的角色;而如果你做了好事,鬼魂則會保護你。
巴爾瓦:據我所知,中國人是有祖先崇拜的,會相信自己的生命與祖先的靈魂在某種程度上相互聯系,因此鬼魂具有如神明一般的保護性力量。在西方不太一樣,鬼魂常常被看作是一種威脅的、有敵意的存在。在拉丁美洲的文學傳統中,鬼魂和現實世界邊界更模糊。一個最顯著的例子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這本書可以說是20世紀西班牙語文學中最杰出的鬼魂小說之一。書中生者和死者的界線完全模糊,讀者讀完后也無法分辨誰是活人、誰是死人,這種模糊性正是小說的魅力所在。

[墨西哥] 胡安·魯爾福 著 屠孟超 譯
譯林出版社 2021-1
你提到中國文化里鬼魂的預言和道德規訓作用,西方也是如此。一個常見的敘事動機是某人由于生前未能解決某件事情,與現實世界的聯系并未完全斬斷,因此鬼魂處于兩個世界之間的“半生半死”狀態,需要通過和活人之間形成互助的契約或承諾來完成未竟之事,以便完全進入死亡的世界。因此,西方的鬼故事往往也是道德寓言。
界面文化:今年你獲得了阿根廷國籍,是什么讓你決定申請阿根廷的公民身份?我們知道阿根廷和西班牙之間有深厚的歷史淵源,你如何看待這兩個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呢?
巴爾瓦:15年前我就和一位阿根廷女子結為夫妻,這10多年里,我都不在西班牙而是在阿根廷生活,我的孩子也出生在阿根廷。擁有西班牙和阿根廷的雙重國籍并非意味著對西班牙國籍的否認,反而公民身份的轉換讓我產生了一種近似解脫、或者說拓寬和延展的感受。
我和阿根廷的關系,不僅僅是與我的妻兒的私人關聯,更是與阿根廷所在的整個拉丁美洲的聯系。我對拉美文化是如此熟悉,它仿佛已成為我身體的一部分。同時,我感到自己像是擺脫了對身為“西班牙人”的認同,也跳脫出了一種流行的、過于狹隘的民族主義視角。過于狹隘的民族主義是一個病癥,因為它往往伴隨著對其他文化的貶低。如果我們不去拓寬自己的視野,主動了解其他國度的文化,也無法成為真正健康的民族主義者。因此,從狹隘的民族主義中解放出來,對我來說也是一種自我療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