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林子人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上個周末,第三次作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參與美國大選的唐納德·特朗普遭遇了他人生中最驚險的一幕。當地時間2024年7月13日下午6時左右,特朗普在賓夕法尼亞州巴特勒市的選舉集會上發表演講約10分鐘后,現場突然響起數聲槍聲,特朗普的右耳被子彈擊中的提詞器玻璃碎片所傷,鮮血迸出。一名現場觀眾死亡,另有二人受傷。槍手被當場擊斃,其身份被確認為20歲的賓夕法尼亞州貝塞爾帕克市男子托馬斯·馬修·克魯克斯(Thomas Matthew Crooks)。
飄揚的美國國旗下,特朗普在特勤人員的簇擁中舉起右拳高喊“戰斗”(fight)的照片迅速登上全球各大媒體新聞頭條,并在社交媒體廣泛流傳,這一爆炸性事件將對今年年底的美國大選產生何種影響也引發了種種猜測。
7月14日下午,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記者采訪了政治學者林垚,從這一突發事件入手,討論了2016年特朗普首次入住白宮以來美國政治版圖的變化、美國社會政治分裂的原因,和歐美各國可能存在的政治僵局。
林垚為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耶魯大學職業法律博士,現為上海紐約大學教師。他曾與友人共同主辦“選·美”項目,力圖為中文公共場域提供關于美國政治的準確信息與深度評論。在他最近出版的文集《空談》中,中卷《攪夢頻勞西海月》匯集修訂了近年來他在媒體或其他公共平臺上發表過的闡述美國政治的相關文章。
從這些文章中我們不難發現,美國當下的兩黨格局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特朗普的卷土重來亦需要被放在這一歷史背景中去理解:民主黨在1960年代民權運動中與南方白人決裂,共和黨則憑借1968年大選中尼克松的“南方戰略”和1980年代初“里根革命”發現了動員保守派選民的高效手段。在那之后,共和黨的影響滲透到了美國政治的方方面面,從選舉制度到最高法院,都越來越有利于推動共和黨的政治議程。與此同時,美國的選舉制度讓兩黨體系日益成為無法撼動的“超穩定結構”,剝奪了兩黨溫和派候選人脫穎而出的渠道和政治改革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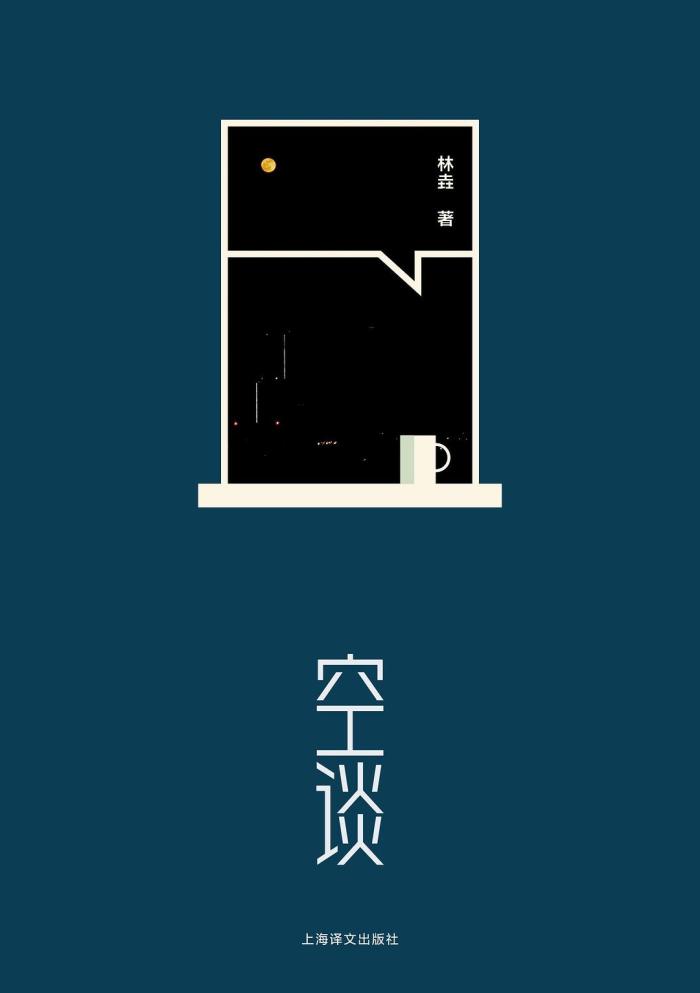
林垚 著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4-6
林垚在采訪中強調,民主黨內部分裂、共和黨日益極端化的現狀其實已持續多年,這與美國的政治制度設計有隱秘關系。他認為,2016年以來美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反思美國政治分裂時提出的各種解釋——包括身份政治令左翼遠離了公民政治、經濟不平等和“精英的傲慢”讓普通美國人轉向反對自由主義價值觀——都未能抓住問題的本質,即美國的政治制度已出現難以修補的裂痕。
01 距離正式投票還有三個半月,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
界面文化:看到特朗普遇襲的突發新聞時,你的第一反應是什么?
林垚:第一反應是又震驚又不奇怪。上個月拜登在電視辯論中表現得很糟糕,很多人來問我的看法。我說不著急,還有4個月時間,現在美國政治那么“狂野”,總會有一些小概率事件發生。當然我也沒想到有人會在集會上開槍。
界面文化: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特朗普要贏了。”
林垚:現在離投票即正式大選開始還有三個半月,如果是投票前一天發生刺殺,我覺得(特朗普勝出)是一定的,但還有三個半月,還有很多事可能會發生。新聞周期過去之后,或者兇手身份被披露后,或者這一事件的熱度被其他事件掩蓋后,(特朗普遇襲)未必是一件大事。我比較排斥陰謀論,不覺得這件事是共和黨安排的,但如果兇手被發現是一個共和黨選民,共和黨就很難拿這件事去指責民主黨(注:報道顯示,克魯克斯的黨派信息登記為共和黨,或曾向民主黨相關組織捐款)。

界面文化:電視辯論之后,民主黨就在討論推舉另外一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可能性。疊加這一突發事件的影響,你認為拜登有可能退選嗎?
林垚:我覺得很難。首先,雖然拜登如果主動選擇退出的話確實是可以退選的,但拜登自認為他在過去四年的政績還不錯,也已經順利走完了初選程序。拜登本身就不是一個善于辯論的人,只是因為在一次電視辯論上口齒不清就被要求退選,他很難接受。
其次,更現實的考慮是民主黨內一時推不出一個大家認為有希望贏過特朗普的人選。2020年拜登宣布參選時曾表示自己只會做一任總統,他的潛臺詞是,我參選是為了擊敗特朗普,然后就可以放心交棒了。大家當時沒有想到特朗普四年之后會再次參加選舉,而在此期間,民主黨中沒有出現一位被推上美國舞臺被選民看到的年輕人。
按照現行選舉法律規定,如果拜登退選,因為目前的民主黨競選團隊是拜登-哈里斯競選團隊,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Davi Harris)就會成為順位繼承人。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黨內很多人不太信任她。賀錦麗是一位黑人女性,他們擔心美國的中間選民有強烈的種族偏見和/或性別偏見。如果在拜登退選后要求賀錦麗一并退選,也不好意思說出口,所以就變成了一個很尷尬的局面。
02 選舉制度影響下,民主黨內部分裂嚴重共和黨日益極端化
界面文化:從2016年至今,美國政治給我們的一個強烈印象是左翼(民主黨)在右翼(共和黨)的長期布局下節節敗退。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林垚:后民權運動時代的民主黨是幾個選民聯盟的大拼盤:黑人、拉丁裔、亞裔等少數族裔;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精英;住在郊區的白人中產。中產選民的選票是有點搖擺的,他們希望像共和黨呼吁的那樣給富人減稅,但他們又可能看不慣共和黨的文化保守主義。這些郊區白人中產選民有多少會走向民主黨、多少會走向共和黨,很多時候取決于候選人制造的觀感。
藍領工人階層的選票大部分還在民主黨這邊,但過去十幾二十年里在逐漸流失,這和工會的衰落有關。民主黨希望能把這部分選票拉回來,那就需要推出再分配、工業復興等經濟政策,而黨內對這些方面的政策側重點是有分歧的。
還有過去一年以來的巴以沖突爭議:受過高等教育的民主黨年輕選民認為巴以問題很重要,巴勒斯坦在遭受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美國應該盡早與以色列政府切割;但很多溫和派選民認為巴以問題沒有那么重要,或者認為以色列是中東地區少數的民主國家之一,不應給以色列政府施加太大壓力。

所以我們看到,民主黨在過去十幾二十年里形成了大致勢均力敵的兩大派別,一派更溫和,一派更激進。這就會造成一個問題,即任何一派推出的候選人都難以服眾。新人沒有與選民發展出長期的基層互動關系,無法靠與選民建立的個人信任拉住一部分忠誠選民,只能靠意識形態來聚攏與自己意識形態相近的人,那么就很容易丟失另外一部分選票。
于是,民主黨只能采取一種縫縫補補的策略:像拜登這樣的老人,雖然年輕人可能看他不順眼,但他至少在黨內耕耘了幾十年,黨內的建制派會為他背書,在拉選票的關鍵時刻會放下成見,呼吁自己的年輕選民基本盤去投拜登。這種情況下,老人就成為了一種黏合劑,爭取把黨內新一代政治家之間越來越大的鴻溝黏合在一起。世代交替的過程肯定要在某個時刻完成,老一輩總會退下政治舞臺,年輕一代在什么節點上會出現在美國舞臺上?如何重新整合民主黨?這是民主黨在過去十幾二十年一直面臨但沒有完全解決的重大問題。
界面文化:如果這是民主黨過去十幾二十年未能解決的重大問題,那奧巴馬難道不是一個很大的例外嗎?
林垚:奧巴馬是一個例外。時任總統小布什在2004年連任成功的時候,美軍在伊拉克戰場上勢如破竹,他當時還很得意地打出了一個橫幅,“Mission Accomplished”(任務完成)。但伊拉克的局勢在2006-2007年急轉直下,美國當時支持的馬利基政府腐敗無能,無法在伊拉克內部彌合種族分歧,很多人開始對伊拉克戰爭產生懷疑。2008年又恰逢金融危機,很多美國人失業,所以在2008年大選的時候,小布什“天怒人怨”,當時很多人覺得不管是誰出來都能贏。
奧巴馬參選也是希望乘這個東風,他得到了民主黨內大佬泰德·肯尼迪(Edward Moore Kennedy)的支持。奧巴馬當時沒有政治包袱,形象比較清新,作為一個黑人,他還能代表美國的歷史性突破。當時確實有很多傳統上的共和黨選民投了奧巴馬的票,但事后來看,我覺得這更像是為了證明“我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接下來他們反對奧巴馬的政策,就不能說他們是種族主義了。很快我們就看到,僅僅兩年的時間里,共和黨中的極端群體茶黨(Tea Party)崛起,特朗普現象其實可以追溯到茶黨。它本質上就是對奧巴馬作為黑人當選美國總統的一個反彈。

界面文化:這是特朗普第三次作為共和黨候選人參加美國總統大選。根據你的觀察,從2016年至今美國的政治版圖發生了哪些變化?
林垚:我在《空談》中寫過,2016年共和黨內同時存在兩個現象,特朗普現象和克魯茲現象。當時支持泰德·克魯茲(Ted Cruz)的選民認為特朗普不夠虔誠、不夠保守,不符合宗教保守派的心意。但特朗普勝選之后,共和黨內經過了一輪又一輪的清洗整合,共和黨選民也完成了認知失調的調整過程。2020年美國大選時我在美國,看到有一戶人家在院子草坪上插了一個牌子,上面寫道,“上帝向特朗普低下了頭,說你比我還偉大。”
在過去幾年里,共和黨的黨務機器也積累了大量特朗普的擁躉。今年3月,特朗普的兒媳拉拉·特朗普(Lara Trump)出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聯合主席,她就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測試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全體工作人員對特朗普的忠誠度,不夠忠誠的人就地開除。所以現在共和黨黨內沒有任何膽敢挑戰特朗普的聲音,黨內的政治新星想往上爬,就需要努力模仿特朗普,發表更出格、更極端的言論。
比如有可能成為特朗普副總統搭檔的J.D.萬斯(注:當地時間7月15日,美國共和黨正式提名他為該黨副總統候選人)。他在特朗普遇襲事件當天立刻發推,說特朗普遇襲的推動者是拜登和民主黨,我們必須予以反擊。這還不算他近年說過的最出格的話。萬斯多年前出版紀實作品《鄉下人的悲歌》時,與如今的他判若兩人;當時他還是共和黨內的反川派,曾經說特朗普是“美國的希特勒”。但后來他想要從政時,發現只有拼命討好特朗普才能上位,于是馬上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成了特朗普最積極的輿論打手和陰謀論傳播者之一。此外萬斯近來還說過很多“女人即使被家暴也不該離婚,不然就破壞了傳統家庭價值觀”之類的話,以討好黨內的宗教保守派。目前共和黨內有望攀爬政治階梯的人都非常極端化,不僅在意識形態上,而是從言論到散播陰謀論等等全盤的極端化。

民主黨這邊分裂的狀況還在持續。可能除了俄烏沖突,民主黨內部在其他許多問題上(從經濟政策到巴以沖突)分歧都非常大,而且這種分歧是一時難以解決的。
這種情況其實與美國的政治制度設計有隱秘關系。我們知道美國總統選舉實行選舉人團制度(Electoral College),參議院席位為每個州兩個,眾議院是根據各州的人口比例來分配名額選出的。眾議院和地方議會的選舉按照選區去劃分。這樣的制度安排意味著地理因素或人口密度因素會隱秘地扭曲整個政治選舉結果的框架。按照州來劃分的話,人口密度更小的州相對而言政治話語權更大。因為一個擁有很多大城市、人口密集的州,在參議院里也只有兩人,在選舉人團里,即使按照普選選票高出另外一個小州很多倍,換算成選舉人團的票數,其實權重就下降了。同樣一個州里,大城市相比于農村地帶,話語權也比它原本該有的更小。
如果美國現在不考慮選區劃分,直接進行全國普選,其實這幾年民主黨總是會高出共和黨幾百萬到上千萬票。但這個優勢通過隱性的制度安排被沖淡了,陷入了僵局,即共和黨即使極端化依然有足夠的概率拉住一些保守派選民,沖頂總統,在參議院和眾議院站穩腳跟,但民主黨沒有辦法往另外一個極端走。在某些選區當然有一些議員會被選民拉著往更激進的方向走,但民主黨內很大一部分選民是停留在中間位置的,就會造成黨內越來越明顯的內部分裂。
03 身份政治和經濟不平等都不足以解釋美國的政治分裂
界面文化: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在《道德政治》(Moral Politics)中提出,進步派的問題是不像保守派那樣敏銳地認識到“道德話語”在政治中的分量,未能有效地向公眾傳達自己的黨派道德政治觀念和黨派道德政治語言。你是怎么看萊考夫的觀點?
林垚:我對這類理論是比較懷疑的。萊考夫提出道德政治理論有很強的時代背景:里根主義興起以后,可以明顯看到共和黨內宗教保守主義情緒的崛起,但其實共和黨有另外一股強大的支持勢力,就是小政府主義者,他們主張減稅、去監管,當時共和黨的策略是利用宗教保守主義選民的選票推動小政府主義的政策。而這也為二三十年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受時代的局限,萊考夫的理論我覺得存在兩大根本問題。

首先,他對政治話語的勾勒本身是有偏差的。在道德政治的框架下,共和黨對國家的理解被描述成“嚴父”模式:國家管好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鼓勵人們過清教徒式的生活。但其實我們也要看到共和黨的財政保守主義傾向——他們恰恰把國家想象成一個甩手掌柜,希望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所以萊考夫對共和黨那邊的描述我覺得本身是有問題的。
對民主黨那邊的描述也有問題。民主黨對國家的理解被描述成“關愛”模式:要投入建設社會福利,保障大家過得上好日子。但其實對很多民主黨人來說,把重點放在國家上本身就錯了。萊考夫的框架預設了兩邊的政治話語從根本上來說都是關于國家應該扮演什么角色的,但其實很多民主黨政客和選民思考的是社會中人與人應該發展出怎樣的關系——因為人與人之間要相互關愛,我們不能讓一部分人受苦,那我們就要利用“國家”這個工具來調配我們的財富。國家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父母”的角色,而是一個工具。
其次,把政治話語抬到如此高的地位,好像在說,“只要把話講對了,傳達出正確的信息,就可以贏得選民。”這有點太小看了其他的制度安排和社會文化中的其他因素。比如“媒體掌握在誰的手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媒體是更加多元的,如果媒體構成了一個公共場域,人們都愿意閱讀了解不同觀點的媒體,而不是陷入信息繭房,只了解經過特定媒體過濾后的信息,效果肯定是不一樣的。
還有我剛才說的,選舉制度安排增加了某一部分人的投票權重,這樣的話就算你多說服了幾百萬人,也不會達到想要的投票結果。這些其實是我覺得更關鍵的問題,在這個基礎之上,可以再去討論道德話語如何呈現的問題。
界面文化:2016年至今,美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對社會分裂也有諸多反思:馬克·里拉和弗朗西斯·福山批評自由派沉迷于身份政治,遠離了公民政治;阿莉·霍赫希爾德和邁克爾·桑德爾認為,經濟不平等加劇造成的挫折感和“精英的傲慢”,讓許多普通美國人轉向反對左翼倡導的平等、自由和多元包容。你認同他們的觀點嗎?
林垚:你提到了兩派,一派是文化派,就是對身份政治、取消文化的批評;另一派是經濟派,就是探討經濟不平等對美國政治的影響。我自己可能更偏向制度派,我會覺得這些問題都是表象,內里是制度出問題了,而且這些問題不是最近才出現的。以前運氣好或經濟形勢好,制度的漏洞沒有被發現;也有可能是過去幾十年里通過了某些當時看起來不起眼的法律,累積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漏洞。回到上述兩派的觀點,我認為文化派的觀點是不成立的,經濟派的觀點部分成立,但沒有抓到真正的痛點。
身份政治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制度層面難以改變,左派就試圖通過重新復興社會文化層面對一些問題的關注,讓這些意識覺醒之后能夠反哺到制度修補上。我在書中提到,美國高校錄取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受到批評,保守派認為照顧少數族裔的結果就是對其他人不公平。我個人也認為平權法案不能解決真正的問題,但它為什么不能解決呢?其實有更多深層面的制度安排導致了種族之間的經濟不平等、就業機會不平等在大范圍地持續發生。小學、中學不同校區之間的居住隔離、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經濟資源分配不公被地方層面、州層面和聯邦層面的各種制度給固定下來,導致了少數族裔占多數的社區中,孩子從幼兒園開始一直缺乏教育機會的支持,等到大學階段,這個差距就會顯現出來。因為地方政府、州政府的種種法律制約,改革地方上的校區制度非常困難,最后導致關心教育公平問題的人在目前的條件下只能盡可能小修小補,比如在高校錄取的時候采取修正的補救政策。但這不能解決真正的問題,病灶依然存在。如果認為高校的平權運動導致了這些問題,就是本末倒置了。文化派沒有看到制度層面更根本的矛盾所在。

至于經濟派,過去幾十年來,全球化帶來的物流鏈變化、就業機會的外包等等確實導致美國出現了所謂的銹帶地區,這是一個真問題。它也確實引起了很多人對民主黨經濟政策的反感,但這里面也同時存在一些吊詭的現象。第一,銹帶地區很多我們認為因為就業機會轉移受影響的人仍然是民主黨的選民——比如大型鋼鐵廠或汽車制造廠的工人,他們當中很大一部分人仍然住在原來的鋼鐵廠或汽車制造廠附近,仍然同以前的工會人士有關聯,其實會繼續投民主黨。但生活在附近城鎮或鄉村地帶的很多選民,他們可能自己不直接受到就業外包的影響,但他們看到了產業的凋敝,因此產生了一套敘事,認為民主黨的政策打擊了當地經濟。所以我們看到,2016年特朗普在鐵銹帶的得票率確實上升了,但如果分析具體是鐵銹帶哪些人、出于何種原因投給了特朗普而非希拉里,這里面的因果鏈條可能會比經濟派的人所呈現的要復雜得多。
這里也涉及到選民接觸到了哪些媒體、媒體如何呈現的問題:到底是誰的政策、什么原因導致了經濟形勢的變化?經濟形勢的變化多大程度上影響到了我、影響到了美國的國運?我到底應該怪罪誰?美國大企業的藍領工人就業機會的喪失、工資福利的下降,除了是全球化造成的結果之外,還有一個很大原因是1980年代里根上臺以后在不斷打壓工會。但在講述美國普通工薪階層的故事時,共和黨打壓工會的這段歷史就被遺忘了,沒有呈現在敘事里。所以我們看到,媒體在敘事呈現上發揮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
經濟形勢的變化能解釋一部分事情,但我們同樣也需要看到背后制度的變化:一些州是不是推出了削弱工會的法案?一些州議會是不是在某些條件下倉促迎來了外地大企業的進入?這些大企業進入后是否增加了地方的就業機會?為了拉攏外地大企業進駐,地方政府是否承諾了太多東西,比如給予稅收優惠,反而損害了當地經濟?這就需要我們去看到具體社區、具體的地方政治。
界面文化:這些年還有許多人提出美國大選的民調在失效。
林垚:對,這是從2016年大選開始的,當時很多民調人士覺得希拉里會贏。回顧來看,民調不準有兩個原因:第一,2016年時很多特朗普的選民不好意思公開表明支持特朗普——其實在支持一個你自己覺得不一定會贏的人的時候,你是不好意思說出來的——或者其中一些人不信任主流媒體,拒絕參與民調。第二,美國選舉制度的設計導致兩邊的候選人在支持度接近的情況下,不確定性過高,最后大選結果就是由那么幾個搖擺州決定的,哪怕某個搖擺州里相差幾萬票,也能決定結果。
現在的話,共和黨選民特別是MAGA選民(注:“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支持者、特朗普的鐵票倉)已沒有什么思想包袱。其實在2020年大選時,因為2016年的挫敗,很多民調人士重新調整了權重,增加了特朗普選民的話語權。當年很多民調認為特朗普會贏,但是他輸了,于是民調又不準了。這意味著今年的民調又要把特朗普選民的權重再調低嗎?

界面文化:紐約時報/錫耶納學院的最新民調中有一個有趣的細節:電視辯論后,更多男性轉向支持特朗普,特朗普的男性支持率增幅幾乎達兩倍,以23%的優勢高于女性支持率。你在《空談》中寫到,2016年特朗普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雖以本土主義為核心訴求,卻能獲得兩大黨之一提名的總統候選人”。根據《紐約時報》的分析,大男子氣概(machismo)是特朗普這一次的宣傳策略,而從最新民調來看這個策略確實有效。近年來男性保守化、女性自由化的趨勢似乎是一個全球性現象。今年1月,《金融時報》看法的一篇報道就認為,全球性的性別分化正在出現,全球各地的Z時代都在性別極化。你認為性別會是今后影響美國政治的一個重要變量嗎?
林垚:我覺得應該是會的,其實這個趨勢在過去幾次選舉中大概能看到。我個人對全球年輕人中同步發生的性別分化有點困惑,不同國家的具體差異還挺大的,比如說韓國要求男性服兵役,我能夠理解為什么很多韓國男性會在軍隊內部的有毒的男性氣質訓練下改變,而且很多韓國男性會覺得(強制服兵役)不公平。歐洲相對來說變化的幅度沒那么大,美國的情況是,過去幾年里發生了墮胎法案被推翻等重大事件,很多年輕女性會感受到切身影響。
另一點是在社交媒體時代,一個國家內部的意識形態思潮很容易在全球其他角落形成聯動,比如“非自愿單身”(incel)的概念一旦產生、形成社群,可能很快就從美國或其他某個國家擴散到世界的其他角落,因為很容易能夠在網絡上找到同好。從這個角度來說,全球同步的性別分化也是可以解釋的,只不過它在美國具體會影響到什么地步,可能還要等這次大選的結果來驗證。
04 目前無人能提出新自由主義政經結構的破局之道
界面文化:如果這次特朗普又成功當選美國總統,接下來美國的國內和國際政策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林垚:國際方面,特朗普當選之后,美國估計會撤回對烏克蘭的支持,烏克蘭就很難在俄烏沖突中撐下去。美國國內方面,最近媒體曝光了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等特朗普支持者在策劃“2025計劃”(Project 2025)。從各方面報道來看,雖然特朗普出面否認了他與“2025計劃”的關系,但這個計劃確實存在,特朗普在一些集會上公開支持“2025計劃”。且不論這個計劃的組織性強到多大程度,它背后反映的這些極右理念是存在的,而且極右分子試圖在貫徹下去。
特朗普雖然很有煽動力,但在治國上他是一個比較無能的總統。在他就任總統期間,想要利用特朗普當選的機會把極右翼治國理念貫徹下去的那些人,也處于在官僚機構中摸索的過程中,因為他們以前都沒有在政府中身居高位的經歷。所以可能對很多美國人來說萬幸的是,特朗普基本上浪費了四年,但如果他重新當選,他手下的那些人應該已經準備好,不會再浪費四年時間了,可以更有效地去執行他們的計劃,包括如何進一步地控制美國的司法體系。
前幾日美國最高法院作出關于總統免于刑事起訴的一個判決,這個判決非常古怪(注:當地時間7月1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數結果裁定,特朗普可以因其總統任期即將結束時采取的一些行動而獲得刑事起訴豁免權,但無權因以私人身份采取的行動而免于起訴)。2021年1月6日沖擊國會事件前后,特朗普曾向副總統彭斯施壓,要求他拒絕認證支持拜登的選舉人票,轉而認證偽造的選舉人票。他還與司法部長討論是否有辦法廢除支持拜登的選票。高院認為,總統與副總統、司法部長商議問題,是總統的分內之事,所以是默認免責的,高院就把這個案件發回下級法院,要求其評估特朗普的哪些行為可以獲得刑事起訴豁免權。

高院的保守派大法官還表示,雖然允許通過證據來證明總統的行為無法免責,但任何與總統的核心官方職能有關的內容都不能拿來作為證據。比如說假設特朗普明確向司法部長下令燒掉支持拜登的選票,我們不能用特朗普與司法部長之間的談話錄音來證明他有罪,因為“與司法部長談話”這件事情本身屬于總統的官方職能。如果尼克松還在世他應該會很高興——當年“水門事件”,高院要求尼克松必須交出錄音帶,然后尼克松就辭職了。如果回到那個時代,尼克松就可以說這是我的核心職能,別人偷錄我說的話不能拿來作為證據。
從全球來看,共有30多個國家給予政府首腦豁免權,其中絕大多數不是民主國家。民主國家中,愛爾蘭、法國等國給予了總統豁免權,但由于政治文化的差異,很少有其他民主國家像美國這樣同時給予總統那么強的赦免權(美國總統可以隨意赦免任何人的聯邦罪),所以形不成一個閉環,總統不容易胡作非為。但如今在美國,假如高院開了(豁免權的)先例,再加上已有的其他制度安排,很難保證未來的總統不會作惡、赦免底下為其辦事的人,以此形成一個完美閉環。
界面文化:到現在這個時間節點,我們可以說美國的政治體制已經不再有自愈功能了嗎?
林垚:事在人為,但總體上的確非常困難。因為就在于美國修憲的門檻太高了,需要兩院的2/3再加上3/4的州支持,這個門檻目前基本是不可達到的。因為前面所說的制度因素,雖然民主黨比共和黨有更龐大的選民基礎,但在國會里基本就是勢均力敵,很難獲得一個絕對多數的票數去修憲,更不用說那些保守州都掌握在共和黨手里,基本上不可能通過3/4的州門檻來批準修憲的動議。所以在根本層面上完成對美國政治體制的大刀闊斧的改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小的修補能不能做到?我覺得不是沒有可能,但目前的情況來看很難。目前美國人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爭取時間,一輪輪的選舉熬下去,等待世代交替之后出現一種新的契機。
界面文化:歐洲極端右翼崛起已不是新鮮事,但近期英國和法國的政局變化格外值得注意:英國保守黨遭遇慘敗,基爾·斯塔默出任英國14年來首位工黨首相;法國國民議會選舉中,左翼聯盟新人民陣線成為第一大政治聯盟,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則遭遇失利,屈居議會第三大黨。英法兩國的政治變化是否具有什么風向標意義呢?
林垚:英法兩國的這次選舉根本上來說都顯示了選民對執政集團的失望,但選民對未來有一個總體上清晰的方向嗎?其實可能也沒有。法國勉強保住了原來的政治格局,英國看起來向左擺了一點點,歐洲的一些其他國家在右轉,但這些都沒有太多的風向標意義,更多好像是選民在表達一種不滿、一種迷茫。
全球可能正在面臨一個重大的轉變關口:全球化幾十年后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新自由主義占主導地位的政經結構發展幾十年后,人們覺得問題已經積累得太多了,想要變化。但往哪里變?現在沒有人能夠給出一個服眾的答案。對選民來說他們也很困惑,所以只能今天投這個、明天投那個。
我不知道在可預見的未來會不會像百年前那樣再出現一次全球性的大蕭條,帶來政經政策上的范式變化,更糟糕的一種情況是,各個地區輪流發生經濟蕭條,但這個沖擊又沒有強烈到所有人都意識到必須或者同步做出變化。
同時還有全球氣候變化的問題。表面上來看它跟經濟關系不大,但氣候變化會影響到農業產出的不穩定、突發高溫、洪水等氣候災難,這些黑天鵝事件越來越多,后果都會反映到政治上。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改革越來越迫切,另一方面政府拿不出足夠的資源、意愿和能力去改革,因為光是應對突發災難就已疲于奔命。我可能比較悲觀,覺得我們大概率面臨的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