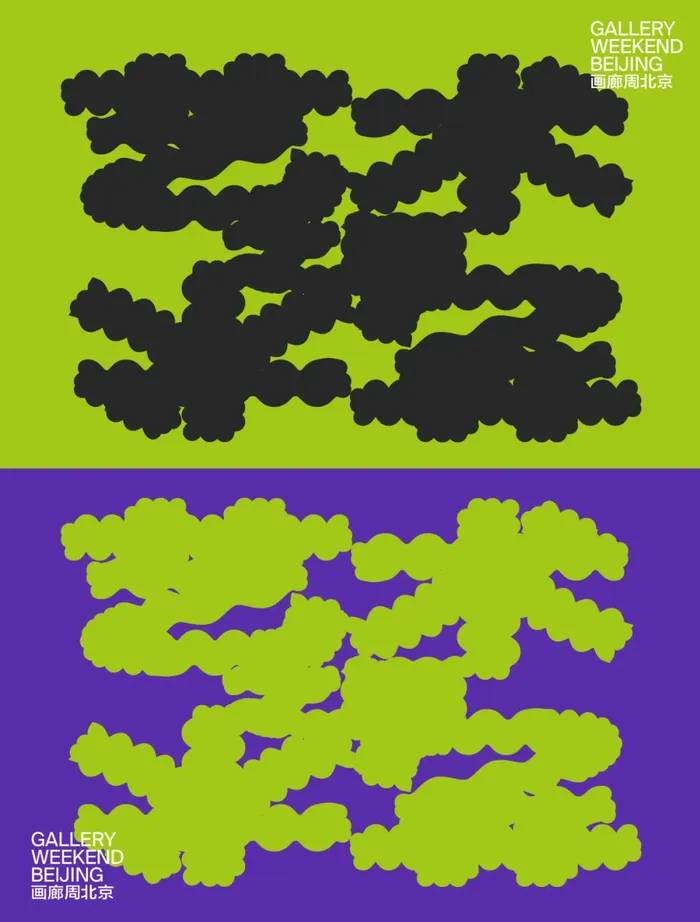界面新聞記者 | 尹清露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2024年第八屆畫廊周北京目前正在舉辦。在5月24日至6月2日為期十日的時間里,畫廊周聯合眾多國內外畫廊與非營利機構帶來諸多藝術活動。與往屆不同的地方在于,在疫情后國際交流恢復、全球氛圍卻愈發極化的今天,如何在離散中自處這一議題變得緊迫。今年畫廊周的主題“漂留”正呼應了這一點,它意指藝術家的出走與回歸,探討本土視角與多元經驗如何相互交融。
圍繞“漂留”的概念,今年畫廊周的新勢力單元推出了30位/組藝術家的群展,并以“風的內側”作為主題,該單元展覽持續至6月24日。這一主題來自于塞爾維亞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Mirolad Pavi?)在1991年發表的同名小說,并由策展人袁佳維再度詮釋,以回應中國當代藝術的諸多問題。

袁佳維告訴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風的內側指的是“風從雨中吹過時沒有淋濕的那一面”,風的外側則是指藝術家在創作時受到的客觀條件限制,比如藝術家位于中國的內部空間或離散在海外,宏大的地緣與身份政治等位置決定了創作的基本線索。在風的內側,藝術家仍然能主觀地為自己的作品設定具體而微觀的時空。“風的內側這句話是非常浪漫的,它能夠描述中國藝術家——尤其是生活在中國大陸的藝術家——在近幾年逆全球化的過程中,如何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再結合身份去思考自己的創作。”
在觀展過程中,界面文化對袁佳維以及三位參展藝術家進行了采訪,他們分別是劉雨佳、陳維與夏喬伊。雖然藝術家們的年齡代際(前兩位是80后,后一位是90后)以及創作方法各有不同,他們的擔憂與關注的議題卻都有共通之處。畢竟,我們都必須承受“風的外側”的重力,一起面對同樣的問題。

睡袋、背包與和田玉:在地質時間中探尋自我身份

走進展廳,首先看到的是夏喬伊的裝置作品《睡眠模塊:可變成背包的探險家睡墊,雙人尺寸》(2024),它由真絲、柞蠶絲、陶瓷等材料制成,既是一個雙人睡袋,又可以卷起來用作背包。豐富的材料意味著文化的交流,夏喬伊從去年開始沿著絲綢之路旅行,從蘭州一路跑到喀什。他希望通過古代的國際化交流以及留下的遺跡,為當下提供一個參照方向。
與此同時,睡袋和背包暗示著人類目前的生存危機。“睡墊和背包都是一種游牧式的生存裝備,在現在中亞的侵略戰爭中,士兵們需要類似的裝備;對普通人來說,我們流行的露營、徒步也需要背包去接觸自然。”這也對應著作品上的不同材料,既有用作防彈衣和軍裝的堅硬布料,又有來自杭州的絲綢,以及來自昆侖山的玉石,它們統統被編織在一起,意味著地質時間、空間的重合和跨越。

圖片來源:畫廊周北京
對夏喬伊來說,“背包”與“編織”的意義遠不止于此,它也融匯了女性主義對于重構世界的反思。他引用科幻小說家厄休拉·勒古恩的“背帶理論”指出,人類的知識經驗會慢慢編織成一張網,網必然存在漏洞,但漏洞也是一種可能性。這個理論批判了男性殖民暴力的歷史建構,也即那種“拿起一根骨頭砸死對方”的歷史觀。與此相反,在通常被認為更女性化的采集時代,人類一周只要工作15個小時,并帶著背包四處采集作物。夏喬伊提到:“無論是背包、睡袋還是帳篷,它們都是身體的延伸,幫助你走到更遠的地方進行交流和探險,并且是用和平的方式,所以這也是一種消除極端地域主義的方法。”
編織與縫合也是夏喬伊一以貫之的創作方式。他出生于一個從事紡織業的家庭,兒時經常看媽媽踩縫紉機。他原本討厭縫紉,卻逐漸認識到這是構成他的身份的重要部分。除此之外,也是由于“如今的圖像太泛濫了”。夏喬伊說,他現在很懷疑生產圖像的必要性,認為繪畫變成了一種為了藝術而制造圖像的行為。他還提到,編織曾經是與繪畫相比更下等的藝術,僅僅是重復平面繪畫的邏輯,然而看包豪斯時期的女性編織藝術家就會知道,編織與建筑更接近,它是一層層的累積,有十分理性的一面,這超越了男性劃定的所謂藝術范疇。
袁佳維認為,當年輕藝術家要定位自己的身份,需要考慮地質時間與文化間性,所以夏喬伊會走出去,做類似于挖掘考古現場的工作。同樣關注地質時間的是劉雨佳,她拍了一部名為《尋寶》(2021)的錄像作品,聚焦新疆喀什與和田地區,并把鏡頭對準了在沙漠中尋找珍貴玉石的個體。
劉雨佳的影片與夏喬伊的編織理念有某種共通之處,其中既有多層的時間,也有多層的空間。影片開頭是巨大而永恒的昆侖山冰川,隨之出現20世紀歐洲殖民探險家斯坦因和斯文·赫定在新疆考古時拍攝的黑白照片,最后以一群2019年的商人在抖音直播上售賣玉石的影像結束。“剪輯時有一個不斷遞進的關系,景別越來越聚焦于小的東西之上。”


在時間上,除了人類攫取開采地質資源這一來自當下與遠古底層的互動,片子還展現了20世紀與21世紀的重合。劉雨佳拍到了斯坦因和斯文·赫定在考古日志中提到的熱瓦依克遺址等等,于是引入了考古日志作為畫外音,配合自己拍攝的畫面來形成跨時間的效果。對她來說,重要的是呈現這些來自過去的日志的“動情之處”:“當時的考古學家都有殖民主義色彩,考古的另一個目的是畫軍事地圖。可是我選取的文本都更個人化,拋開殖民立場,他們其實有許多情感性的書寫,并與我的旅途產生了共鳴。”
對劉雨佳來說,新疆是一個“接觸地帶”,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在這里匯集。這種匯集展現在地質的多層性上:“我拍的地方接近塔克拉瑪干沙漠,那里是佛教傳入中國的必經之路,和田在此前也是小乘佛教的中心。所以這里發生過很多佛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戰爭,曾經是一個很大的戰場,成千上萬的人與雕塑遺跡一起埋在地下。”
疫情、GIF與虛擬網絡:當對城市不再有想象
如果說前兩位藝術家選擇了出走以回應某種困惑,陳維的單路視頻作品《Light me #210902》(2021)則遁入了網絡空間。這件作品創作于疫情期間,一個人孤單地坐在密閉房間圍起來的電腦屏幕前,唯一且微弱的變化是被屏幕照亮的面部。這呼應著這一特殊時期的、被裹挾的時空感覺——人只能被動接受電子設備的信息,日夜與四季更迭都似乎不再存在。

與虛擬世界或網絡有關的作品有很多,陳維覺得大部分與之相關的作品都“太流行文化”了。流行文化的更迭速度很快,當代藝術卻仍然在一個狹窄的視野中,采用非常古老的方法。與其這樣,不如花更多時間做準備,去看有什么是仍然有效的,“我很少會直接把流行文化拿來用。很多東西我會丟在那,先不去管它,如果過一段時間它就沒了,那就不要做好了。”
這也是為什么《Light me #210902》借用了GIF動畫的格式,陳維說:“GIF技術有很多年了,我讀書時就在畫這個格式的動畫,一直到社交媒體興起,它才開始用于表情包,而表情包是語言的擴展。所以GIF這一媒介既與錄像、照片有親緣關系,又因為社交媒體才存活下來。”
將時間拉長至十幾年就會發現,陳維的創作脈絡與全球氛圍的變化息息相關。此前他曾長期關注城市的流變,從2012年開始“新城”系列的創作,探索都市人的生活處境。疫情期間,他覺得“新城”必須要結束了,因為“我們對城市沒有想象了”。
陳維認為,“新城”其實是一種心理狀態。1998年他剛滿18歲,來自小城市的他看到,所有親戚都想著去往更大的城市,對城市的想象是根植在心里的。看到巴黎和紐約就覺得太好了,但如今很少再有這種感覺,不再有在哪里久住的期待:以前是想去“那兒”,現在是無論如何都不想在“這兒”。“可問題是,我們還能去哪兒?”陳維問。

觀展時,袁佳維也提到了中國藝術家在年代和心態上的變化。以八九十年代甚至是北京奧運為節點,此前的藝術家有一種激烈的對抗感,他們會批評后來的年輕藝術家沒有荷爾蒙和能量,也沒有真正的批判意識。而在袁佳維看來,現在的藝術家當然懷有批判意識,只不過這種意識更加微妙了。對于陳維、劉雨佳與夏喬伊來說,這個形容也十分恰當,因為他們必須時刻跨越風的“內側”與“外側”,在一個不存在答案的世界穿針引線。
藝術家要如何一邊承受無力感一邊繼續創作?陳維和夏喬伊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人類學家項飆,“把自己作為方法”地游走于土地之間,并在互聯網之外“重建附近”地創造真實的快樂。這是一個預料之中的答案,但或許也是我們此刻能擁有的最好的答案了。
2024畫廊周北京
展覽時間:5月24日至6月2日
展覽地點:798藝術區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