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中文系在中國大學學科建制中的風光時刻。看似光鮮,其實和時代背景與其內在品質有關,這點作者有著清醒的認識。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科技對人文學的重要影響,中文系開始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戰。如何調整自己,保持學科與思想文化互動的活力,進而重新出發,是有學科擔當意識的學人必須思考的問題。陳平原的文章兼及國內外漢語言文學系共同的問題,代表了當下學人的困惑與不甘。
《中文系的使命、困境與出路》
文 | 陳平原(《讀書》2024年1期新刊)
人文學者喜歡說獨立思考、自由表達,實則很大程度受制于大環境——政治、經濟、科技、教育等。放長視線,具體學者,小困難可以自己克服,若碰上大運勢,個人無能為力,只能在觀察、思考的同時,不斷進行自我調整。我不太相信有哪位著名學者或思想家憑一己之力“力挽狂瀾”,若真的時運不濟,能獨善其身就已經很不錯了。
無論回憶或暢想,都有個時間尺度問題。太過“古老”或無限“遙遠”,都不是討論問題的最佳入口。我更愿意在可審視、可明察、可把握的視野中,討論“過去”與“未來”。若這么定位,三十年或許是個比較合適的尺度——也就是一代人在歷史舞臺上表演的時間。
現在就以“三十年河東”的視野,來談論中文系的遠慮與近憂——涉及國際政治、科技進步、學院文化以及具體的研究策略。
01 大時代與小學科
十一年前,我在《讀書》雜志發表《人文學之“三十年河東”》,主要討論五個話題:第一,日漸冷清而又不甘寂寞的人文學;第二,官學與私學之興衰起伏;第三,為何人文學“最受傷”;第四,能否拒絕“大躍進”;第五,一代人的情懷與愿望。結論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大概是念現代文學的緣故,我相信前路茫茫,既是墳墓,也有鮮花。”
又到了轉折關頭,只好先“瞻前”,再“顧后”。最近兩三年,我多次在演講中回望全球化時代及其危機。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全球化”成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深刻影響人類社會及其日常生活。從蘇聯解體標志著冷戰結束,到二〇〇一年底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WTO),標志著中國的產業(乃至文化)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再到二〇二〇年中美對抗加劇,疊加三年疫情,全球化之路變得波詭云譎。這個并不遙遠的“大趨勢”,無時無刻不制約著我們中文系的教學與研究。

從事學術史研究,審視前輩的足跡,不能只局限于國內政治,還應牽涉國際環境——前者往往與后者互相勾連,密切相關。不僅談論反右、“文革”、改革開放等重要關口,而且將其放置在冷戰大背景下來思考。十年前我在港中大教書時,曾撰寫《中文系的使命與情懷——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北大、臺大、港中大的“文學教育”》,仔細辨析兩大陣營的對抗以及中國的獨特位置、冷戰背景下新中國的高等教育、作為學科的“中國現代文學”如何崛起、不同國家/地區的中文系怎樣受制于意識形態的變遷等。最近兩年,我也不止一次做題為《冷戰背景下的文學史建構——以王瑤、普實克、夏志清為中心》的專題演講,那是集合我好幾篇文章而成,比如收入《小說史學面面觀》(三聯書店二〇二一年版)中談普實克與夏志清二文,還有我討論王瑤先生的諸多文章。如此選題與立意,當然是別有幽懷,不僅指向歷史,而且關涉當下。二〇二三年春季學期,我在北大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其中第三講“冷戰時期的文學史建構(五十至七十年代)”,進一步擴充論述對象,掘發許多學者/著作背后不為人知的幽思。之所以一再致意冷戰背景下東西學人的尷尬處境與隱微心思,是希望給年輕一輩提供借鑒,以回避各種隨時可能出現的陷阱。
以我很不專業的推測,今日世界,既不可能完全倒回冷戰時代的鐵壁銅墻,也迥異過去三十年全球化的高歌猛進。前些天為一位老學生著作寫序,感嘆個人的天資與勤奮,必須有時代的大環境相配合,否則很難順利綻放。“隨著國際形勢變得波詭云譎,地球村的愿景逐漸消逝,下一代中國學者的路能不能越走越順,國際交流與合作到底該如何展開,目前誰也說不清。”
02 從換筆運動、數碼時代到ChatGPT
在中國語境中談學問、學科與學人的命運,原先主要考慮政治(整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突出經濟,如今還得添上科技的因素。剛剛過去的這三十年,科技迅猛發展,徹底改變百姓的日常生活,談論人文學的軌跡與進路,無法回避這一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個很具體的例證,那就是個人電腦普及,以及網絡時代的到來。
我是一九九三年開始使用電腦的,啟蒙老師是著名哲學史家龐樸先生。龐先生那年六十五歲,早已功成名就,可迅速迷上了電腦。朋友中有誰需要安裝、調試或使用個人電腦的,一個電話,他馬上騎自行車上門指導。那年頭,北大晉升高級職稱,外語成績之外,還得考電腦知識——包括IBM的歷史,DOS系統的使用,以及你的中文輸入速度。當初稱之為“換筆運動”,參與者無不意氣風發,也確實使得文人及學者的閱讀、思考與寫作發生巨大變化。但有一利必有一弊,換筆運動的后遺癥,那就是讀書人徹底遠離毛筆與宣紙的古典時代,也不再有保存或研究手稿的習慣了。
不同于換筆運動的潤物細無聲,網絡時代的來臨,更像是疾風驟雨。二〇〇〇年我撰寫《數碼時代的人文研究》,其中有一段,今天讀來仍覺驚心動魄:
最大的擔心,莫過于“堅實的過程”被“虛擬的結果”所取代。不想沉潛把玩,只是快速瀏覽,那還能叫“讀書人”嗎?如果有一天,人文學者撰寫論文的工作程序變成:一設定主題(subject),二搜索(search),三瀏覽(browse),四下載(download),五剪裁(cut),六粘貼(paste),七復制(copy),八打印(print),你的感想如何?如此八步連環,一氣呵成,寫作(Write)與編輯(Edit)的界限將變得十分模糊。如果真的走到這一步,對人文學來說,將是致命的打擊。不要說凝聚精神、發揚傳統、增長知識的功能難以實現,說刻薄點,連評判論文優劣以及是否抄襲,都將成為一個十分棘手的難題——誰能保證這篇論文不是從網上下載并拼接而成?
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變革,誰都希望盡早洞察大趨勢,以便趨利避害。可實際上,科技進步這匹狂傲的野馬,其馳騁方向根本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當初誰也預測不到,還將有比網絡檢索神奇百倍的ChatGPT出現。
作為人工智能技術驅動的自然語言處理工具ChatGPT,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發布,當即引起全球各界強烈震撼,其沖擊波至今沒有消停或減弱。人文學科同樣感受到這一巨大沖擊,朋友們紛紛上網測試,有不以為然的,也有擱筆長嘆的,更多的是陷入沉思。

科技進步以及產業奇跡每年都有,但這回很不一樣,相關報道讓人膽戰心驚。具體到不同職業,比如教師及醫生還有沒有存在價值,藝術家會不會被取代,人工智能技術多大程度影響人文學的研究與教學,眾多討論明顯帶有自我撫慰性質。若真的如OpenAI研究人員預估的那樣,“受影響最大的職業包括口譯員和筆譯員、詩人、詞作者、公共關系專家、作家、數學家、報稅員、區塊鏈工程師、會計師和審計師,以及記者”,那毫無疑問,中文系的處境相當危險。若你交叉質詢ChatGPT:“你對人文學科有何影響?”閉著眼睛也能猜到,回答必定是利弊參半。其中最直接的陷阱是,當寫作可借助ChatGPT完成時,人文學的價值驟降。也有學者對此持樂觀態度:“從技術上看,以ChatGPT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改變了寫作,但它們無法模仿人文學科的創造力、倫理道德和精神氣質。”(郭英劍)這點我相信,問題在于,能從事真正意義上的獨創性寫作的,實在是少而又少。在這個意義上,從網絡時代擔憂的“寫作與編輯的界限變得十分模糊”,到ChatGPT的直接生成各類你想要的文本,而不需要經過長期的文學教育或學術訓練,這對人文學來說,絕對是巨大的災難。
當然,若不是從社會評價的角度,而是著眼于個人修養以及氣質形成,比如閱讀經典的能力,洞察世界的幽微,理解人生的苦難,培養人性的高貴,所有這些確實是ChatGPT所不具備的。在廣州舉辦的二〇二三“書香嶺南”全民閱讀論壇上,我被要求談論“我們未來的閱讀與創新力”,當初的報道是:
“在一個科技進步越來越快,生活越來越便捷的時代,全民閱讀很可能是‘為己之學’。”陳平原認為,當下的全民閱讀有別于職業培訓,閱讀是為了自己的修養、為了自己的愉悅、為了自己的生活充實。三十年后的閱讀將變成什么樣?陳平原提出了自己的暢想:“只要三十年后人們還繼續讀書,就應該多讀‘無用之書’。三十年前計算機考試的教材是‘有用之書’,如今早已被淘汰。但三十年前讀過的那些文史哲的‘無用之書’,卻深深留在了人生里。因此,全民閱讀應該提倡多讀‘無用之書’,多讀跨職業、跨學科、跨媒介的書。”
可這樣的回答,能讓心存疑慮的讀者釋懷嗎?我實在沒有把握。所以,我不敢如樂觀者所言:“ChatGPT的出現讓我們進一步看到了人文學科的不可替代性。”
03 校園內外的中文系
轉念一想,也許是我過慮了。因類似的警世恒言,并非第一次出現,既不能不聽,也不能太信。比如,五年前我還聽過比這更令人振奮,也更讓人擔憂的科技預言。
那是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五日,首屆未來科學大獎頒獎典禮在北京舉行,科學家大膽預言:十年后人工智能超越人類思想;二十年后全球百分之八十的就業人口不用工作;三十年后人類可以實現不朽。我的直覺是,若這三大預言全都實現,世界將變得更加動蕩,人類未來更為堪憂。看到我首先憂慮這百分之八十的閑人/廢人如何度日,主持人說,全都改學文學藝術,很優雅的。真有這等好事嗎?若有那么多人感覺自己完全無用,生活的意義何在?還有,若醫學真的能讓某些人不朽,那么誰來決定每個人壽命的長短,以及人類的新陳代謝如何完成?沒有了死亡這個大限,整個人類的智慧及倫理全部都得重構。
回到眼下,人類未來與學科前途,遠慮與近憂,我們都得關心。這就回到大學校園內,各院系之間的楚河漢界以及利益紛爭,那更是迫在眉睫的難題。我曾專門撰文,主張從“學科文化”角度看“大學”,主要觀點是:作為一種組織文化,大學內部的復雜性,很可能超越我們原先的想象。各有各的學術視野,各有各的專業趣味,各有各的偶像崇拜,也各有各的自尊與自愛。當這些趣味不同、發展途徑迥異的學科集合在一起,組成知識共同體“大學”時,必然會發生摩擦與碰撞。所謂“大學管理”,某種意義上,就是在大學內部進行有效的協調與整合。
具體到我們長期學習、工作、服務的中文系,在當下中國,到底是強勢還是弱勢,我曾專門談論這個話題,引起很多同道的感嘆唏噓(陳平原:《學科升降與人才盛衰——文學教育的當代命運》,《中華讀書報》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外有世俗的薪酬比較,內有大學的經費分配,中文系為代表的人文學處境其實很不妙。作為個體的學者,你可以完全不顧世俗偏見,心無旁騖地讀自己的書,走自己的路;可若顧及學科的發展以及作為整體的人文學者的歷史命運,你又不能不有所反省。多年以前,我曾在一個座談會上慷慨陳詞,而后寫成《理直氣壯且恰如其分地說出人文學的好處》,收入《文學如何教育——人文視野下的文學教育》(東方出版社二〇二一年版),且將其置于篇首,以凸顯我對這個話題的關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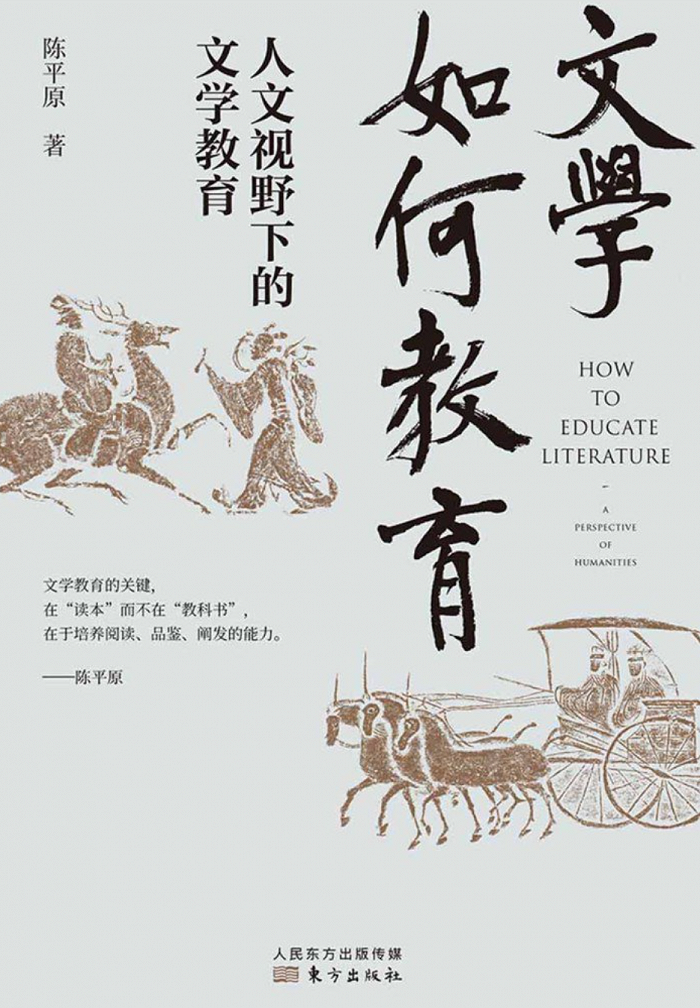
兩年前,北大中文系紀念建系一百一十周年,我有幸作為教師代表發言,其中談及每個國家的本國語言文學系,都是這個國家文化及精神建設的重要力量,而北大中文系對公眾影響力之大,是很多院系所難以企及的。“很大程度,這是一種溢出的效應,也就是超越專業限制的影響力。有的院系很厲害,可他們的影響力局限在本專業之內。中文系你仔細看,它的老師及學生,他們的活動范圍,他們的發言姿態,以及他們影響社會的能量,是超越原先的專業設計的。”正因如此,談各名校中文系的業績,不能只看學科排名,甚至也不應局限于教育史或學術史,適當的時候,還得將目光延伸到文學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過去這樣,希望以后也能如此。演講博得滿堂掌聲,蒞會的北大校長也起立鼓掌。但我知道,并非每個領導或學者都認同我的觀點,只是公開說出來,總比憋在心里生悶氣好。
04 四說“三足鼎立”
這篇文章的題目,原本為《中文系的困境與機遇》,最后刪去“機遇”,突出了“使命”。為什么?因大家都喜歡聽好話,偶爾說到困境,馬上話鋒一轉,稱“危機”就是“轉機”。其實很難的,由危機四伏轉變成生機勃勃,這樣的機遇不能說沒有,但必須是天時地利人和。說話聽聲,鑼鼓聽音,關鍵詞一般在最后,原題很容易一轉而為光明在前,成績為主。其實,尋路的關鍵,在明白陷阱何在,才不會落入大話套話。
最近這些年,我的論述策略是:對外,大聲說出人文學的好處;對內,不斷自我反省,勤練內功,努力提高中文系的競爭力。十多年前,我撰寫《人文學的困境、魅力及出路》,其中有這么一段:“假如將‘學問’做成了熟練的‘技術活兒’,沒有個人情懷在里面,對于人文學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悲哀。所以,我首先想說的是,學問中有人,有喜怒哀樂,有情懷,有心境。”這里所說的“情懷”與“心境”,包括努力為我所安身立命的中文系,尋找困境中的出路。落實到操作層面,我設想了四種“三足鼎立”,并在實踐中不斷地自我完善。
第一個三足鼎立由來已久,起碼有將近百年的歷史。若著眼于學科建制,一九五九年北大在全國率先設立了古文獻專業,并交給中文系統管,至此,北大中文“三足鼎立”局面才正式形成。可實際上,自一九二五年起,北大中國文學系的專業范圍,就不是純粹的“文學”,還包含“語言”及“文獻”。關于這個話題,我在《“中文教育”之百年滄桑》以及《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中有專門的論述。在中國教育部頒發的學科目錄中,目前這三大專業同屬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相互支撐的同時,也在各自拓展視野及領域,比如語言學專業積極申請自然科學基金,古文獻與歷史學結盟,文學專業則擴展到電影、戲劇等藝術學領域。

第二個三足鼎立,指的是古典研究、現代研究與跨文化研究。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國家和地區,到底該如何配置資源,補齊短板,尋求突圍方向,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以北大為例,八十年代創建比較文學學科、九十年代突出傳統文化研究、二〇二二年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的成立,都是有感于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以及學科發展的需要。二〇二一年我給北大校長寫信,提及如何集合跨學科的力量,從整體性和長時段的視野對“現代中國”展開綜合性的研究,是有感于最近二十年來,北大更注重古代中國研究、跨文化研究等領域的學術建設,相對忽略了“現代中國”,資源配置和人才培養方面均相對滯后。我以為,應從戰略上并重古代中國、現代中國和跨文化研究,形成“三足鼎立”的穩定格局,才能更好地承擔起北大的歷史責任。
第三個三足鼎立,說的是研究中如何兼及文字、圖像與聲音。十年前撰寫《“現代中國研究”的四重視野——大學·都市·圖像·聲音》,某種意義上,是意識到時代思潮及技術手段的變遷可能導致中文系轉型的一種對策。延續以前的研究,當然也可以;但引入新的視角及思路,或許會“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我是中文系教授,并沒有受過美術史方面的專業訓練,談“讀圖”其實有點越界。《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增訂版刊行并大獲好評后,我在答問中談及:“只靠文字來傳遞知識與情感,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必須意識到,文字越來越面臨圖像以及聲音的挑戰。”二〇二三年五月,商務印書館推出我的《有聲的中國——演說的魅力及其可能性》,著重討論作為“傳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說”,如何跟“報章”與“學校”結盟,促成了近現代中國思想、政治、學問、文章的變革。該書出版后引起關注,上了好幾個好書榜,九月十六日,北大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主辦“跨媒介視野中的現代中國”工作坊第一期,更是以“有聲的中國”為題,討論聲音研究的各種可能性。在保持中文系師生擅長的“解字”與“說文”的同時,關注圖像與聲音,那樣有可能拓展我們的思考與表達。我相信,追隨時代的變遷、技術的進步、媒介的轉型,以及讀者/受眾能力及趣味的提升,中文系的教學與研究,有必要也有可能擴容與升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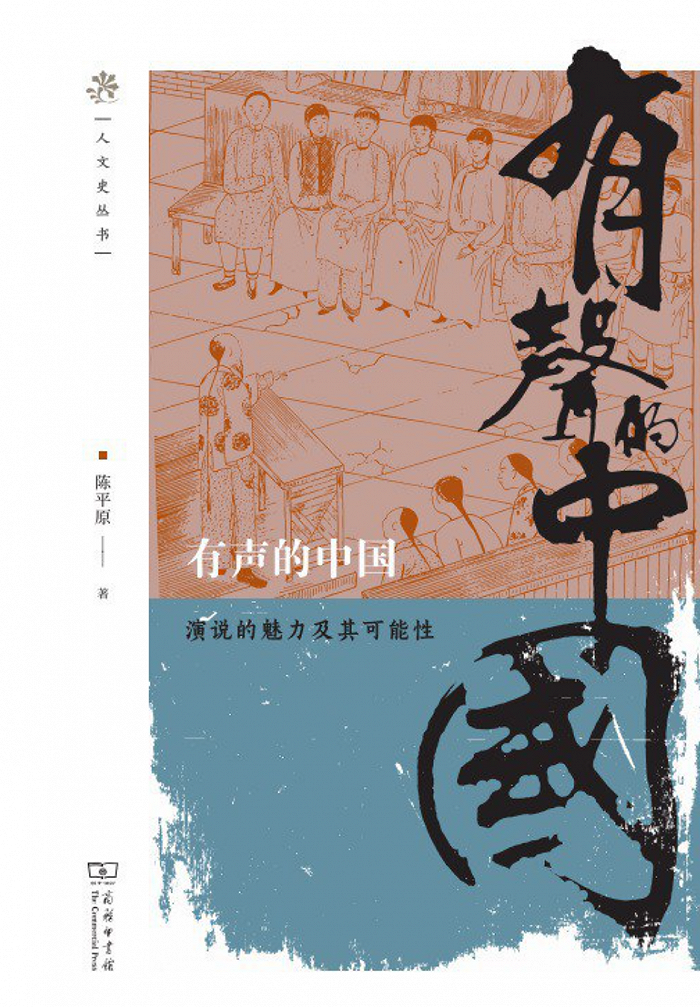
第四個三足鼎立,說的是教學、科研與社會實踐三合一。前兩者乃大學校園里的常規動作,有明確的評價標準,也有制度性保證。至于社會實踐/服務,中文系既不同于自然科學,極少專利可以轉化;也迥異于社會科學,不以智庫見長。我們的走出校園,有貢獻才華服務社會的意味,但也與自身學識與修養的提升大有關聯。換句話說,這里的社會實踐,并非外在的添加,而是內在于我們的教學與研究。這或許是人文學的性質決定的,讀書、讀人與讀社會并重。我曾依自己的趣味,改一副老對聯:“兩耳聞窗外事,一心讀圣賢書。”
來源:讀書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