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期主持人 | 徐魯青
下班后只有精力刷小視頻,沒力氣看書看長電影,好像成了人們的常態。
在《花束般的戀愛》里,主角上班幾年后,從打《塞爾達》的文藝男變成只能玩《智龍迷城》的社畜,再也看不進書了。最近網絡流行的二創改編,各大城市的男女主角踏遍文藝地標,最后都因為工作太累,興趣漸行漸遠而分手告終。除了玩笑,評論區也會出現“我也是男主”、“文化體力”耗盡等感慨。“文化體力”對應著生理體力,指沒有體力參與較為深度的文化、藝術等活動。就像在劇里,男主角看到一墻的書,說自己已經“讀不進去了”。到底是什么讓我們讀不進書了?
觀察身邊的朋友們,很多人都開始放棄完整電影,只看解說,吃飯一小時就可以刷完四五部大片。從多年前開始,我也習慣了看劇調至1.5倍速,一邊快進,一邊跳躍到大結局。最近微短劇的風行或許也和當代人文化體力有關,一分鐘一集的長度,剛好掐準了我們的耐心值。

另一方面,市民夜校和老年大學卻好像火爆起來,原本是老年人占大多數的課堂,現在涌入很多打工后倍感疲憊的年輕人,有媒體把市民夜校看作人們文化體力的喚醒地。瘋狂報名搶夜校的年輕人是為了什么?作為文化記者,每天的工作就是和書打交道,你有文化體力不夠的時候嗎?你如何看待文化體力不足的焦慮?
也歡迎讀者給我們留言,說說自己的看法。

01 看爛片也能治愈,口水歌也有門道
徐魯青:上一天班之后沒有文化體力做深度思考,只能回家刷短劇,你們怎么理解這樣的狀態?
潘文捷:可能是沒有吃飽。忘了哪本暢銷書里有談過,人意志力不夠常常是因為餓肚子血糖低,吃飽了之后就不容易在超市瘋狂采購,不容易和人吵架,可能也會更有力氣閱讀海德格爾吧。
林子人:其實《花束般的戀愛》是我家屬強烈推薦我看的,他有一次出差在飛機上看了這部片子,大為震撼,回家后就拉著我又一起看了一遍。看完后我有點理解為什么家屬對這部片子印象深刻,他其實是對片中男主角的境遇心有戚戚:加班、出差和應酬不斷吸干了自己的精力,回家后就真的只想躺倒刷抖音了(不過也是托抖音的福,家屬對最新影視作品的了解程度比我高多了)。我家也有滿墻的書,他從頭到尾讀完的書兩只手就能數得過來。
徐魯青:有時候看爛片會給我一種治愈感,特別是在情緒脆弱、精力衰竭的時候。人在特別疲憊后容易質疑事情的意義,但小視頻娛樂可以阻斷我去面對這些問題。看“俗”一點的爛片,每個人都活得熱熱鬧鬧的,覺得也挺好,還有什么過不去呢。

潘文捷:如果幸福是快感的總和,那么獲得幸福人生的秘訣就是吸毒。雖說甲基苯丙胺之類的物質不可能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但為啥有些文化消費尤其令人上頭上癮呢?我特別喜歡看大爛片、狗血劇的劇情吐槽,一個是本身劇情狗血夸張,二是解說up主狂噴的語言又搞笑又讓人站在制高點上。
仔細想想,這也是高超的技巧不是嗎?阿多諾批判流行音樂工業化,現在大家都不聽鴻篇巨制的古典音樂,改聽幾分鐘一首的歌曲了。但是流行音樂能做到用同一個4536251做出這么多歌來,還產生了不少名作,也多少有點兒神乎其技。
我們說文化體力的時候往往說的是消費,如果從生產的這一頭去琢磨,并不是用同一個和弦走向的任何口水歌都能紅得起來,也不是任意一個短劇都那么令人上頭,其中也有不少門道。
董子琪:閱讀真的需要門檻。觀影好像好很多,最近看不進去書的時刻,就會看電影,看老電影、新電影、不知名的電影,找回了過去的一點感覺,也有一些更細微的觀察——像是許多流行電影里都會安排男女主人公讀書,像桑德拉·布洛克在《觸不到的戀人》里就一直在讀簡·奧斯丁的《勸導》,《緣分天注定》里凱特·貝金賽爾和約恩·庫賽克因為《瘟疫時期的愛情》結緣。這些文本與電影本身構成了一種互文的關系,也成為了富有意味的注腳。 這是不是意味著流行文化與嚴肅經典之間本來就存在著轉化和流動的可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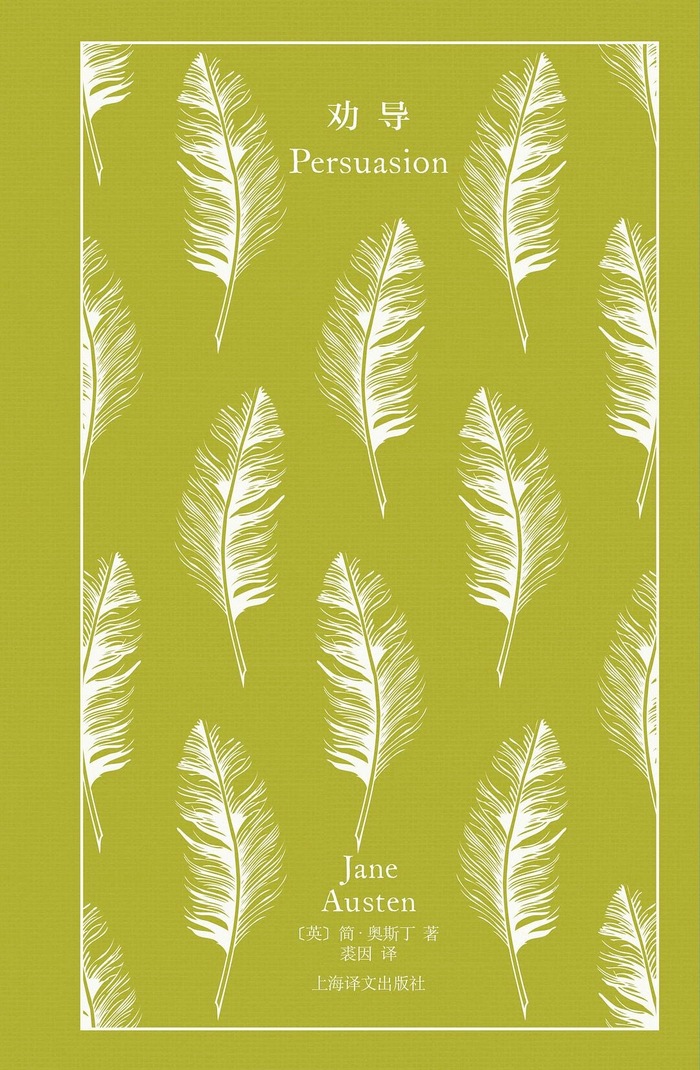
[英] 簡·奧斯丁 著 裘因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1-10
02 資本主義將重構我們的生活、希望和關系
徐魯青:你作為文化記者的狀況是什么樣,有文化體力不夠的時候嗎?
林子人:托工作的福,我們文化記者有很多機會從事文藝活動,但這絕對不意味著我們能一直保持文化體力!就我個人而言,文化體力被消耗的時候,恰恰是自己被要求親歷各種文化現場的時候:展覽、演出和講座,新書、電影和電視劇,我們被要求時刻保持敏感的文化雷達,向讀者介紹最新的熱點事件,但記者的注意力和時間是有限的,我們沒法做到時時在場。
今年為了保護自己的文化體力,我騰出更多時間看書,大大減少了看電影和電視劇的時間,對絕大多數綜藝節目更是敬而遠之。打開任何超過一個小時以上的視頻我都要斟酌一下,能利用獨自吃飯的碎片時間看完的視頻再好不過了。于是我發現自己最近都在看動畫片,現在在追《間諜過家家2》和《葬送的芙莉蓮》。
的確,文化記者能參與各種文藝活動,但我們能抱怨所謂充沛的文化體力帶來的倦怠嗎?《躺不平的千禧一代》這本書的作者安妮·海倫·彼得森也是一位文化記者,她在書中提到的一個現象我感同身受:她認為最應該對倦怠感負責的是社交媒體平臺,它進一步模糊了工作與娛樂的界限,進入社交媒體時代后,每時每刻都是產出內容的機會,你的社交賬號就是一個精心打造的個人品牌,這一點對知識工作者來說甚至更加重要,因為他們的工作就是內容輸出和表達自我。她寫道:
“那些原本能抵消或緩解倦怠的時刻,就這樣被社交媒體撕得粉碎。社交媒體使我們沉溺于記錄發生的事件,而與事件的實際體驗疏離。它也把我們塑造成毫無必要的多任務處理者。它還侵蝕了人們曾經所謂的閑暇時光。而其中最具破壞性的一點也許是,它摧毀了獨處的可能性:凱爾·紐波特(Cal Newport)借鑒雷蒙德·凱斯利奇(Raymond Kethledge)和邁克爾·歐文(Michael Erwin)的定義,將‘獨處’描述為‘自我心靈不受來自其他心靈的輸入影響的主觀狀態’。換句話說,與你自己的心靈作伴,與經驗揭示和挖掘出的所有那些情緒與念頭作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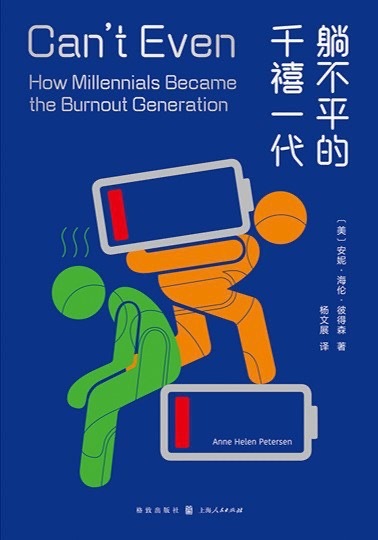
[美]安妮·海倫·彼得森 著 楊文展 譯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10
徐魯青:《躺不平的千禧一代》里描述,美國的“千禧一代”(1981—1996年間出生的人)深陷職業長期倦怠,筋疲力竭的狀態一直持續,休閑時間被工作不斷擠壓侵占,所剩無幾的休息花在手機上。我很喜歡美國記者Ezra Klein給這本書寫的評價:“我們以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經濟的方式。但如果時間足夠長,它的影響還不止于此:資本主義將組織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希望、我們的關系。”
不僅是與人的關系,還有與世界的關系,我們的愉悅感被重塑了,但愉悅不是生命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嗎?看來這個系統不會到點下班,更不僅僅影響我們的銀行進賬,它潛移默化地潛入生命的方方面面。
尹清露:認同魯青說的,資本主義將重構我們的生活、希望和關系。我認為用《花束般的戀愛》來說明這一點十分合適——當生活被壓榨到精疲力盡,連看書的力氣都沒有,自顧不暇之時又怎么指望認真戀愛呢?上次還跟同事聊到,身邊這么多有關婚戀的愁苦和吐槽,前怕NPD(自戀型人格障礙)后怕鳳凰男,好像戀愛更多是關于兩人如何互相戕害而不是互相治愈,但這并不怪人本身,而是我們壓根沒有身處讓人有余裕“對別人好”的環境中。扯遠了,我想說的是,首先要明白看不進去大部頭不是你的錯也無需怪自己,在無助疲憊的時候,guilty pleasure也可以成為救命稻草般的生命之光。
子人說到最近看動畫片較多,然而疲憊的時候,即使是動畫,我也只能看泡面番或者無厘頭的中二作品,尤其是和現實沒有太多關聯的作品,比如最近愛看的《輝夜大小姐想讓我告白》,講的是精英學校的會長和副會長互相愛慕卻死撐著不告白的故事——因為距離現實太遠,看了就會覺得放松。前幾天興致勃勃地打開了期待已久的浦澤直樹的《冥王PLUTO》,其中對中東戰爭和AI的指涉實在是太壓抑,在文化體力不足時,已經很難把它當作娛樂向作品來看了。還依稀記得以前在大學時是很沉迷于浦澤老師那些既魔幻又宏大的敘事的,這樣看來,我非常能共情《花束》男主角的經歷。

03 沒有了文化體力,更無法直面人生的深層無聊
徐魯青:雖然很多人都感到文化體力不夠,但現在市民夜校卻很火,人們打完工還會去上幾節音樂戲劇茶藝課,好像是幾年前沒有的現象。上班之余,“想學門手藝”也是這些年經常聽到的話。手藝好像和文化體力所指的“高雅文藝活動”不同,有一些實用性,但又不會多耗費文化體力。
潘文捷:市民夜校的快樂在我看來既有薅羊毛的快樂,有社交的快樂,也有真的學到什么東西的快樂。
董子琪:文藝夜校看起來非常有趣。我萌生過學個手藝的念頭,也很向往老年大學的課程,總覺得其中醞釀著某種詩意,就像是枝裕和電影里會讓老太太去學習古典樂,應該有超出培訓的意義吧。
其實上海有許多培訓項目,價格不貴,還有補貼資助。我也讀過相關的報道,覺得其中值得關注的是,年輕人想要在公司職場和家庭生活之外尋找到另外的空間,一個可以與人聯結同時又發現自我的場合。這意味著一種對于個體身份多元化的想象,因為平常人們總是固定在一些家庭角色與職位中,而這樣的場合能夠讓人們稍微喘口氣。

作家保羅·索魯回憶過上世紀80年代的北京夜校,向來尖酸刻薄的他,對于那些努力奮斗學習外語的年輕人,變得非常溫柔。他能體會到當時在夜校讀書的同學們迫切渴望念書的心情,鼓勵他們說,人人都知道夜校是個好東西,但是堅持上夜校是世界上最難的事情,因為他們白天全部都要工作,“只能說他們是值得的,他們在盡他們所有地尋找自己在中國大眾中的出路。”
但另一方面,年輕人是不是過于相信培訓了呢?之前參與過一個活動,分享“年輕人不想上班”的話題,在場的年輕讀者的反應也很有意思:有一位讀者表達,不想上班的gap之年,她其實也得不到真正的休息,因為總想要充實自己,所以總要報上幾個班,再學幾門外語。這樣的情況也相當普遍。這是文化體力旺盛的體現,還是無法直面人生的深層無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