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從劍橋大學畢業之前,Ashley就收到了好幾份錄取通知,其中有兩個機會特別吸引她,Ashley可以到瑞士去,進入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商,開啟她的職業生涯,或者進入歐洲排名第一的商學院就讀。無論選擇哪一條路,她就業后的起薪都至少有十萬美元左右。”
Ashley是上海紐約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姜以琳的研究對象之一,是她所定義的中國年輕精英中的一員。
從2012年到2019年,姜以琳追蹤了28名北京精英高中生,從高二、高三開始直到他們大學畢業。他們去往世界各地的頂尖校園,畢業后進入華爾街、硅谷等職場,或是繼續研究深造;他們就讀于北京排名前十的其中五所中學(北京市共近300所中學),他們所在家庭的收入是中國城市家庭收入前10%的兩倍以上。無論是從他們的社會經濟背景還是學習成績來看,他們都是“小鎮做題家”眼中的大城市精英學生。

姜以琳注意到,在同是精英的父母和中學的共同協作下,這群精英學生進入世界頂尖大學,在全球競爭中爭奪到一席之地。她想弄明白的是,家庭與學校資源給予了他們什么?他們是如何運用自己有形和無形的資源爭奪地位,甚至在全球精英競爭中取得成功的?
在著作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中,姜以琳記錄了這項歷時七年的田野研究。今年九月,Study Gods 成為了皮埃爾·布爾迪厄教育社會學圖書獎的第一部聚焦非美國本土案例的獲獎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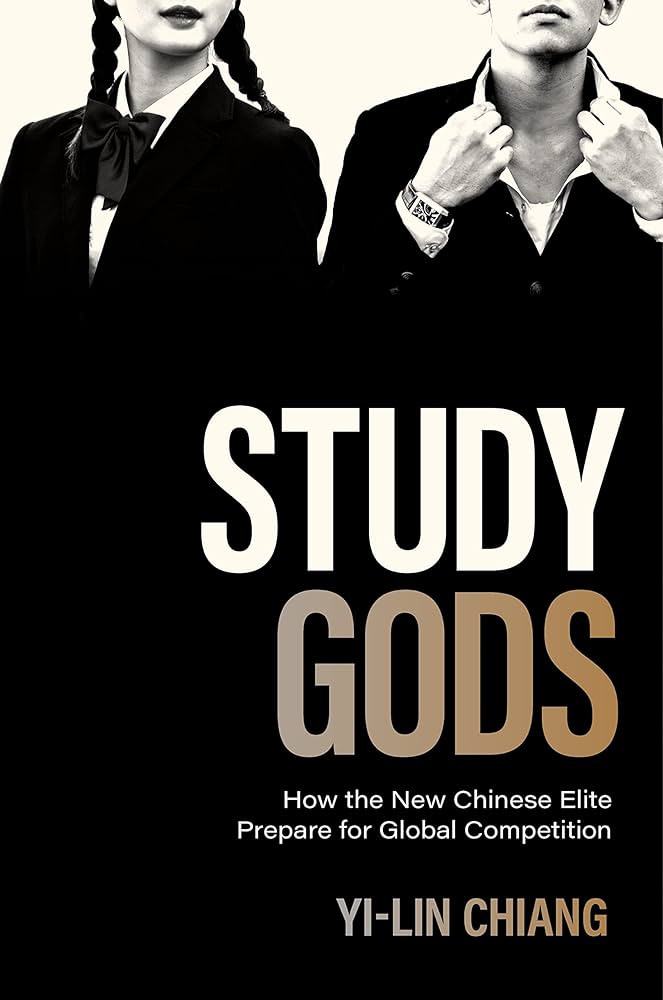
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專訪時,姜以琳分享了七年來在超級高中教室聽課、和學生相伴生活的經歷,以及在走進他們的家庭后看到的精英學生完成精英復制的過程:家庭提供的有形與無形的資源,讓學生毫無后顧之憂地投入全球競爭中。在頂尖高中里,校長老師每日與學生的微觀互動,都累積著精英意識的養成。家庭資源也成為保護孩子免于失敗的緩沖,畢業后萬一職業發展不理想,父母將提供孩子們爭取二次成功的機會,依然擔任后援角色。
姜以琳認為,中國年輕精英之所以能在全球精英大賽中攻城略地,是因為他們懂得如何成為“學神”。實際上,從“學神”到“學弱”的校園系統滲入了高中生活的方方面面,學生采取策略試圖在系統中勝出,并在這一過程中鍛造了駕馭地位等級的能力。“在其位謀其政”的處事方式一直延續至世界各地的職場,她觀察到,精英學生們與老板、同事的互動方式,也仍延續著他們多年前和老師、同學的類似方式。姜以琳說,“身處這套等級系統,學生把考試成績歸結為天賦、能力與基因,并未察覺自己在競爭中的優勢是不平等的結果。”

01 尋找不在西方研究視野里的東亞精英學生
界面文化:最早為什么想做關于中國精英的研究?是否有想對話的理論或者田野?
姜以琳:最早是因為讀到幾本西方教育社會學的經典,西莫斯·可汗的《特權》和Peter Demerath的Producing Success都是在講美國精英學生,都是作者去精英學校考察、作為老師去研究學生不同面相的情況。我看完后覺得很喜歡,但又有一種深層的不滿足,因為在這些研究里我看不到任何我認識的東亞精英學生們,完全反映不出我曾經接觸過的同學們——我的初中是一所私立學校,在那里讀書的人大多都是有錢人,我算是考進去幫學校沖升學率的“書童”。
比如《特權》里提到“愜意感”,我們高三誰愜意啊?里面說學生被培養出文化平等主義心態,可以用相同的心態欣賞莎士比亞式和“俗”的愛情小說。不是,《古文觀止》我們是需要背的,我高中看愛情小說只會被覺得是浪費時間。
所以我做這個研究最早應該是一種不滿足,覺得東亞的情況一定會不一樣,我就自己來做一個研究。
界面文化:從2012年到2019年,你追蹤了北京28位中國精英高中學生的人生路徑,你如何定義新生代中國精英?他們的社會經濟背景是什么樣的?
姜以琳:“精英”有非常多的定義法,大部分東亞社會定義的精英高中學生,是頂尖名校的學生,在北京就是像北京四中、人大附中等學校的學生。

但是我想對話的是世界主流的文獻,所以最后選擇跟他們一樣的定義——家庭收入在全國的前10%的學生。有錢人通常會報低他們總收入,他們的“灰色收入”可能比報稅收入高出許多倍,盡管如此,這些家庭報告的收入中位數也能到達中國城鎮收入前百分之十的兩倍以上,他們是一群非常有錢的孩子。
我參考了一些具體的指標,比如能不能負擔孩子到美國讀私立大學的四年學費,所有家長都確定可以負擔這筆錢。大部分的家庭在北京至少有兩套房子,有的在其他省份也有房產。這些學生的父母幾乎都是借高等教育實現了向上流動,他們在1980年代中后期上了大學,許多父母是清華北大的校友,有一些人有碩士學位,還有一些擁有國外留學的經歷。28個學生里,大多人的父母都至少一個是高階管理或專業人員。
界面文化:你從高二高三一直追蹤到他們大學畢業后工作和讀研,這些精英學生中學后的人生發展路徑一般是什么樣的?
姜以琳:從高中到大學分兩類,一群學生留在了國內,一群人出國讀大學,但到了大學后,兩個路徑合一——他們幾乎全部都出國了,28個人里只有3個人沒有出國。
出國之后,他們大部分不會再回到國內。但人算不如天算,疫情爆發,2020年畢業的那群孩子碩士畢業后沒找到工作,美國留不下來,全部都回來了,現在他們已經在國內工作兩年。我前陣子又見了兩三個人,說還是想出國,方式可能就是出去讀個博,再看要怎么繼續留下工作,或者讓公司外派出去(他們大多數在外企工作)。這群小孩未來的發展一定是跟國際接軌的,他們很愛國,但他們世界公民的認同也很強烈。
當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畢業時找到一份薪水優渥的工作。這群年輕精英里的許多人會進入金融界,但也有人會去做環境保護、科技和學術等等。對于大部分人來說,這些都是令人羨慕的未來。

02 家長與學校在互動中培養精英
界面文化:在你的觀察中,家庭資源在這些精英的成長過程中提供了什么樣的幫助?
姜以琳:有形的幫助是金錢,但我覺得最主要的是無形的幫助。中國很多社會制度不會讓人花大錢,公立教育體系并不貴,加上現在雙減,這樣一來,無形的影響變得非常重要。
比如父母對升學體系的認識。他們怎么會知道大學怎么招生呢?大概率是他們自己也經歷過,而且還勝出了、是贏家,完全知道要怎么玩這個游戲——我們通常說這是“文化資本”。一方面父母知道什么時候要出手幫小孩,一方面知道小孩怎么走可以最快速到達終點,家長心里很篤定、有信心,那小孩會受到父母的影響,就不會那么焦慮,有問題就會跟爸媽討論。
我書里寫到一個女孩Claire,后來去了耶魯讀書,她媽媽是一個有博士學位的人,Claire的家庭成員都受過高等教育,在中國有很好的人脈,但他們不滿足待在中國社會的頂端,希望孩子追求全世界的精英地位。她媽媽就說過,她們家從內蒙出來走向北京,所以她女兒會從北京走向世界。
她媽媽每次都跟我說對Claire沒有任何幫助,其實幫助可大了。她說Claire是個容易緊張的孩子,她就是在閨女緊張焦慮的時候坐在她旁邊,跟她聊聊心里的想法。這相當于心理咨詢了,中國有多少家長能做得到這個呢?有一次在訪問她媽媽的途中,我聽到她接了Claire的一個電話,要她幫忙做個海報,她就趕緊交代博士生,最后大家很快一起印出來一個人形大小的海報。但之后我再問他們的時候,沒有任何人記得,他們不覺得這算是什么值得說的事情。

界面文化:父母的幫助一直能夠延續到多長時間?你在書里提到,學生出國后,爸媽的權利范圍一般涉及不到國外的區域。
姜以琳:這就是世界不公平的地方了(笑)。如果是一個美國或英國的精英,那他們的影響很可能涉及到中國,他可以幫小孩在中國某個地方上學校,或是在文化交流中心安插一個職位,但中國這一代父母是比較難做到的。
對這群父母而言,如果小孩留在國內,他們可以一直幫下去,在單位里幫小孩找個工作都是沒問題的,但每一個小孩最后都走出了父母設立的溫室,往世界去了。
父母還會給孩子做很多備案,尤其在現在這個不確定的全球狀況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這個備案一般就是他們在國內有工作的機會,而且隨時可以再繼續申請一個國外的PhD。這種備案常常是一般中產不會有的視野。
界面文化:在人際互動中,你提到精英中學會讓學生相信自己的意見很重要,教師有意或無意間在學生身上培養出一種精英權利意識。具體是如何運作的呢?
姜以琳:學校會一直對學生說“你很重要”,老師常對學生說他們會“改變世界”,和學生閑聊時經常提到“我們顯然比別人更好”或者“我們是本區最優秀的學校”。我做研究的時候,副校長指著往來的學生自豪地和我說:“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學校都說我們學校的學生是天才!”校長也會和學生直接溝通,很尊重學生的意見,學生未來就會有預期有權力的成年人會滿足他們的要求。
這些在大部分學校都是沒有的,只有精英高中才有。有些高中可能一直會對學生說“你不夠好”,但這幾所學校是不斷提醒學生,他們比其他學校的學生更優秀,每個人都有無限可能,都會做出巨大的貢獻。聽著聽著學生就會習慣,我就是一個很好的學生,我就是個優秀的人,我就是可以做成很多事。
這就是一種不平等,誰可以上這些學校?誰有能力?誰會在家庭和學校中接收到這些一致的信息?老師、家長,同學之間也互相形成這樣的信念,最后組成一個極小圈子的群體。這是只有精英才會有的一個成長過程。

界面文化:《不平等的童年》一書對美國的中產群體教育方式也有類似的觀察,中產家庭的溝通方式常常是協商而非指令,孩子可以反駁成年人的話,從中習得精英權利意識。在這一點上,你覺得這種意識是共通的嗎?
姜以琳:關于“我值得”的信念這部分是共通的。他們相信,我就值得被這么好地對待,我就值得拿到這么多的資源。
書里我寫到了一個男孩子Tony,在美國工作,生日找了一大堆朋友同事,來他的頂樓公寓喝酒聊天、打牌慶生。但他從來沒有想過,公司的同事剛去完兩個禮拜的集訓,換了三個城市,每個人都非常累,他從來沒有想過有人會拒絕他的生日邀請。
03 “學神”-“學弱”鄙視鏈的調試與顛覆
界面文化:你在書中詳細描繪了精英中學內部學生地位的劃分方式:學神、學霸、學渣與學弱,依次降低。等級的劃分依靠的是考試成績和愜意程度——金字塔頂端是“學神”,指不太用功但考試成績卻很高的學生;最底層是“學弱”,即很用功但成績不好的學生。“學神”到“學弱”的金字塔等級分類體系會影響到什么時候?學生畢業后的分類評價會發生改變嗎?
姜以琳:這個體系直到工作后也一直延續下來。我訪問的是同一群人,他們不記得七年前跟我說了什么,但我回去聽錄音稿,發現他們用七年前一模一樣的、描述同學和老師的字眼,去描述七年后的同事和老板。
比如我問一個學生為什么跑去跟老板說一大堆事情,為什么老板要對你這么好。她說,我這么好的員工,老板當然喜歡我呀。七年前我問過她類似的問題,有一天她半夜打電話給老師要求改一個文章,而且30分鐘之內就要上傳好。她說一模一樣的話,老師當然喜歡我啊,我這么好的學生,為什么不喜歡我呢?他們跟老板的相處方式,延續了以前和老師的相處模式。
這些學生覺得,個人表現會直接影響上司是否喜歡他們,那些覺得自己表現不好的人不敢違抗上司,而成功的人認為在上司面前應該擁有某種特權。雖然他們大多數人已經是收入金字塔頂端了,他們依舊贊同自中學以來的特權和績效表現掛鉤的社會地位模式。
對“學神”、“學霸”來說,世界就是他的后花園,他們想要做什么,同學老師們都支持,世界有什么東西是不能嘗試的呢?但如果學生成績不好,相當于達不到社會對你的唯一要求,老師、同學和家長都不會給你什么自由。如果你想要去做一件不太一樣的事情,爸媽就會說,你要不要先把成績顧好?老師可能說,這對你有點難,他的整個心態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我覺得長期來看,兩群學生也會有不一樣的發展。

界面文化:如果是這樣,在中學地位比較高的“學神”和“學霸”到了職場,會在人際互動方面比“學渣”展現出更多權利意識嗎?
姜以琳:不一定。這些學生習得的,是在每個場域立即區分自己在什么地點、哪個位置。高中的時候可能是“學神”或“學霸”,到了大學要重新區分一下,發現變“學渣”了,就會表現出不一樣的行為。工作后同樣也會根據地位進行調整。
我在書里寫到一個去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學生,到了大學她表現還不錯,也屬于高地位的一群人,但到華爾街工作后突然發現自己工作能力不行,沒有其他從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來的人優秀,她的行為突然就變了。我在高中跟著她的時候,她跟我說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大學的時候,她也說想怎么玩也沒有問題;但工作的時候,她就是不敢離開崗位,怕老板隨時找來。我跟她約了時間見面,但那天下午五個小時里,她一直不敢離開電腦,五個小時都待在房間里等Email,怕老板突然來找她。她發現這個世界不是后花園了,她要開始注意很多事情了。
界面文化:根據地位調試的行為改變似乎很快。
姜以琳:很快,他們學的不只是自己的行為模式,而是內化了整套地位體系的運作方式,所以隨時都知道人在什么位置要做什么事。除了他們擁有的社會經濟資源,精英學生們還了解決定彼此在社會中相對位置的潛規則。在一個依照潛規則運作的世界,這些能力可以帶來實際的好處。
界面文化:最重要的是“成績”和“愜意程度”兩項指標,研究美國精英高中的《特權》一書也注意到了學生身上的“愜意感”培養。你覺得這是同一種“愜意”嗎?
姜以琳:這個問題我也想了好久,因為提到愜意感,就需要和之前的概念有對話。《特權》里的愜意感更像一種文化資本上的愜意感,是我的身體感受到的,我很輕松,跟任何人講話都不焦慮,見到同學跟見到校長、見到主席都是一樣的愜意,這是一種文化資本,必須要有某些背景或家庭的資源才能得到的愜意。
但是我在書里提到的愜意感,純粹就是數字上的“愜意”,是每天花多少個小時睡覺、多少個小時念書,身體本身愜不愜意是不知道的。他可能每天睡覺都睡不著,因為他很焦慮,可能吃飯都狼吞虎咽。這不是真的文化資本的愜意,就是一個時間的量化指標。
界面文化:你在調查的幾所中學里都區分了本部和國際部,在你的觀察里,這套金字塔等級體系都適用,你覺得本部和國際部學生的評判標準是類似的嗎?
姜以琳:是一樣的,我也很驚訝,論文都是要有一個比較的單位吧,我本來是想要比較精英學校里的有錢人和勞工群體,后來發現這些學校幾乎沒有勞工群體,少到沒有辦法做。有的話大多是少數民族,那又牽涉到更多問題。所以我就想,那就比較本部跟國際部吧,出國的跟不出國的學生,然后就發現完全一樣。
我想可能是因為他們就是在同一個環境下長大,從出生到18歲都在國內,處事的方式大概是一樣的,只不過有一群人有三年是用英語上課,然后準備出國,另一群人是準備高考,像國際部的“學神”到“學弱”的體系劃分主要也是成績,最重要的是能申請到哪里,就像本部的高考成績一樣,說到底都是看成績。

界面文化:這樣的地位金字塔體系,你覺得和西方學校中的地位劃分方式有何不同之處?
姜以琳:西方學校不是一個單一的金字塔,而是有幾個評價維度,比如學業、體育、藝術音樂等。可能最被喜歡的是有學業成績的學生,但學習成績實在不好沒有關系,體育好就行,或者音樂藝術好就可以。但中國的體系劃分很簡單,就是學習成績加上愜意程度 ,其實就算沒有愜意也沒有關系,只要成績高,地位就是高的。
界面文化:進了大學,你提到許多北京地區的學生,對比人口大省考入名校的學生們,無法再維持學霸地位了。這些精英學生們會有什么樣的策略?會用什么方式區別于“小鎮做題家”嗎?
姜以琳:他們沒有尊稱過“小鎮做題家”,顯然這已經不是尊稱了,但我連這個詞都沒有聽他們用過。他們會跟我說那些人像瘋子一樣,“他們都瘋了”,“像是神經病一樣”。這些學生進入頂尖大學后,發現自己做不成“學霸”了,他們會把整個位階都顛覆過來,改成為最頂尖是“學神”,第二層就到“學渣”,再之后才是“學霸”和“學弱”。扭轉這套階序的說法是大學要探索自我,要學會怎么生活,不能只是學習。
最有意思的是,我去問其他省的同學,大家也都服從了這一套新的排序。如果我說北京的大學生成績不怎么樣,其他省的同學會說,他們是“素質”更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懂得探索自己,和北京學生說自己的話一模一樣。精英學生即使人這么少,但就是有能力扭轉整個態勢。
但對于出國的學生來說,就算發現自己滑落到了“學渣”,也沒有能顛倒以前的序列。其中還有性別的差異,比如女生通常高中成績都比男生好,所以去美國會讀很好的學校,像普林斯頓、耶魯這些地方,去了之后發現自己成績不行。但男生可能學校沒有很靠前,就發現自己成績還不錯。所以男生經過國外的一番洗禮,自信心都出來了,女生反而八成都出現了壓力、焦慮等問題。
界面文化:你在書中提到“假裝愜意”的學生。她從耶魯畢業,后來找的工作并不滿意,但她向周圍人強調,選擇這份工作只是因為懶得繼續再找了,實際上她為了得到這份工作付出了很多,表面上的輕松掩飾了她實際上在偷偷努力。
姜以琳:她本來是“學神”,后來到耶魯地位滑落,以為可以變“學霸”,但眼看著不能了,所以就趕緊強調愜意感。因為她不能變“學弱”,強調愜意感還可以把自己保留在“學渣”的位置。“學神”是不會刻意強調愜意感的,“學渣”最強調,因為它一定要跟最下面的“學弱”分開。
界面文化:為什么變“學弱”那么讓人害怕呢?大家害怕的到底是什么?
姜以琳:他們怕自己的努力沒有任何回報,這是讓人很難接受的事情,跟所謂“美國夢”和“中國夢”的說法都不一樣。

我們一直都覺得世界就是我努力就可以成功,至少努力會有一點希望,分數會更高一點,大家會更喜歡我一點,但最后發現盡了自己一切所能都沒有成功機會。學生們也不知道怎么解釋,他們會說“學弱”是基因問題,把成績和地位歸結為個人能力。大部分人避免變成“學弱”走的是不承認努力路線,有一些會假裝不在乎,但其實他們很在乎。
對于努力但沒有成果的人,這個社會不存在一種解釋的話語或者機制,完全沒有安慰,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04 從精英高中走向世界
界面文化:很多關注社會不平等和階層復制的研究,考慮的是一個國家的情況。而你的這本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指出,精英地位的復制是跨國進行的,新生代精英完全可能在一個國家出生,到另一個國家接受教育,去第三個國家工作,最后在第四個國家退休。你覺得從全球范圍內考察階層復制,可以為此前單一國家范疇的考察帶去什么新視野嗎?
姜以琳:眼界放開的話,你在意的東西就會不一樣。如果我只是在國內看的話,那上清華北大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進入一個國企單位也會是最重要的事情,甚至,如果你是女性的話,嫁一個好先生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但如果我們放眼全球化的話,在國內視野內原本重要的東西會發生扭轉。

界面文化:你認為,中國的年輕精英之所以能夠在全球精英大賽中勝出,是因為他們懂得如何成為“學神”。但是全球精英競爭中的優績主義標準和國內并不相同,中國精英是如何把高考經驗轉換為全球競爭的資本的?他們在中國升學競爭中所學習的策略,可以延伸為全球競爭優勢嗎?
姜以琳:最有趣的是,美國人沒有在跟中國人來往,中國人一多就自成一國,有少數的學生是非常認真努力想要學習美國、英國,但毫無例外全部都失敗了。我問在美國的學生,他們通常跟誰混在一起,你們朋友是哪里人,大多都是中國人。
一般留學生不跟其他人來往,可能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因為就代表沒有資源,人際關系網不夠好,但精英可以直接復制他自己的圈子。
界面文化:當中國新一代精英學生大量涌入國外,不同優績標準是否會發生互動和沖撞?比如你在書后提到中美教育有相互靠攏的趨勢?
姜以琳:有研究表示是會發生沖擊的,加州有一些華人很多的學校,突然變成跟中國一樣,連白人老師評價學生都是,TA很普通,就是個白人。那篇文章的標題就叫When White is Just Alright,發現白人在這套標準中已經變成中間檔次了。還有研究說,美國很多白人看到學校或者社區里的華人或者韓國小孩變多,就會搬走。除了種族歧視之外,也是因為覺得這個學區難上大學,因為美國申請看的不只是SAT成績,還有校內排名。
還有一些研究發現,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很多學生意識到,成績不好就上不了好學校,找不到好工作,越來越在乎有沒有好的GPA,雖然其他的課外活動也很重要,但沒有以前那么在乎了。
兩國之間的靠攏趨勢也會有的。如果你仔細看,從布什到奧巴馬都在講小學要開始考試,美國至少在K12前(編者按:指小學一至高三的教育體系,即小學、初中、高中三個階段的基礎教育)和中國越來越接近。另一方面,國內也有自招面試,高校希望招到多面向的學生,而不是只準備考試的學生。所以我覺得,至少在政策方面似乎是有靠攏趨勢的。
(本文圖片除注明外均來自視覺中國)



